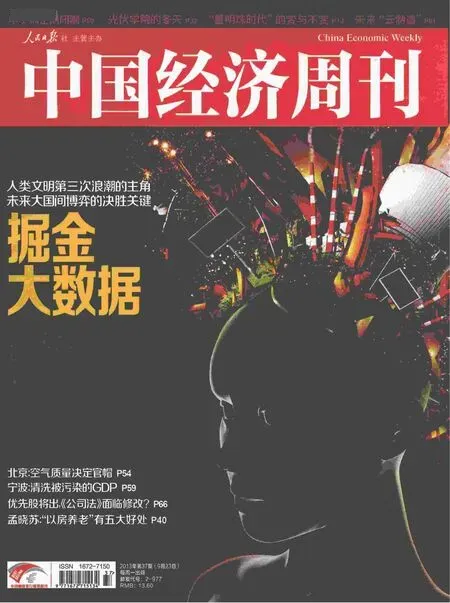上海試點藥品注冊與生產分離
程子
“這一改革實際上就是打造了生物醫藥產業的‘平臺經濟,由專業的研發型企業進行研發,由專業的生產型企業進行生產,分工協同,極大提高藥廠的效率,有利于突破土地資源和環境資源的約束,促進藥企強強聯合。”活爾科技創始人易翠林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
8月3日,上海市食藥監管局發布《上海市開展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工作實施方案》(下稱“上海方案”),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率先在上海破冰試點。
巨資建廠,還是低價“賣青苗”?
2008年4月,從德國留學歸來打算創業的易翠林博士第一次聽說國內藥品上市的政策是醫藥企業必須研發和生產“捆綁”。
這讓1997年到德國留學,在德國學習工作了11年的易翠林覺得很奇怪,因為在德國施行的是藥品上市許可制度,即MAH制度,醫藥公司或研發機構在研發出新藥、獲得藥品批文之后,可將藥品的加工和生產委托給具有規模化藥品生產能力的制藥工廠進行代加工生產。
雖然當時從國外帶回來的創業項目外用中藥制劑已經研發成熟,但是礙于生產研發捆綁的政策,易翠林覺得步履維艱。
“如果將這一研發成果申報臨床批件并拿到生產許可,再后續建廠并建立銷售渠道,就需要籌措大量的資金。我了解到,生產一種生物藥,從廠房建設到設備投資,國際標準在5億元左右。這對于一個靠自己的有限資金歸國投資創業的科技型初創企業來說,簡直是望而卻步,壓力巨大。”易翠林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回憶當時的情形。
易翠林所遇到的情況對于藥品研發類的科創型企業十分普遍。試點方案發布前,國內藥品上市遵循的是2007年修訂的《藥品注冊管理辦法》。根據《藥品注冊管理辦法》,我國對國產藥品實行上市許可與生產許可合一的管理模式,僅允許藥品生產企業在取得藥品批準文號,經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認證后,方可生產該藥品。
因此,在過去,藥品研發機構和科研人員往往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花巨資自建一家生產企業才能取得藥品批準文號。另一種便是忍痛 “賣青苗”給藥品生產企業。
根據業內人士透露:一種生物藥的研發時間一般長達10年以上,一般研發費用占銷售額的5%,有的為15%~20%,如果再建生產線,那么成本會一路飆升,而且必須在二期臨床前就要把錢投進去,即使把廠建起來了,頭兩年主要精力放在藥品上市申請上,工廠相當于空轉,利用率不足30%,造成了巨大的不必要的浪費。
迫于資金壓力,很多科研人員和研發機構只好選擇第二條路:賣青苗,即科研人員在實驗室完成了新藥研究的前期技術工作,發表了論文,取得了科技成果獎,但由于大多數科研機構和高校不具備進一步研究開發和生產經營能力,只能將成果轉賣給有興趣的企業和相關機構。
據了解,一個“青苗”的價格大概為幾百萬元人民幣,相對于科研院所前期研發投入的技術成本,這樣的價格是非常低廉的。
這就造成了另一個極端的情況出現。清華大學法學院衛生法研究中心、藥事法研究所主任王晨光教授認為:“有些研發者追求短期利益,進行技術轉讓,從而不再關心藥品的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甚至還有一些研發者采用私下多次轉讓、分段轉讓或‘重復研發,導致藥品研發低水平重復和創新乏力等一系列問題。”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曾在官網解讀《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方案》時指出:“這種藥品注冊與生產許可‘捆綁的模式,不利于鼓勵創新,不利于保障藥品供應,不利于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開展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工作,對于鼓勵藥品創新、提升藥品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生物醫藥產業“平臺經濟”的上海試點
2015年8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揭開了深化我國藥品監管制度改革的大幕。2016年6月,國務院正式發布《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方案》將試點區域定在上海等10省市。
上海市食藥監局8月3日發布上海方案,藥品上市許可和生產許可正式“雙分開”,上海成為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的率先破冰試點。
上海市食藥監局副局長陳堯水介紹,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改革有三大重要內容:一是“擴圍”,允許藥品研發機構、科研人員作為藥品注冊申請人,提交藥品上市申請,在取得藥品上市許可及藥品批準文號后,成為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二是“代工”,批準上市藥品的生產,允許持有人委托試點行政區域內具備資質和能力的藥品生產企業承擔。三是“更替”,申請人或持有人在藥品上市許可相關申請已受理、尚未審批階段或獲得批準后,均可以提交補充申請,變更申請人、持有人及受托生產企業。
試點藥品范圍主要包括2016年6月6日后批準上市的新藥、按新標準批準的仿制藥,以及2016年6月6日前已批準上市的部分藥品。不包括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放射性藥品、預防用生物制品、血液制品。
同時,對于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上海方案也有明確的規定,必須是注冊地址位于上海市且依法設立的藥品研發機構、藥品生產企業,或者工作地址位于上海市且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科研人員,同時均需具備藥品質量安全責任承擔能力。
易翠林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國家這一新政策的出臺,對我們研發型的企業來說,如沐春風。把有限的資金用在我們最擅長的研發環節上,而生產和銷售尋求與適合的廠家合作,既能緩解我們資金不足的壓力,又能避免產能浪費‘廠空轉。相信通過這種創新的模式,可以使中國患者獲得更多高質量的創新藥。”
陳堯水認為,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改革將夯實上海生物醫藥產業的“平臺經濟”,由專業的企業進行研發、生產,分工協同,做強做大;有利于突破土地資源和環境資源的約束,促進藥企強強聯合;有利于加快新藥上市,落實供給側改革,滿足市民對優質、價格合理藥品的需求;有利于集聚藥品科研人員、研發機構、創新企業,助推上海科創中心建設。
據了解,為了鼓勵企業參與試點,上海還設立了試點藥品的風險救濟資金,對注冊在張江高科技園區核心區內的持有人和受托生產企業,提供風險救濟保障,并為企業購買商業責任險提供保費補貼。此外,上海市食藥監管部門還提前介入加強服務,對試點單位、試點品種開辟綠色通道,加大技術指導和服務力度。
根據上海市食藥監局提供的材料,上海方案自2016年7月25日起,實施至2018年11月4日。
建立新型的藥品監管模式將成新難點
其實,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是歐洲、美國、日本等制藥發達國家和地區在藥品監管領域的通行做法。以美國為例,美國的新藥申請包括兩個步驟:新藥研究申請和新藥申請。一般將藥品上市許可頒發給醫藥企業集團總部和科研單位,而將藥品生產許可頒發給具體制藥企業。
根據業內人士的介紹,因為國外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已經運營很久,所以對于各方的權利義務以及契約精神等已經“約定俗成”。
2016年8月,活爾科技的中藥項目通過了上海張江藥谷的審批,可以落戶張江藥谷平臺,有幸能夠參與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改革。
但是易翠林仍然擔心三個問題:研發型企業在委托生產過程中的專利保護問題;藥品質量負責主體責任如何明晰的問題;基于雙方的相互依存關系,如何實現雙方的數據共享及數據保密問題。
易翠林擔心的也是上海其他研發類藥企所擔心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破冰試點接下來會遇到新的難題。業內人士認為:接下來將面臨權利和義務的重新分配,而政府的監管難度將加劇。
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查閱,《上海試點方案》對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規定了7個方面的權利和義務,除了履行法律規定的主體責任、建立有效的質量管理體系外,還規定應與受托生產企業簽訂書面合同以及質量協議,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與責任,并督促受托生產企業切實履行;同時委托受托生產企業或者具備資質的藥品經營企業代為銷售藥品的,應約定銷售相關要求,督促其依法依規并落實藥品溯源管理責任等。
而對于受托生產企業做了兩個方面的規定:一是履行《藥品管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規規定的有關藥品生產企業在藥品生產方面的義務,并且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二是誠實守信,履行與持有人依合同以及質量協議等約定的相關義務,并且承擔相應的責任。
《上海試點方案》的試點工作中如何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根據上海市食藥監局提供的材料:對于藥品上市企業的監督管理包括監督持有人履行保證藥品質量、上市銷售與服務、藥品監測與評價、藥品召回等義務情況,督促持有人建立嚴格的質量管理體系,確保主體責任落實到位。對于本市受托生產企業的監督管理,內容包括監督受托生產企業嚴格按照《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組織生產、履行與持有人約定義務等情況。
王晨光建議,監管部門不僅要在審評審批等節點上進行靜態監管,而且要對藥品全生命周期進行動態監管;不僅要自身切實負起監管責任,而且要通過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推動“多元參與”和“社會共治”新監管模式及體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