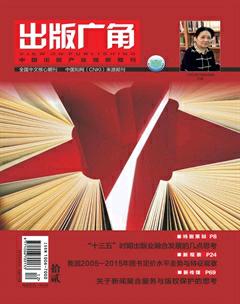論口述體紀錄片的文獻特征
【摘要】口述作為一種文明傳承的主要形式先天具有文獻性,而從紀錄片的起源則可以看出文獻性是其本源特征,因此,口述體紀錄片是最能體現本源特征的紀錄片形式。借由口述方法的使用,口述體紀錄片的文獻性主要體現在私人化和當代性兩個方面。私人化為我們呈現新的歷史視角與歷史細節,當代性為我們建立對當代生活的信心。
【關鍵詞】口述體紀錄片;文獻性;私人化;當代性
【作者單位】楊吉琳,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口述,是當今國內紀錄片創作的重要敘事策略。口述體,也日漸成為一種成熟的紀錄片類型而獲得更多的關注。從經典的藝術紀錄片,到活躍于電視媒體的商業性欄目紀錄片,口述都在當中起到了重要的敘事支撐作用。口述體紀錄片中,屬于經典紀錄片范疇的有賈樟柯的《海上傳奇》,電視紀錄片《大魯藝》,崔永元團隊的《電影傳奇》《我的抗戰》等;屬于口述體電視紀錄片欄目的則有央視的《講述》,北京電視臺的《口述》以及鳳凰衛視的《口述歷史》等欄目。要理解口述體紀錄片的審美特征,毫無疑問得從口述這種方法講起。
口述,作為一種以口頭敘述來傳播的方法,在人類文明史上早就存在,它甚至就像人類歷史一樣古老,是傳播學所講的人類最早的傳播媒介。在文字出現之前,人類的文明、歷史等知識都是通過“口傳心授”這種傳播途徑來實現的。文字出現之后,文字的記載取代口述成為知識傳承的主要方式。然而依然有很多的故事,乃至個人的記憶不為紙質媒體所記載,仍保持以口傳的形式傳播。在西方有游吟詩人,在中國有說書人,他們就是典型的口述者。直到今天,各種各樣的傳奇故事、稗官野史、家族記憶、個人際遇無一不是以口述的形式進行傳播的。
一、口述體紀錄片的文獻性契合了紀錄片的本源
紀錄片使用口述的方法作為敘事技巧由來已久。紀錄電影史的發展進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直接電影”和“真理電影”的紀錄方法與實踐的興起,以往紀錄片“畫面加解說”的經典“格里爾遜模式”被新的紀錄方法與理念取代。紀錄片電影人開始走上街頭進行實景采訪與拍攝,普通人的生活與講述開始走進紀錄電影。時至今日,當時所開創的采訪方法已經構成紀錄片以及電視節目的重要素材來源。但在一般的電視節目中,采訪與口述只是一種方法,所產生的作用自然不能與其在口述體紀錄片中產生的作用相提并論。在口述體紀錄片中,口述不僅是一種素材來源,也是作為作品的結構性支柱的一種敘事策略,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能夠深刻地體現創作者對口述的態度,以及對口述方法的信念與執著。《大魯藝》的總編導閆東就曾經表示自己對口述體紀錄片情有獨鐘,“用電視這種方法來反映口述歷史,會比文字有更大的優勢”[1] 。紀錄片創作中的這種策略、類型傾向與信念,深刻影響了當今紀錄片創作的格局,也創造了口述體紀錄片獨特的審美特征,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口述體紀錄片的文獻性特征。
在紀錄片的所有特征中,最能說明紀錄片本源的便是紀錄片的文獻性。紀錄片英文詞源documentary的本意就是“文獻資料”,最早將這個詞語與紀錄片聯系在一起的是英國人格里爾遜的一篇評價弗拉哈迪影片《摩阿拿》的文章。在文章中,格里爾遜指出《摩阿拿》對波利尼亞青年的日常生活事件所做的視覺描述,具有文獻資料價值(documentary value)。毫無疑問,紀錄片的第一屬性便是文獻資料性,只不過documentary這個詞在翻譯成中文時被譯作“紀錄片”,文獻資料的第一屬性便讓位于紀錄這個名稱所指涉的記載與載錄功能。documentary更偏重于內容的“資料文獻性”,紀錄片則更強調功能的“記載、載錄”作用,其區別之下依然無法否認文獻性是紀錄片的本源性特征。
文獻作為被歷史流傳下來的,有一定價值的知識體系,是人類在社會活動中積累知識的主要載體,也是傳播交流的方式。紀錄片能夠具有文獻性,毫無疑問是基于影像的機械復制機制,這種機械復制機制與以往以文字為代表的記載工具相比,更具客觀性。電影史上最早的一批影片都可以稱為紀錄片,甚至從更廣義上來說,即使是故事片,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時人們生活與思考的體現,在今天乃至更遙遠的未來,都可以將其視為某一個時代的反映,從而具有一定的資料文獻價值。比如在今天的電影研究中,我們經常會去審視某個獨特時代的電影,以期用之解讀那個時代。
在人類歷史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口述都是人類文獻資料傳播的主要手段。只不過口述的方法重新獲得重視,有其時代背景。一方面,口述作為一種歷史寫作的方法越來越成熟,口述史已經成為史學寫作的一種重要模式。另一方面,受20世紀中葉新歷史主義思潮的影響,“新歷史主義把言說歷史的話語權交給了普通的生命個體”[2]。口述的方法也在新歷史主義的潮流中獲得了重要地位。也就是在同樣的背景下,口述體紀錄片作為一種紀錄片類型開始逐漸成熟,并以其文獻性契合了紀錄片的本質屬性。進一步審視口述體紀錄片的文獻性,我們便會發現,口述體紀錄片與傳統文獻紀錄片的文獻性有所差異。如果說傳統文獻紀錄片的文獻性主要體現在文獻的宏大性與歷史性的話,那么口述體紀錄片的文獻性則更多體現在私人化與當代性上。
二、口述體紀錄片文獻的私人化
在口述體紀錄片中,文獻的私人化不再是以正史、官史等宏大的面貌呈現,而是以私人化,尤其是個人記憶的形式呈現。正如史學家保爾·湯普遜所說的那樣,與正史、官史不同,文獻愈是私人、地方和非官方的,就愈難以幸存[3]。與官史、正史有專人負責,有專門的經費作保障不同,私人化文獻與記憶極有可能隨著當事人的離世而徹底消失。因此,幾乎所有從事口述史與口述體紀錄片工作的人都是在以搶救文獻的態度來進行工作的。無論是《大魯藝》的總編導閆東,還是在中國傳媒大學進行口述史研究的崔永元都有過這樣的表述。口述體紀錄片中這些私人化的文獻視野也為其作品呈現了獨特的審美格局。
1985年上映的《浩劫》是導演克勞德·朗茲曼歷時11年完成的長達9個小時的紀錄片。這部反映猶太大屠殺的作品可以說是口述體紀錄片的最早嘗試。此片并沒有像同題材的其他紀錄片一樣引用大量的關于大屠殺的影像資料作為文獻,而是采訪相關當事人,以當事人的口述作為主要文獻。在朗茲曼的采訪對象中,既有當時的受害者、施害者,也有一些旁觀者。與正史、官史的描寫不同,他們是當時事件的親歷者,他們的記憶與口述中帶有很多的私人角度和歷史細節。在朗茲曼的拍攝實踐中,最能體現與正史不同的私人化便是對諸多旁觀者的采訪。這些人中有當時負責在婦女被送入毒氣室之前,把她們頭發剪下的理發師,也有負責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的火車司機,以及集中營附近的農民。在正史中,這些旁觀者只是作為歷史中一個很小的細節,甚至只是作為歷史的大背景而存在。但是在朗茲曼的鏡頭里,他們作為證人,向觀眾分享他們的個人記憶。這些口述因建立起與正史、官史不一樣的視角而鮮活起來,歷史因為有了見證人而顯得更真實可信。
集口述體文獻紀錄片《大魯藝》是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發表70周年而制作的,其選材、立意都非常官方。但是總導演閆東所帶領的團隊,完全放棄了盛行一時的話說體紀錄片制作模式,采用口述的方式進行創作,開創了中國歷史文獻紀錄片創作的新風氣。在這部口述體的文獻紀錄片中,攝制者采訪拍攝了80多位與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有關的老人,如賀敬之、于敏、于藍、黎昕等。歷史中的著名人物,從歷史中走出來,坐在鏡頭面前,向觀眾娓娓道來過往的故事,以其細節與情感吸引觀眾。影片的結構雖然基本是按照時間順序,圍繞魯藝的發展歷程展開,但在整體架構之下,每個人都通過口述補充歷史細節,在相互佐證的言語中完成了作品的影像架構。這種視角在當時的紀錄片創作領域應該說是很有特色的。閆東團隊的其他作品也有很多采取這樣的口述方式,像關注偉人題材的紀錄片《百年小平》《楊尚昆》等。此外,欄目紀錄片《口述》中有一集《紅墻記憶——身邊人眼中的開國領袖》也是這樣,不再采用以往影像資料匯編的匯編體作為常用策略,而是采訪與偉人有關的當 事人,在這些當事人的回憶中建構起偉人的形象。私人化的回憶使歷史在這些作品中是私人化的,使歷史偉人也具有了親切的一面。
三、口述體紀錄片文獻的當代性
除了關注歷史,口述體紀錄片還關注當下題材,呈現口述文獻獨特的“當代性”。這種文獻的當代性體現在口述體欄目紀錄片上,與經典的藝術紀錄片不同,欄目紀錄片主要在電視媒體播放,其在創作周期、選材方法上都有自己獨特的要求,尤其是在選材上要與觀眾親近,內容要具有延續性,以便欄目化操作。當代人、當下社會成為欄目紀錄片的重要關注對象,其口述文獻的使用也就具有了當代性。口述體也因其可以欄目化運作的特征,成為電視紀錄片欄目比較常用的敘事策略。
由央視社會專題部推出的口述體紀錄片欄目《講述》定位于展示當下百姓生活、時代變遷,每一期走進鏡頭進行講述的都是一些普通人,他們的故事也就更具有當代性。比如,《講述》在2016年五一勞動節期間播出的“建設者”系列,其中幾期作品關注的便是普通的工程建設者。他們中有中國一建成都高科技電子廠房的建設工程師、上海洋山港的工程師、海南瓊中抽水蓄能電站的建設者、平潭海峽公路鐵路兩用大橋的建設者,以及滬昆高鐵云南、貴州段的建設者等。中國當代的工程奇跡,由他們來講述再合適不過了,節目也因此樹立了中國當代工程建設者的人物群像。
北京雷禾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制作并在國內多個電視媒體播放的紀錄片欄目《口述》,也有很多題材是關注當下生活的。在最近兩年的節目中,中國沙畫藝術的開創者蘇大寶,著名科幻作家劉念慈,配音演員季冠霖(《羋月傳》中羋月的配音),《仙劍奇俠傳》的開發制作者姚壯憲等人紛紛走進電視屏幕,向觀眾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應該說這些被采訪者都在自己的領域做出了獨特成就,但從著書立說的角度來說,現在還不到為他們立傳的時候。口述體紀錄片對他們的關注則將他們的影像和故事用自我言說的形式記載下來,發揮了文獻獨特的當代性特征。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口述體紀錄片中,口述者所講述的歷史事件,在經歷一段時間之后,因講述者所具有的新的背景,被賦予了某種獨特的當代性。2010年上映的電影《海上傳奇》用口述的形式向我們講述了關于上海這個城市與生活在其中的人的點點滴滴。作為國內不太多見的在院線上映的電影紀錄片,導演賈樟柯主要采用口述的形式建構這部電影的視覺形象。全片共采訪了18位與上海有關的人物,其中有杜月笙的女兒杜美如,曾國藩的曾外孫女張心漪,以及黃埔名將王仲廉之子電影導演王童。在電影中他們都回憶自己祖輩的往事,這些口述資料以獨特的見證者身份進行了歷史揭秘,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但同時,他們所談論的話題長久以來在大陸屬于敏感話題,《海上傳奇》能夠收錄他們的口述并公映,不得不說是受當代的政策與兩岸關系的影響。站在當下口述過去,歷史鮮活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其意義不言而喻。口述文獻也在跨越時間中獲得了歷史性與當代性相生的特征。
鳳凰衛視播出的《口述歷史》欄目,關注的對象往往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與重大事件。欄目制作的模式往往是由某一個獨特的講述者引起,建構起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系。《口述歷史》欄目在2006年1月24日播出了一集《榮毅仁與榮氏家族百年傳奇》。該集的口述者是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兒子榮智健先生,節目內容是榮智健先生對榮毅仁以及榮氏家族的回憶。但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榮毅仁先生是于2005年10月26日去世的,出鏡的榮智健胸前還戴著白花。由此可以看出這集節目的制作契機,其中人物的評論意義不言而喻。在對過去的講述中建構起人物的當代意義,這種口述文獻的當代性極具特色。
口述這種形式在當代紀錄片創作中不再僅僅是一種素材來源,它可以成為一種敘事的策略,乃至一種紀錄片的理念。口述體紀錄片的文獻性,與口述這種形式、紀錄片這種藝術的文獻性特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種類型與形式的高度契合,使口述體紀錄片成為最能體現紀錄片文獻性的一類。口述文獻的私人化和當代性特征也給我們呈現了獨特的口述體視覺影像,私人化使紀錄片呈現的歷史是充滿細節的;當代性一方面使紀錄片更多地關注當代人的生活,為未來留下影像資料,另一方面,也在歷史與現在的二元維度中,因其講述者是在當代,而被歷史文獻賦予當代意義。
[1]閆東. 口述體文獻紀錄片的再探索與思考[J]. 現代傳播,2012(7):77.
[2]張宗偉. 新歷史主義思潮與當代中國文獻紀錄片的敘事策略[J]. 藝術評論,2007 (12).
[3]保爾·湯普遜. 過去的聲音——口述史[M].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