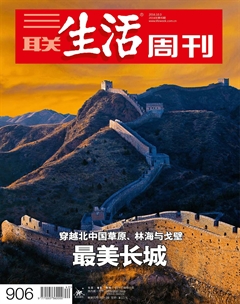煤價上漲與去產能的反復
謝九
被視為嚴重產能過剩的煤炭行業,近期價格突然出現快速上漲,為“去產能”之路帶來新的挑戰。
最近兩個多月以來,煤炭價格強勢反彈,不同品種的煤炭漲價幅度大概在20%至40%之間,蕭條已久的煤炭行業再度出現了“煤難求”“船等煤”等昔日的盛世景象。煤炭價格的意外上漲,也使得下游鋼鐵行業再度面臨虧損的壓力,中鋼協不得不向發改委呼吁增加煤炭供應,以保障鋼鐵企業正常生產。
這一輪煤炭價格上漲的導火索主要因為去產能所致。作為去產能的重點對象,煤炭行業在今年上半年的去產能計劃完成得并不理想,今年上半年全國煤炭退出產能7227萬噸,僅完成全年2.5億噸目標任務的29%。7月份,發改委要求:“各地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有關決策部署,倒排任務量、倒排時間表,確保11月底基本完成任務;中央企業和地方大型國有企業要發揮表率作用,力爭11月上旬完成任務。”在硬性指標面前,下半年以來煤炭去產能加速推進,7月底,煤炭退出產能距離全面目標完成了38%,到了8月底去產能已經完成了80%。
隨著煤炭產能急劇萎縮,市場的供需矛盾開始顯現出來。上半年,全國煤炭消費量同比減少9750萬噸,降幅為5.1%。盡管煤炭需求下降,但是煤炭產量下降更甚,上半年同比減少1.7億噸,降幅9.7%,產量降幅明顯高于需求降幅。進入下半年以來,煤炭行業去產能提速,供需矛盾更加緊張,因此導致最近兩個月以來煤炭價格快速上漲,國內煉焦煤主要煤種每噸上漲100至150元,漲幅超過20%,進口煤漲價更是驚人,澳大利亞煉焦煤較今年6月初上漲超過80%。
面對煤炭價格的快速反彈,首先坐不住的是下游的鋼鐵行業。2015年,國內主要鋼鐵公司虧損600多億元,進入2016年之后,由于煤炭價格下跌帶來成本下降,加之房地產和基建的投資對需求的拉動,今年上半年鋼鐵行業實現126億元的盈利。不過隨著下半年煤價大幅上漲,很多鋼鐵公司再度進入盈虧邊緣。如果煤價延續反彈的勢頭,下半年鋼鐵行業可能會再度陷入集體虧損之中。壓力之下,中鋼協向發改委呼吁增加煤炭供應。
9月8日,國家發改委召集神華、中煤、同煤、陜煤等24家煤炭企業召開“穩定煤炭供應,抑制煤價過快上漲預案啟動會議”,主要思路是通過釋放煤炭先進產能來解決當前的供需矛盾。這次會議選定了74處煤礦為首批先進產能,參加調節市場供應任務。具體辦法包括“當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達到460元、480元、500元且連續兩周上漲時,這些先進產能可以對應日均增產20萬噸、30萬噸、50萬噸”等等。
由于當前煤炭行業的主旋律仍是去產能,所以發改委此次釋放先進產能的做法也顯得頗為謹慎,比如市場原本預期可能會放開煤炭企業工作日的限制,允許先進產能的工作日從276個工作日調整為330個工作日,不過發改委對此并未完全放開,顯示出在去產能的主旋律之下,即使面對煤炭價格反彈的壓力,管理層也依然擔心產能過剩卷土重來,只能在去產能和控價格的雙重目標之間謹慎微調。
不僅是煤炭行業的去產能之路走得艱苦反復,此次面對煤炭漲價而叫苦不迭的鋼鐵行業,更是去產能的頭等大戶,其去產能之路更加曲折。由于國內鋼鐵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已經對國際鋼鐵市場產生了強烈沖擊,鋼鐵業的產能過剩更是在近年升級為國際問題。今年5月中旬,歐洲議會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理由就是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尤其是中國的鋼鐵產能過剩和對歐洲的廉價出口,為歐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及環境后果。今年6月份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國鋼鐵產能過剩成為雙方爭論的焦點問題,在此之前,人民幣匯率一直是這個舞臺的主角。
今年二季度以來,由于美聯儲加息預期下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反彈,國內鋼鐵價格也隨之走高,鋼鐵企業出現了近10年來最好的盈利水平。大量鋼鐵廠家迅速復產,4月份的國內鋼鐵日均產量甚至達到了歷史新高。按照預定的去產能計劃,2016年壓減粗鋼產能目標為4500萬噸,但今年前7個月去產能僅完成全年任務的47%,與此同時,大量鋼鐵企業在利潤誘惑下偷偷復產,使得去產能之路陷入了市場和行政指令的兩難之間。鋼鐵和煤炭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國是鋼鐵的凈出口國,去年中國的鋼材出口量同比增長20%,達到了1.12億噸,創下歷史新高,占去年全球鋼材出口的一半,正因為如此,國內鋼鐵的產能過剩才成為全球性問題,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而我國煤炭行業還是凈進口的地位,因此,相比之下,煤炭行業的產能過剩更多只是內部問題,并沒有引發國際關注,這一次煤炭價格上漲,首先做出強烈反應的也正是國內的鋼鐵行業。
煤炭和鋼鐵行業去產能之路的艱難和反復,也顯示出依靠行政指令和市場調節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當前學術界的一大爭論熱點,近期國內經濟學家張維迎和林毅夫就政府是否應該制定產業政策展開論戰,當前去產能的現實遭遇其實很能說明問題。
今年6月份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國財長雅各布·盧認為中國的鋼鐵過剩問題對全球市場造成了扭曲和破壞,而中國財長樓繼偉回應稱:“中國已不是中央計劃經濟,無法向企業下達去產能的量化目標。”雖然政府并沒有直接向具體企業下達去產能的量化目標,但是上升到各個行業,還是有非常具體的去產能指令,比如鋼鐵行業的去產能目標是,今年壓減粗鋼產能4500萬噸,從2016年開始,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煤炭行業2016年的去產能目標是2.5億噸。
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人為制定的具體去產能數字如何能夠確保其科學性和準確性?如張維迎所言:“由于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是注定要失敗的。所以,政府不要實行產業政策。”雖然去產能這一大目標毫無疑問是當前中國經濟亟需解決的問題,但是具體到如何去產能,以及如何制定合理的去產能目標,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實踐驗證;尤其是政府和市場之手各自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可能也是去產能需要反思的問題。
從目前來看,去產能過程中政府之手扮演的角色還是遠遠大于市場之手,這就使得無論是鋼鐵、煤炭還是其他行業,去產能之路總是需要政策事后的修修補補。比如今年下半年煤炭去產能提速過快,結果導致供需在短時間內失衡,造成煤價強烈反彈,于是政策制定者又開始釋放先進產能,而且對于不同的情形下釋放多少產能都有詳盡規定,但這未必能夠適合當前市場的供需,一旦將來市場供需再度失衡,相關人士可能不得不對政策細節再打補丁,如此和市場反復博弈,大多數時候政策只能跟隨在市場后面。
這一輪煤價上漲動了鋼鐵的奶酪,因此鋼鐵企業齊聲呼吁煤炭擴產,下一次鋼鐵漲價如果又觸動下游行業的利益,也不排除會有相關利益方呼吁鋼鐵復產。作為供給側改革的第一大任務,去產能之路可能會陷入循環反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