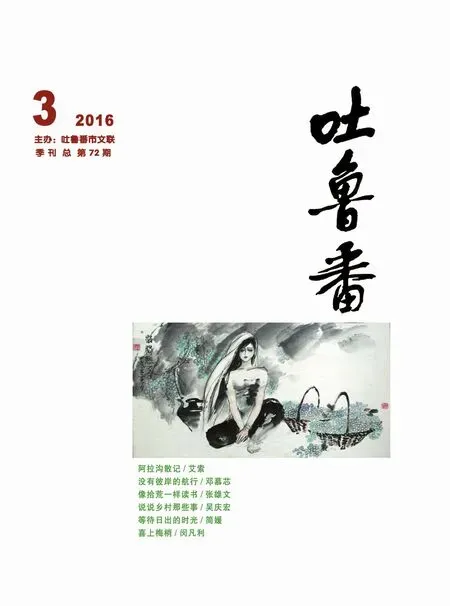父親節的追憶
朱大珪
父親節的追憶
朱大珪

父親不僅是一個家的脊梁,也是對兒女們最初的心中偶像。父愛是那嬌艷花朵下的花托,不求任何回報;父愛是那明亮星星下的夜空,不求任何索求;父愛是那翠綠小樹下的沃土,不求任何盈利。想想孩童時在爸爸懷里撒嬌;想想上學時父親的叮嚀;想想長大后父親為了我們向別人點頭哈腰,你體會過父親的艱辛嗎?歲月在悄悄流逝,轉眼間父親已老。多年前你騎在父親背上逛街玩耍,多年后你會扶著父親走過斑馬線嗎?
為了紀念父親節,筆者采訪了幾位朋友。他們分別向我敘述了自己與父親之間的故事,我在這里略加整理用化名傳播出來,讓我們共同分享吧!
父愛如山
沒事時,我總愛向著營房對面的那座大山靜靜地望著,總感覺那山有種讓人讀不盡的魅力,總感覺山就是一種胸懷,一種性情,一種精神。
我父親就是一位像山一樣的老農民,一輩子在那個山溝里幾乎是沒挪出過一步,他年輕時考上大學,卻因為成分是富農而只能與鋤頭犁耙做伴一生。所以他把他畢生的精力都傾注在了兒子身上。在我們那個村莊那時連村長都還未訂報紙時,父親不僅為我取了學名叫郭光明,還為我訂了《中國少年報》等好幾種報刊,當時家里窮,父親竟下決心戒掉了有十年歷史的煙和酒,把節省下的錢為我買書和訂報紙。
小學時,我家離學校有好幾公里路遠,路上有河有山,我們那個地方又經常下著綿綿雨,在我的記憶中,我的小學都是在父親背上度過的。一到下雨天父親擔心我在路上不安全,總是雷打不動地背著我到學校。整整六年時間一次也沒落下過,哪怕是他重病纏身。
由于高中時的貪玩,我沒能完成父親的夙愿考上大學。當我向父親提出要當兵時,只記得他拍著我的肩語重心長地說:“明兒,你現在也懂點事了,你喜歡什么家里不攔你,只希望你能爭氣就行了……”
自從穿上軍裝,我剛開始還能主動地把部隊的生活與學習情況向父親作詳細的匯報,幾乎兩三天就寫一封信。可到后來,發現自己幾乎是半年沒給父親寫過一封信了,而自己也總能找出一個個不寫信的理由。但父親每月總會雷打不動地給我打電話,每次一接電話當我問父親有什么事的時候,他總是嘿嘿地笑著,然后用那蒼老的聲音說道:“其實也沒什么事,只是想聽聽你的聲音。”這就是我小時候牽著衣襟才不哭不鬧、睡覺也要他抱著睡的父親,現在竟對兒子這般依戀!
在我心中,父親是個最寡言少語的人,而每次一打來電話,他的話都出奇地多,有時竟能一口氣說上半個小時,什么新疆的天氣冷了啊,要多加衣服,什么晚上寫稿要多喝水少抽煙啊,什么天氣冷鞋墊最好墊上兩雙啊……聽我媽媽說,自從我當兵后,不喜歡看電視的父親一有空就守著天氣預報看新疆天氣和收看央視七套的軍事節目。
當兵三年,我竟連父親一面也未曾見過,但他那句句關切與勉勵的話語總會時時回蕩在我的耳畔,有時旁邊沒人時我就會習慣地把父親的照片拿出來看上一會兒。是的,在這個苦累緊張多于輕松悠閑的軍營里,父親的一句句話語,一遍遍叮囑就像串糖葫蘆的竹簽,貫穿于我整個軍旅生活的酸甜苦辣。
父愛如鞭,時時總在催著我、趕著我,使我不得停息;父愛深沉,如山那樣厚重踏實,如山那樣綿延亙久,時時給我力量,給我勇氣!
父親的健身操
父親不懂養生,但他卻知道健身,他常對我說,活動,活動,要想活就得動。一個“動”字,使他身體越來越強壯,一個“動”字,讓他活到今天88歲的高齡。
其實,我所知道的年輕時的父親,身體并不好,父親說他不知什么原因從小就有一個氣管炎的病根,一到冬天就“抱蹲”,什么事也干不了,整天彎著腰蜷在炕上咳嗽不止。父親參加工作后,愣是用他自己創造的或者說是在實踐中摸索出的一套健身方法,制服了這個病根,并且長壽至今。
父親的健身方式主要是騎自行車,工作單位無論遠近,他從不坐車,自行車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我記憶中的父親換過四五輛自行車,都是騎壞的。父親騎自行車的技術很高明,自行車的后座上馱著我,另一只手能再扶一輛自行車一起向前騎,就像演雜技一樣。
父親壯年后的健康身體還得益于籃球,那時父親是籃球場上的活躍分子,每天打完球后大汗淋漓。父親還愿意打撲克,經常與我們在一起打得“面紅耳赤”。
父親說,喝酒也是健身,可以活躍血脈。父親雖然天天喝酒,卻只是每天晚上喝一次,早晨和中午不喝。父親說早上喝酒一天醉,父親是很少喝醉酒的。我記憶中的父親只有一次喝醉了,那時我還很小,父親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來家里做客,年輕氣盛的父親被客人逼到了“懸崖上”才喝多的。喝多酒的父親像得了一場大病。從那里天起父親說,再喝醉就改姓。并把我的原名“長久”改為“求實”。此后我發現酒桌上的父親只要說喝好了,就是天王老子勸也沒用。因此我沒見父親再喝高過,父親也就始終沒有改姓。
父親的身體一直很瘦,一米七五的身高只有110多斤。身體硬朗的父親對飲食特別注意,從來不暴飲暴食,每頓飯吃到七分飽,就是再好吃的飯菜也不再動筷了。
一年冬天,七十多歲的父親在路上不慎滑倒,骨骰頭摔裂,在醫院治療了半個多月,在大腿上打了六根鐵釘。當時我們兄妹都說,這回父親怕是再也不能走路了。誰知,從來不服軟的父親,硬是靠倔強的性格和頑強的毅力,重新站立了起來,后來竟扔掉了拐杖。盡管走起路來有點跛。
一次,我的繼母有事不在家,晚上我陪父親睡覺。第二天早上六點多鐘,我就被一種“啪啪”的聲音吵醒。起來一看,是父親在健身。父親健身結束后,我問父親這是什么操?父親說,他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四五十分鐘,一直做到身上排出些許汗液為止。由于在室內做,方便,經濟,又不受任何條件限制。
父親做操時非常認真,敲打身體的各個部位時非常用力,而且每個環節都認真地做到位,從不馬虎。父親說,退休后從未間斷。
哦,我恍然大悟,父親晚年的健康體魄原來來自于他自創的健身操啊!
我從父親那里學會了這種健身操,也天天練了起來。向父親學習,一輩子都有學不完的知識。我要把父親的健身養生操傳承下去。
清明,我為父親點支煙
父親生前是個地地道道的莊稼漢。打我記事起就已經抽煙了,一天中除了睡覺吃飯,只要有空閑免不了要叼上一支煙。
父親是知道吸煙有害的,這也只是他不讓我抽煙的理由。記得我剛上學那會兒,也許是年幼好奇的緣故吧,我拿了父親的半支煙和幾個小伙伴鉆到村頭的拱橋下模仿著大人的模樣抽了起來,可能是臨走時忘了熄滅留下的煙頭,最后,河畔的那個草垛讓我們幾個小伢崽燒了個精光。父親知道這事后狠狠地揍了我一頓,并罰我跪了一晚的搓衣板。從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香煙沾上一點兒邊了。
后來,我接到了南方一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是一切都得自費,為此不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積蓄,而且還欠下了一些債務。從此,父親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瀟灑地到村頭小店去買煙了。不過,父親倒也有他自己的辦法。每天黃昏時分,他便到田間去采集枯萎的向日葵葉子,回家暴曬后去掉莖絡、揉碎,再研磨成細末,然后用我廢棄的舊課本裁成紙條包卷起來,煙癮來犯時就抽上幾口。父親常常被嗆得連連咳嗽,可他卻依然裝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
大學畢業后,我應聘進了城里的一家國有企業。當我領到第一個月的薪水時,我就毫不猶豫地給父親買了一條帶過濾嘴的“紅塔山”。當然,那煙父親平常是舍不得抽的,除非家中來了客人,即便如此他還得再三聲明是兒子買的,言語中充滿自豪。后來,因為工作關系,我被單位派駐到上海辦事處,于是也就難得回家一趟了。忽然一天,我接到了母親的電話,她說父親病危要我立即趕回家,其實她早就想通知我了,只不過是父親怕影響到我的工作,總是不讓。當我匆匆推開家門的時候,父親已經去了,煙灰缸里還殘留著一根父親抽了一半的煙頭……我的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
而今,轉眼又是多年過去了,每次清明回鄉,我總要走到父親的墳前默默地替他點上一支香煙,任萬般思緒在煙霧氤氳中隨風飄向遠方……
封面國畫作者簡介:

劉玉社,生于1954年6月,河北人,現為中藝財富畫院畫家、新疆兵團美協副主席、中國美協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揚州大學兼職教授、新疆兵團新疆大山水畫研究會會長、石河子大學新疆大山水畫創作研究所所長、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客座教授。其著作的多篇美術理論文章在《光明日報》《中國藝術報》《國畫家》等刊物發表,創作的如《一路好風光》等國畫作品被多家專業機構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