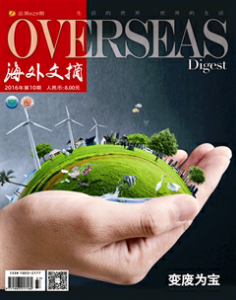冰雪民族
亞歷山大·秋科斯基
在俄羅斯的極寒之地泰梅爾半島上生活著“冰雪民族”——恩加納桑人、多爾甘人、涅涅茨人和埃文基人。他們世代生活在冰封雪蓋的白色荒漠地帶,在連飛鳥經過也不會過久停留的環境中生存繁衍。
北極地區生活著數百萬人,其中北極土著民族人口數量相對較少,但地理分布非常廣闊,大多數起源于中亞,足跡散布在西伯利亞、歐洲、北美洲等地,分屬于前蘇聯、美國、加拿大和丹麥等國家,其中一半以上在前蘇聯境內。

每處恩加納桑人定居地都有縫紉店,婦女們在那兒用馴鹿皮制作地毯和服飾。
每個北極土著民族的語言各不相同,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首先在外貌上,他們都具有蒙古人種的典型外表特征;其次,各土著民族在文化上也大致相同。他們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也有明顯的共同之處。如西伯利亞部落民族和愛斯基摩人、印第安人的雪靴很相似;在宗教上,普遍信奉薩滿教。在漫長的幾千年里,北極土著民族幾乎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空間,極少與外界接觸,保持了新石器時代人類生活方式的許多特征。
北極土著民族是地球上生活條件最艱苦的民族。氣候寒冷、物資匱乏、食物短缺時刻威脅著他們的生命。冬季氣溫最低零下四五十攝氏度,夏天最高溫度通常不超過10攝氏度。進入現代文明社會前,他們穿獸衣,逐獵冰原,過著游獵的生活。但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使他們具備了抗寒、耐饑、承受力強的能力。他們樂觀、安于天命、善良純樸。
恩加納桑人
恩加納桑人是生活在西伯利亞泰梅爾半島凍土地帶的一個古老民族,研究人員稱他們為“人類學上的活化石”。數世紀以來,他們自由馳騁在北極遼闊的冰原上,過著無拘無束的游牧、游獵的原始生活。最早生活在前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的游牧部落,以狩獵、捕魚為生,后來大部分民族轉為放牧馴鹿。但和北極其他土著民族不同,恩加納桑人不靠飼養馴鹿為生,而是以狩獵馴鹿為生。據2010年俄羅斯官方數據統計,恩加納桑族共有862人。恩加納桑語屬烏拉爾語系的薩莫迪語族。

現在北極地區共生活著數百萬人,其中北極土著民族人口數量相對較少,但地理分布非常廣闊。
斯維特拉娜·古麗亞高娃,說唱歌手和泰梅爾半島最后一代巫師。
斯維特拉娜·古麗亞高娃一家都是歌手,盡管他們更喜歡說恩加納桑語,但蘇聯時期,他們只能說俄語。斯維特拉娜小時候,從老家來的親戚經常用恩加納桑語給她講故事或唱歌。
高中畢業后,斯維特拉娜想去外地上大學。當時媽媽擔憂地看著她說:“斯維特拉娜,外面的世界比家里大多了……你爸爸不一定會同意的。”晚上爸爸坐在沙發上邊喝茶邊說:“你打算去外地上學?好,去吧。但是,不要因為適應不了外面的世界偷偷跑回家里。”

在西伯利亞的嚴寒天氣下,保暖是第一要素,因此涅涅茨人的衣服鞋子均是由獸毛皮制成。
終于,斯維特拉娜去諾里爾斯克讀了音樂學院。那里有一個已經有16年歷史的民間藝術團,經常在莫斯科、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和圣彼得堡等地巡演。她第一次上電視表演后,父親打電話激動地說:“我很為我的女兒感到自豪!”
恩加納桑人的圖騰是熊,他們認為熊總能帶給他們好運。斯維特拉娜剛去諾里爾斯克上音樂學院的時候,還不是很適應城市生活,還夢到過熊,后來便好運連連,開始不斷有機會登臺演出。
盡管斯維特拉娜生活在定居點,但也會經常回凍原看看。不久前她剛從杜金卡的冰雪小村回來,和她兒時的伙伴一起回去的。近6年,她共回去4次,并盡量用恩加納桑語和當地人交流。
當我問她有沒有想過搬到像莫斯科或圣彼得堡這樣的大城市生活時,她說更喜歡生活在貼近自然的冰雪地帶。
如今的恩加納桑人已經不再像從前一樣養鹿,最后一批鹿在80年代就被殺光了。可能也正是從那時起他們逐漸開始丟掉自己民族的語言的吧,但他們也一直在努力保留傳統文化。

涅涅茨人的生活和馴鹿息息相關,新生嬰兒出生后首先接觸的就是接生婆給裹上的鹿皮,而人死之后也同樣是用鹿皮包裹。
以前恩加納桑人的主要食物來源靠狩獵野生馴鹿,捕獵黑雁、雷鳥和魚。泰梅爾半島的特色是出產凍魚和大馬哈魚。到了夏季,還有美味的漿果和蘑菇。從80年代起,他們就開始過定居生活。在每處恩加納桑人的定居點都有縫紉店,婦女們在那兒用馴鹿皮制作地毯和服飾,用馴鹿腿部的皮制成靴子,還要在靴子前裝飾上彩珠。恩加納桑人通過出售皮貨,用掙來的錢在定居點的商店里買一些糖、面粉和蔬菜等本地不出產的食物。
斯維特拉娜自己生活在極寒之地,但不想干涉孩子未來的選擇。她說想把所有最美好的事物留給孩子,他們要接受教育,也要學自己民族的語言。她愿意和孩子們一起學習本民族文化。“他們可以自己選擇想走的路,畢竟我也不清楚5年甚至10年后會發生什么。或許,我們會搬走,去我丈夫的故鄉生活,那里也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寒冷地帶,那里的老人都不會說俄語,他們保留了自己的語言。孩子們也從小都說本族語言。” 斯維特拉娜說。斯維特拉娜更擔心的是,會講恩加納桑語的人越來越少,這種語言恐怕有一天會消失。孩子們在學校里和其他不同民族的學生一起上學,因此在學校里說的和老師教的都是俄語。她非常贊賞那些鼓勵孩子們練習母語的老師。極少數家庭選擇搬離定居點回歸到凍原過傳統生活,這也讓他們看到了傳統語言和文化可以傳承下去的希望。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能注重稀有語言的發展,讓我們的下一代不是通過聽錄音來學習自己民族的語言。

北極土著民族都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種的外貌特征。
涅涅茨人
涅涅茨人大概有4.5萬人,其中4.4萬人生活在俄羅斯境內,主要分布在秋明州、阿爾漢格爾斯克州、涅涅茨自治州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州。他們一年近300天生活在冰雪之中。涅涅茨語屬烏拉爾語系的薩莫迪語族薩莫迪諸語言,有兩種方言:凍原涅涅茨語和森林涅涅茨語。
洛薩·雅普杜,新聞記者,在“諾里爾斯克”廣播電視公司工作。
洛薩的曾祖父曾經養了許多鹿。以前鹿在他們這里就是全部:既能做衣服,又能當交通工具。洛薩家有6口人,有3個姐妹和一個兄弟,大多數都生活在凍原,一個在城里的姐姐是畜牧專家。洛薩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手工女式包。這里的女孩從很小的時候就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包,雖然那時只裝用布、鳥啄、木頭和鹿角做的玩具,但她們從小就學會成為‘女主人了。所有涅涅茨女性都有這樣的包,每天出門都要隨身攜帶。在她們的包里能找到針、線、頂針和火柴等。此外,這種包有神圣的意義——像避邪物一樣,驅趕不好的東西。洛薩還特地在她的包上加了鈴鐺,在里面縫上了貂皮——他們認為貂是一種神圣的動物。
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天氣下,保暖是最重要的,因此涅涅茨人的衣服鞋子都是由鹿的毛皮制成的。在當地,可以看到幾乎所有涅涅茨人都穿著鹿皮大衣,戴著毛帽,所穿褲子和鞋子里面都布滿了濃密的鹿毛。他們的生活也和鹿息息相關,孩子一出生就會被裹上鹿皮,人死之后也用鹿皮包裹。涅涅茨人以父系為宗,并有共同墓地和祭祀場以及氏族標記,還明確規定氏族內部禁止通婚。
洛薩保留了許多自己民族特有的老物件,她想以后傳給孩子。也多虧了這些老物件,孩子們才能了解他們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例如,一根看似普通的木棍,能讓孩子們學會搭帳篷的傳統方法。
洛薩一家人現在仍然住帳篷,而不是現代房子,因為她的父輩們不習慣住其他建筑。生活在凍原的其他年輕人已經開始搭建有梁的房子,但大多數涅涅茨年輕人還是喜歡住帳篷。帳篷是人類發明的最獨一無二的住所。我們生活在現代文明社會,很難再對帳篷感興趣,但對生活在凍原的土著民族來說,這就是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洛薩現在已經52歲了,經歷過還沒通電的時代,當時他們的帳篷里只放一盞煤油燈供全家人照明。直到1979年他們才有了電視,現在也有了發電機、電燈和電話等現代設備。
當我問到他們為什么仍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時,洛薩說:“因為這是我們的特色。我們是冰雪民族,這是屬于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后也不會改變。”
涅涅茨孩子會在寄宿學校中度過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因為他們的家人要帶著自己的馴鹿群四處遷徙。一旦這些孩子接受完教育,并能熟練地使用涅涅茨語和俄語,他們就必須作出一個選擇:回歸他們的游牧傳統,或是融入俄羅斯的主流生活。
像大多數涅涅茨孩子一樣,洛薩十四五歲時才第一次接觸到城鎮生活。當時她的學校所在的村子發生了火災,孩子們搬到了鎮里學習,在那里洛薩參加了民族樂團,學習跳舞和唱歌。后來她們去杜金卡演出,她第一次見到了其他冰雪民族——恩加納桑人。高中畢業后,洛薩考上了克麥羅沃人文大學,但由于害怕孤身一人去大城市生活,就回家鄉找了份工作。但一年后,她打算重新考大學,可是沒等考上就嫁人了,生了兩個孩子,從此生活重心又轉移到了家庭和孩子身上。
盡管洛薩還想回到原始凍土帶生活,但條件不允許,父母總對她說:“你一定要學習,考上大學。” 洛薩的父親是文盲,母親算半個文盲,對他們來說,她繼續深造才是最重要的。
洛薩經歷了3段婚姻,長子是混血,他外表上好像與洛薩屬于完全不同的民族,但在精神上仍是涅涅茨人。因為他是洛薩的父母帶大的。當年她一個人生活得很艱難,父母經常把孩子帶到凍土帶生活。
盡管現在洛薩的孩子們都不會說涅涅茨語了,但他們都能聽懂。洛薩那些生活在凍土地帶的兄弟姐妹仍說涅涅茨語,他們的孩子也是。洛薩的兄弟姐妹都還是以傳統方式生活,像18-19世紀時那樣,他們也有了相機、電話、視頻設備和蜂窩通信,但這些對他們來說并不是必需品。
埃文基人
西伯利亞地區有3.7萬埃文基人,生活在雅庫特、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布里亞特共和國、 外貝加爾邊疆區和阿穆爾州。還有3.9萬埃文基人生活在中國和蒙古。僅20%的埃文基人會講本族語言。北部埃文基人曾以漁獵、馴鹿、毛皮和養殖為主,并有石墨、煤炭等采礦業,而南部埃文基人有加工業和制造業。
塔基亞娜·柏麗娜-烏佳秋爾,太梅爾地區唯一一位埃文基語專家,中學兼幼兒園教師,作家。
蘇聯時期,埃文基人甚至被認為不是泰米爾土著民族。但實際上,公元2世紀他們就生活在這里了,歷史也有記載恩加納桑人曾與帶紋身的通古斯人作戰,而埃文基人更早就在臉上刺花紋了。埃文基人是游牧民族,塔基亞娜也不習慣在一個地方待太久,所以即便他們現在不再游牧,她也要經常出去度假。通古斯人稱埃文基人為‘泰加林里的茨岡人,因為他們都喜歡游牧生活。
埃文基民族分布在如此廣袤的土地上,但還有統一的民族語言。在中國和蒙古生活著近3000埃文基人。俯瞰俄羅斯東部地區,埃文基人幾乎無處不在,雖然他們都是以很小的群體聚集。最有意思的是,其實塔基亞娜小時候并不會說埃文基語,她的父母年輕時在機關部門工作,父親當年是集體農莊的主席兼獸醫,經常和鎮上的人打交道,都用俄語和他們交流。
塔基亞娜的父母懂自己民族的語言,他們倆對話都用埃文基語,只有塔基亞娜說俄語。后來塔基亞娜去了伊加爾卡上學,她的老師是伊爾庫茨克埃文基人,曾批評她不會說自己民族的語言,讓她感到非常羞愧。耳濡目染了40年后,塔基亞娜終于無師自通,學會了埃文基語,現在還可以用埃文基語寫文章。“現在掌握這種語言的人越來越少了。我的奶奶已經81歲了,叔父也已經75歲,還有兩個祖母也都年紀很大了,掌握這種語言的人都已經老了。而且純正的埃文基人越來越少,這種語言正在消失。”
年輕人都不會埃文基語,但他們也在試圖拯救這種文化。語言的生存能力水平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可能很快就消失的語言的評估。根據這種分類,埃文基語、恩加納桑語和森林涅涅茨語的生存已經受到嚴重威脅。
埃文基絕大多數人的名字都和動物有關。塔基亞娜曾經有位老師叫“小崽兒”。在這里,以前孩子出生后,都要起一個不好聽的綽號,避免被野獸和鬼神抓走。父母會專門起各種各樣的動物小崽的名字。
塔基亞娜小時候眼睛特別圓,父親叫她“大眼睛”。她的祖父叫“野鹿”,她也是很久之后才明白為什么這么叫。她的祖父年輕時又英俊又高挑,經常穿著白色鹿皮和白靴,非常受女孩歡迎,因此叫“野鹿”。
多爾甘人
多爾甘人人口7885人,由埃文基人和突厥語族的雅庫特人融合而成,實際上是一支說雅庫特語的突厥語民族。
妮娜·古里亞科娃,民間藝術部門和泰米爾房屋民俗志部負責人。
妮娜大學畢業后,被派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的師范學院教多爾甘語言文學。但事實上,那里并沒有多少人學習這種語言,她才意識到或許泰梅爾半島更需要她,便辭職回家了。1989年《泰梅爾報》恰巧需要多爾甘語翻譯兼記者,并推出了一個新的項目:首次開通泰梅爾的民族語言專用通道。妮娜確定這份工作很適合她。她還記得她寫的第一篇文章叫《我的家鄉》。妮娜的家鄉在哈坦加灣海岸最北端的村莊,現在那里大概只有500人生活,是光禿禿的凍土帶,低矮的白樺樹在那里就算最高的植物了。后來妮娜還歌頌了家鄉的漁民和馴鹿牧民。
妮娜現在和家人交流都說多爾甘語。多爾甘語在放牧馴鹿的地方保留得更好。
妮娜的家鄉在凍土帶,以前她上學要去很遠的地方,靠近雅庫特,只能假期回家。上學第一天,妮娜第一次看到了比低矮的白樺樹高的樹,知道了森林的概念。妮娜的家鄉小村幾乎是附近唯一一個有居民的地方,那里有許多會說多爾甘語的孩子。
多爾甘人是世界上唯一以在雪橇滑木上搭建可移動的小木屋為家的民族。這種小木屋可以用皮帶套在鹿身上,由鹿拉著移動,可供3至4人居住,屋內可放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還可以放一張小桌子和一個爐子。不過生火的木材是個大問題,凍土帶不產木材,要從很遠的地方運來。因此,每到冬季,他們就不得不從北邊凍土帶的開闊地,轉移到南邊針葉林附近扎營度冬,對他們來說,這“附近”兩字卻并非一般人頭腦中的概念,可能意味著七八個小時鹿拉雪橇的路程。
當然,多爾甘人對這一切,無論是不時肆虐的暴風雪,還是零下50多度的酷寒,打小就司空見慣了。就拿如廁來說吧,廁所間設在小木屋旁,也是用木板搭蓋在滑木上的,糞坑挖在廁所間下的雪地上,寒風依然可以直接灌進廁所內,去上廁所時你得“全副武裝”,穿上厚重的袍子,戴上毛皮帽和手套,一樣也不能少。解手的動作還得非常麻利,否則私處難免會凍傷。
每間小木屋旁都有一個堆滿冰塊的雪橇,這些冰是備作飲用水和盥洗用水的。一雪橇的冰塊可以用上3天,這些冰塊必須省著用,因為用完了以后得到很遠的干凈湖泊取來補充,路上來回要6個小時。
當我問她后來是否重回過原始凍土地帶時,她開心地回憶道:“2012年,我們組了一個民俗探險隊,拜訪了兩個至今仍保留多爾甘語的原始村落。牧民特地烤了新鮮的面包,燉了鹿肉招待我的同伴,味道好極了,這些食物可以讓人感覺到體內熱氣升騰,不再害怕寒冷。”
[編譯自俄羅斯《薛定諤的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