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事件與語言事件
蘇豐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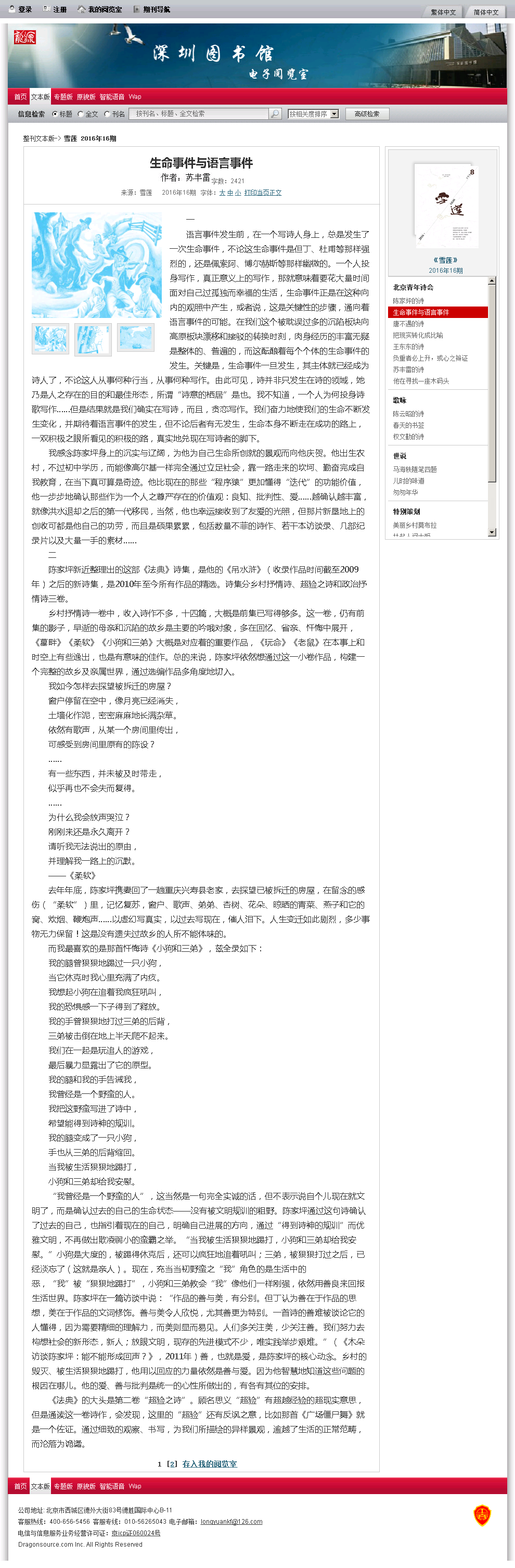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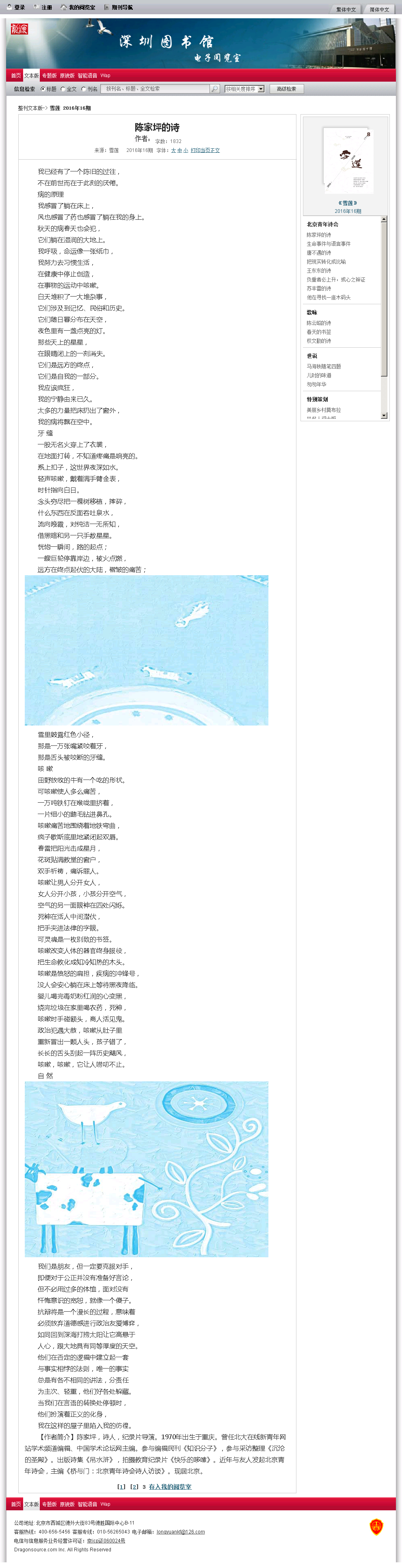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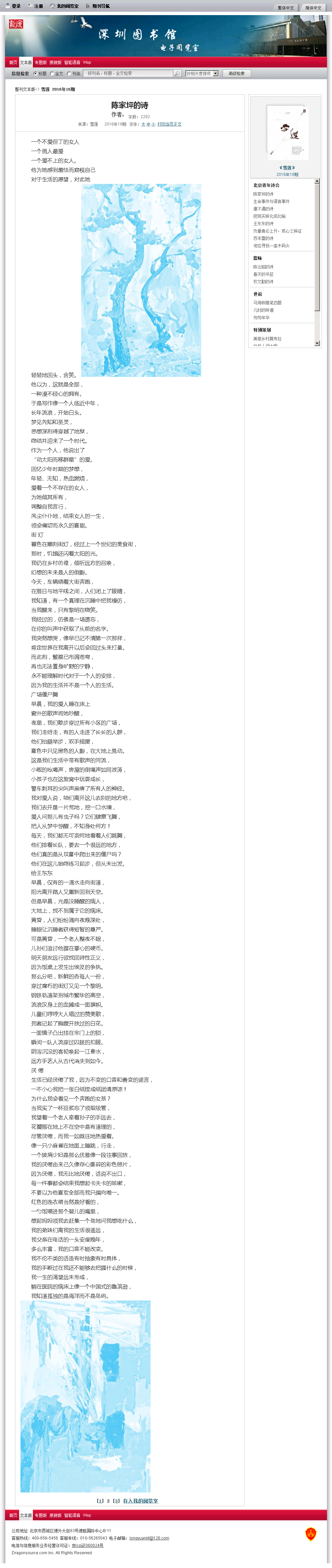
一
語言事件發生前,在一個寫詩人身上,總是發生了一次生命事件,不論這生命事件是但丁、杜甫等那樣強烈的,還是佩索阿、博爾赫斯等那樣幽微的。一個人投身寫作,真正意義上的寫作,那就意味著要花大量時間面對自己過孤獨而幸福的生活,生命事件正是在這種向內的觀照中產生,或者說,這是關鍵性的步驟,通向著語言事件的可能。在我們這個被耽誤過多的沉陷板塊向高原板塊漂移和接駁的轉換時刻,肉身經歷的豐富無疑是整體的、普遍的,而這醞釀著每個個體的生命事件的發生。關鍵是,生命事件一旦發生,其主體就已經成為詩人了,不論這人從事何種行當,從事何種寫作。由此可見,詩并非只發生在詩的領域,她乃是人之存在的目的和最佳形態,所謂“詩意的棲居”是也。我不知道,一個人為何投身詩歌寫作……但是結果就是我們確實在寫詩,而且,貪戀寫作。我們奮力地使我們的生命不斷發生變化,并期待著語言事件的發生,但不論后者有無發生,生命本身不斷走在成功的路上,一雙積極之眼所看見的積極的路,真實地兌現在寫詩者的腳下。
我感念陳家坪身上的沉實與遼闊,為他為自己生命所創就的景觀而向他慶賀。他出生農村,不過初中學歷,而能像高爾基一樣完全通過立足社會,靠一路走來的坎坷、勤奮完成自我教育,在當下真可算是奇跡。他比現在的那些“程序猿”更加懂得“迭代”的功能價值,他一步步地確認那些作為一個人之尊嚴存在的價值觀:良知、批判性、愛……越確認越豐富,就像洪水退卻之后的第一代移民,當然,他也幸運接收到了友愛的光照,但那片新墾地上的創收可都是他自己的功勞,而且是碩果累累,包括數量不菲的詩作、若干本訪談錄、幾部紀錄片以及大量一手的素材……
二
陳家坪新近整理出的這部《法典》詩集,是他的《吊水滸》(收錄作品時間截至2009年)之后的新詩集,是2010年至今所有作品的精選。詩集分鄉村抒情詩、超驗之詩和政治抒情詩三卷。
鄉村抒情詩一卷中,收入詩作不多,十四篇,大概是前集已寫得夠多。這一卷,仍有前集的影子,早逝的母親和沉陷的故鄉是主要的吟哦對象,多在回憶、省親、懺悔中展開,《墓畔》《柔軟》《小狗和三弟》大概是對應著的重要作品,《玩命》《老鼠》在本事上和時空上有些逸出,也是有意味的佳作。總的來說,陳家坪依然想通過這一小卷作品,構建一個完整的故鄉及親屬世界,通過選編作品多角度地切入。
我如今怎樣去探望被拆遷的房屋?
窗戶停留在空中,像月亮已經消失,
土墻化作泥,密密麻麻地長滿雜草。
依然有歌聲,從某一個房間里傳出,
可感受到房間里原有的陳設?
……
有一些東西,并未被及時帶走,
似乎再也不會失而復得。
……
為什么我會放聲哭泣?
剛剛來還是永久離開?
請聽我無法說出的原由,
并理解我一路上的沉默。
——《柔軟》
去年年底,陳家坪攜妻回了一趟重慶興壽縣老家,去探望已被拆遷的房屋,在留念的感傷(“柔軟”)里,記憶復蘇,窗戶、歌聲、弟弟、杏樹、花朵、晾曬的青菜、燕子和它的窩、炊煙、鞭炮聲……以虛幻寫真實,以過去寫現在,催人淚下。人生變遷如此劇烈,多少事物無力保留!這是沒有遺失過故鄉的人所不能體味的。
而我最喜歡的是那首懺悔詩《小狗和三弟》,茲全錄如下:
我的腿曾狠狠地踢過一只小狗,
當它休克時我心里充滿了內疚。
我想起小狗在追著我瘋狂吼叫,
我的恐懼感一下子得到了釋放。
我的手曾狠狠地打過三弟的后背,
三弟被擊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
我們在一起是玩追人的游戲,
最后暴力顯露出了它的原型。
我的腿和我的手告誡我,
我曾經是一個野蠻的人。
我把這野蠻寫進了詩中,
希望能得到詩神的規訓。
我的腿變成了一只小狗,
手也從三弟的后背縮回。
當我被生活狠狠地踢打,
小狗和三弟卻給我安慰。
“我曾經是一個野蠻的人”,這當然是一句完全實誠的話,但不表示說自個兒現在就文明了,而是確認過去的自己的生命狀態——沒有被文明規訓的粗野。陳家坪通過這句詩確認了過去的自己,也指引著現在的自己,明確自己進展的方向,通過“得到詩神的規訓”而優雅文明,不再做出欺凌弱小的蠻霸之舉。“當我被生活狠狠地踢打,小狗和三弟卻給我安慰。”小狗是大度的,被踢得休克后,還可以瘋狂地追著吼叫;三弟,被狠狠打過之后,已經淡忘了(這就是親人)。現在,充當當初野蠻之“我”角色的是生活中的惡,“我”被“狠狠地踢打”,小狗和三弟教會“我”像他們一樣剛強,依然用善良來回報生活世界。陳家坪在一篇訪談中說:“作品的善與美,有分別。但丁認為善在于作品的思想,美在于作品的文詞修飾。善與美令人欣悅,尤其善更為特別。一首詩的善難被談論它的人懂得,因為需要精細的理解力,而美則顯而易見。人們多關注美,少關注善。我們努力去構想社會的新形態,新人;放眼文明,現存的先進模式不少,唯實踐舉步艱難。”(《木朵訪談陳家坪:能不能形成回聲?》,2011年)善,也就是愛,是陳家坪的核心動念。鄉村的毀滅、被生活狠狠地踢打,他用以回應的力量依然是善與愛。因為他智慧地知道這些問題的根因在哪兒。他的愛、善與批判是統一的心性所做出的,有各有其位的安排。
《法典》的大頭是第二卷“超驗之詩”。顧名思義“超驗”有超越經驗的超現實意思,但是通讀這一卷詩作,會發現,這里的“超驗”還有反諷之意,比如那首《廣場僵尸舞》就是一個佐證。通過細致的觀察、書寫,為我們所描繪的異樣景觀,逾越了生活的正常范疇,而淪落為詭譎。
一個不愛但丁的女人
一個男人最愛
一個愛不上的女人。
他為她感到羞怯而窺視自己
對于生活的愿望,對此她
輕輕地回頭,含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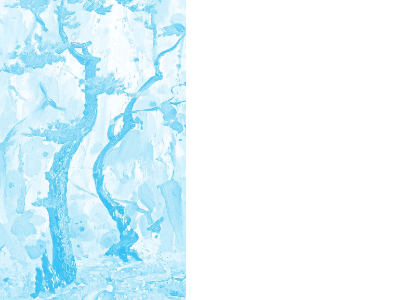
他以為,這就是全部,
一種漫不經心的擁有。
于是寫作像一個人臨近中年,
長年流浪,開始白頭。
夢見先知和圣靈,
思想深刻得穿越了地獄,
終結并迎來了一個時代。
作為一個人,他說出了
“動太陽而移群星”的愛。
回憶少年時期的夢想,
年輕、無知,熱血燃燒,
愛著一個不存在的女人,
為她傾其所有,
調整自我言行,
風塵仆仆地,結束女人的一生,
領會痛切而永久的喜劇。
街 燈
暮色在雕刻街燈,經過上一個世紀的美食街,
那時,饑餓還閃著太陽的光。
我仍在鄉村彷徨,傾聽遠方的召喚,
幻想的未來是人的倒影。
今天,車輛繞著大街奔跑,
在落日與地平線之間,人們閉上了眼睛,
我知道,有一個真理在沉睡中把我模仿,
當我醒來,只有黎明在微笑。
我經過的,仿佛是一場遺忘,
在你的叫聲中獲取了從前的名字。
我突然想哭,像早已記不清第一次那樣,
肯定世界在我離開以后會回過頭來打量。
而此刻,繁星已布滿蒼穹,
再也無法置身曠野的寧靜,
永不能理解時代對于一個人的安排,
因為我的生活并不是一個人的生活。
廣場僵尸舞
早晨,我的愛人睡在床上
窗外的歌聲將她吵醒,
夜里,我們散步穿過所有小區的廣場,
我們走呀走,有的人走進了長長的人群,
他們抬腿舉步,雙手搖擺,
幕色中只見黑色的人影,在大地上晃動。
這是我們生活中帶有歌聲的河流,
小販的吆喝聲,房屋的倒塌聲如同波濤,
小孩子也在這旋窩中玩耍成長,
警車刺耳的尖叫聲麻痹了所有人的神經。
我對愛人說,咱們離開這兒去別的地方吧,
我們去開墾一片荒地,挖一囗水塘,
愛人問那兒有蟲子嗎?它們肆意飛舞,
把人從夢中驚醒,不知身處何方!
每天,我們都無可奈何地看著人們跳舞,
他們排著長隊,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他們真的是從墳墓中爬出來的僵尸嗎?
他們在這兒始終練習起步,但從未出發。
給王東東
早晨,僅有的一滴水走向街道,
陽光離開路人又重新回到天空。
但是早晨,光是沒睡醒的病人,
大地上,找不到屬于它的病床。
黃昏,人們紛紛涌向夜晚深處,
睡眠讓沉睡者獲得短暫的尊嚴。
可是黃昏,一個老人整夜不眠,
兒孫們追討他握在掌心的硬幣。
明天朋友遠行欲找回詩性正義,
因為飯桌上發生出埃及的爭執。
那么分吧,新鮮的杏每人一份,
穿過腐朽的街燈又見一個黎明。
鋼鐵軌道架到城市繁華的高空,
流浪漢身上的血攤成一面旗幟。
兒童們哼哼大人唱過的贊美歌,
死者記起了胸膛開放過的白花。
一面鏡子凸出掛在牢門上的鎖,
瞬間一隊人流穿過囚服的扣眼。
陰溝沉沒的客輪喚起一江春水,
遠方手藝人從古代消失到如今。
厭 倦
生活已經厭倦了我,因為不變的口音和善變的諾言,
一不小心我把一張白紙捏成紙團請原諒!
為什么我會看見一個奔跑的女孩?
當我買了一杯豆漿忘了領取吸管,
我望著一個老人牽著孫子的手遠去,
花瓣落在地上不在空中是有道理的,
盡管厭倦,而我一如既往地熱愛著。
像一只小麻雀在地面上蹦跳,行走,
一個披肩少婦是那么優雅像一段往事回放,
我的厭倦由來己久像存心撕碎的彩色照片,
因為厭倦,我無比地厭倦,話說不出口,
每一件事都會結束我想起卡夫卡的咳嗽,
不要以為他喜歡全部而我只偏向唯一。
紅色的連衣裙當然是好看的,
一勺飯喂進那個嬰兒的嘴里,
想起媽媽領我去趕集一個勁地問我想吃什么,
我的弟妹們離我的生活很遙遠,
我父親在電話的一頭安度晚年,
多么豐富,我的口音不能改變。
我不倫不類的話語有時抽象有時具體,
我的手斷過在我還不能夠去把握什么的時候,
我一生的渴望遠未形成,
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像一個中國式的魯濱遜,
我知道孤獨的是海洋而不是島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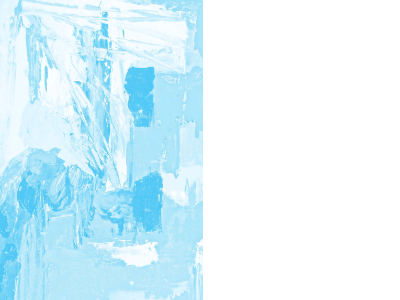
我已經有了一個陳舊的過往,
不在前世而在于此刻的厭倦。
病的原理
我感冒了躺在床上,
風也感冒了藥也感冒了躺在我的身上。
秋天的病春天也會犯,
它們躺在濕潤的大地上。
我呼吸,命運像一張紙巾,
我努力去習慣生活,
在健康中停止創造,
在事物的運動中咳嗽。
白天堆積了一大堆雜事,
它們涉及到記憶、民俗和歷史。
它們隨日暮分布在天空,
夜色里有一盞點亮的燈。
那些天上的星星,
在眼睛閉上的一刻消失。
它們是遠方的終點,
它們是自我的一部分。
我應該瘋狂,
我的寧靜由來已久。
太多的力量把床扔出了窗外,
我的病將飄在空中。
牙 縫
一股無名火穿上了衣裳,
在地面打轉,不知道疼痛是響亮的。
系上扣子,這世界夜深如水。
輕聲咳嗽,戴著滿手臂金表,
時針指向白日。
念頭窮盡把一棵樹移植,摔碎,
什么東西在反面吞吐泉水,
流向晚霞,對純潔一無所知,
借黑暗和另一只手數星星。
恍惚一瞬間,路的起點;
一艘巨輪停靠岸邊,被火點燃,
遠方在終點起伏的大陸,褶皺的痛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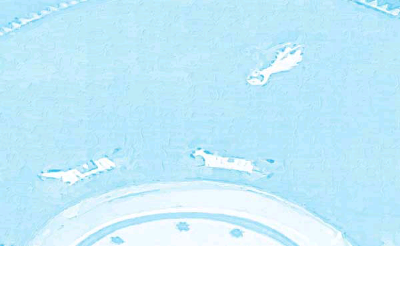
雪里皴露紅色小徑,
那是一萬張嘴緊咬著牙,
那是舌頭被咬斷的牙縫。
咳 嗽
田野放牧的牛有一個吃的形狀。
可咳嗽使人多么痛苦,
一萬噸鐵釘在喉嚨里擠著,
一片細小的鵝毛鉆進鼻孔。
咳嗽痛苦地圍繞著地鐵彎曲,
瘋子歇斯底里地緊閉起雙唇。
春雷把陽光擊成星月,
花斑貼滿教堂的窗戶,
雙手祈禱,痛訴罪人。
咳嗽讓男人分開女人,
女人分開小孩,小孩分開空氣,
空氣的另一面眼神在四處閃爍。
死神在活人中間潛伏,
把手夾進法律的字眼。
可靈魂是一枚別致的書簽。
咳嗽改變人體的器官終身服役,
把生命教化成知冷知熱的木頭。
咳嗽是憤怒的扁擔,疾病的沖鋒號,
沒人會安心躺在床上等待黑夜降臨。
嬰兒喝完毒奶粉紅潤的心變黑,
燒完垃圾在家里喝農藥,死神,
咳嗽時手碰額頭,商人活見鬼。
政治犯遇大赦,咳嗽從肚子里
重新冒出一顆人頭,孩子錯了,
長長的舌頭刮起一陣歷史颶風,
咳嗽,咳嗽,它讓人嘮叨不止。
自 然
我們是朋友,但一定要克服對手,
即便對于公正并沒有準備好言論,
但不必用過多的體恤,面對沒有
懺悔意識的寬恕,就像一個傻子。
抗辯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意味著
必須放棄道德感進行政治友愛博弈,
如同回到深海打撈太陽讓它高懸于
人心,跟大地具有同等厚度的天空。
他們在否定的邏輯中建立起一套
與事實相悖的法則,唯一的事實
總是有各不相同的講法,分責任
為主次、輕重,他們好各處躲藏。
當我們在言語的轉換處停頓時,
他們扮演著正義的化身,
我在這樣的屋子里陷入我的彷徨。
【作者簡介】陳家坪,詩人,紀錄片導演。1970年出生于重慶。曾任北大在線新青年網站學術頻道編輯、中國學術論壇網主編。參與編輯民刊《知識分子》,參與采訪整理《沉淪的圣殿》。出版詩集《吊水滸》,拍攝教育紀錄片《快樂的哆嗦》。近年與友人發起北京青年詩會,主編《橋與門:北京青年詩會詩人訪談》。現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