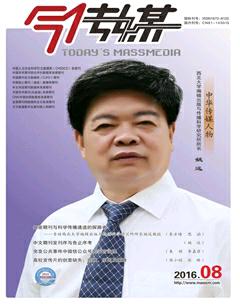自媒體時(shí)代生活意義的建構(gòu)
梁強(qiáng)
摘 要:自媒體時(shí)代是一個(gè)以個(gè)人傳播為主的時(shí)代,在這個(gè)時(shí)代,每個(gè)人都可以變身為媒體元,發(fā)布分享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所感之事,本文以人們?cè)诘湫偷淖悦襟w形式——微信“朋友圈”中的活動(dòng)為切入點(diǎn),思考自媒體對(duì)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進(jìn)而探討生活意義的建構(gòu)問題。
關(guān)鍵詞:自媒體時(shí)代;虛實(shí)交疊;分享情懷;人際互動(dòng);生活意義
中圖分類號(hào):G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2-8122(2016)08-0019-03
當(dāng)下很多學(xué)者都在研究分析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化可能引發(fā)的深刻變遷,認(rèn)為這是人類社會(huì)即將經(jīng)歷的一次重大轉(zhuǎn)型。隨著媒介技術(shù)的空前發(fā)展,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也在不斷革新,如今自媒體時(shí)代已全面來(lái)臨,依托于新媒介技術(shù)出現(xiàn)的微信業(yè)已成為社交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新寵。微信給不同層次不同年齡的人帶來(lái)了愉快的互動(dòng)體驗(yàn),充實(shí)了人們的閑暇時(shí)光。其中影響最為顯著的當(dāng)數(shù)微信的“朋友圈”功能,“朋友圈”已成為多數(shù)人發(fā)布和接收消息的重要渠道。人們從面對(duì)面的真實(shí)世界進(jìn)入到這種由網(wǎng)絡(luò)建構(gòu)的虛擬世界中,這一轉(zhuǎn)換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如今人們似乎對(duì)于自媒體的有血有肉更為喜聞樂見,本文以“朋友圈”為例,探討在自媒體時(shí)代下個(gè)體如何建構(gòu)生活意義。
一、生活世界的變化
自媒體時(shí)代是一個(gè)人人都能發(fā)聲,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可以變成媒體源的時(shí)代,在這樣一個(gè)時(shí)代,人的生活世界悄然變化。
(一)生活場(chǎng)域的轉(zhuǎn)換
1.從現(xiàn)實(shí)世界到虛擬世界
自從邁進(jìn)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人們的生活場(chǎng)域就隨之發(fā)生了轉(zhuǎn)換,從面對(duì)面的真實(shí)世界進(jìn)入到由網(wǎng)絡(luò)所建構(gòu)的虛擬世界當(dāng)中。自媒體所營(yíng)造的虛擬世界,不同于以往的電子網(wǎng)絡(luò)空間,其虛擬場(chǎng)域和現(xiàn)實(shí)場(chǎng)域具有較高的融合度。比如“朋友圈”,它將現(xiàn)實(shí)中人們的關(guān)系復(fù)制到移動(dòng)網(wǎng)絡(luò)之中,實(shí)現(xiàn)了虛擬世界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對(duì)接,二者相輔相成相互滲透,人們的生活場(chǎng)域被烙上了虛擬和現(xiàn)實(shí)相互交疊的二重性印記。
2.共享空間的延伸
自媒體時(shí)代下,個(gè)體的日常生活正在變成“新聞發(fā)布”[1],一直以來(lái),沉默于私人空間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走出了私人領(lǐng)域,換上了共享性的標(biāo)簽。微信用戶可以通過(guò)“朋友圈”發(fā)布圖文,分享自己的生活動(dòng)態(tài),也可分享文章、視頻、音樂等,構(gòu)筑了一個(gè)全新的共享空間。
3.公共生活的彰顯
自媒體時(shí)代,信息的來(lái)源渠道更加暢通,人們更大程度地進(jìn)入到公共生活領(lǐng)域當(dāng)中。“朋友圈”里,人們分享傳播各種公共性話題以及最新出臺(tái)的各項(xiàng)方針政策,體現(xiàn)了對(duì)公共生活的密切關(guān)注。
(二)互動(dòng)形式的變化
1.跨越時(shí)空限制的特性
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dòng)往往發(fā)生在具體的情境中,具有很強(qiáng)的空間和時(shí)間的實(shí)在性,人們?cè)跁r(shí)空的緊密關(guān)系中把握行動(dòng)。互動(dòng)的主體必須“共時(shí)”且身體“在場(chǎng)”,互動(dòng)者的表情神態(tài)、語(yǔ)言、動(dòng)作以及著裝、打扮等,都可能成為自我表達(dá)情感的重要媒介。而自媒體時(shí)代,基于移動(dòng)網(wǎng)絡(luò)的互動(dòng),主體之間可以脫離時(shí)空的限制,以“共時(shí)”和“異時(shí)”交錯(cuò)身體“缺場(chǎng)”與意識(shí)“在場(chǎng)”的形式來(lái)溝通交流,實(shí)現(xiàn)隨時(shí)隨地的互動(dòng)。這樣的互動(dòng)形態(tài)更大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互動(dòng)的自由。微信用戶在“朋友圈”發(fā)布新鮮事,微信好友點(diǎn)贊、評(píng)論,進(jìn)而展開互動(dòng),這樣的互動(dòng)并不需要互動(dòng)主體“共時(shí)”“共在”。
2.互動(dòng)主體的自由度加深
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每個(gè)行動(dòng)者都會(huì)被打上社會(huì)性的印記,各種各樣的社會(huì)特征會(huì)影響人們之間的互動(dòng)。而在“朋友圈”這種虛擬空間中互動(dòng)時(shí),人們不用太顧忌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各種身份標(biāo)識(shí)所帶來(lái)的各種溝通障礙。微信用戶在“朋友圈”分享信息之后,可以看到這條信息的人關(guān)注的是信息本身或者是該發(fā)布者的情感變化,互動(dòng)雙方會(huì)暫時(shí)忘卻彼此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各種屬性差異所造成的人際溝壑。
3.互動(dòng)內(nèi)容的多元化及互動(dòng)體驗(yàn)的真實(shí)化
交往行動(dòng)者總是在其生活世界內(nèi)行動(dòng),不會(huì)脫離生活情境。人們通過(guò)“朋友圈”分享的內(nèi)容異彩紛呈,這些互動(dòng)內(nèi)容都是依托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朋友圈”并不是基于相同價(jià)值觀念而產(chǎn)生的聚集,其結(jié)構(gòu)成分的多樣性以及他者的不確定性等特征,充實(shí)了自我體驗(yàn)的形式和內(nèi)容,使得人們每天都能接受到不同的觀點(diǎn)和信息。正是這種內(nèi)容的多元化,增加了互動(dòng)的樂趣。圖文并茂、音頻視頻相結(jié)合的表現(xiàn)形式令內(nèi)容更加生動(dòng),可以充分調(diào)動(dòng)人們的感官,使互動(dòng)者的身體也能突破時(shí)空限制,產(chǎn)生“臨場(chǎng)感”,帶來(lái)更加真實(shí)的互動(dòng)體驗(yàn)。
(三)傳統(tǒng)人際關(guān)系的回歸
由網(wǎng)絡(luò)所構(gòu)建的虛擬世界最初是一個(gè)隱匿的世界,以陌生人交往互動(dòng)為主,人們通過(guò)ID進(jìn)場(chǎng),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身份標(biāo)識(shí)在這個(gè)虛擬空間里不復(fù)存在。而自媒體時(shí)代,人們傾向于延續(xù)和維護(hù)熟人關(guān)系。“朋友圈”里主要是“熟人社交”,它是以個(gè)人為中心向外生成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人們將傳統(tǒng)社會(huì)的差序格局整體復(fù)制到這個(gè)社交平臺(tái)中。微信用戶經(jīng)常關(guān)注的是與自己私交甚好的伙伴們?cè)凇芭笥讶Α钡膭?dòng)態(tài),并與其進(jìn)行親昵的互動(dòng)。微信“朋友圈”看似拓寬了人們的交往圈,但實(shí)則親近的依然是少數(shù)人。
(四)情緒分享的發(fā)展
一般來(lái)講,人們進(jìn)行情緒分享是為了從分享對(duì)象的反應(yīng)中獲得親密和支持。進(jìn)入自媒體時(shí)代,情緒分享可以依托于社交媒體,各種各樣由情緒推動(dòng)的分享匯聚在我們的生活當(dāng)中。在自媒體時(shí)代,情緒分享逐漸生成了兩大主題,一是“你在干什么”,二是“剛剛發(fā)生了什么”。自媒體的發(fā)展帶來(lái)了觸控技術(shù)、碎片化表達(dá)和時(shí)間流[2]。觸控技術(shù)令人們只要完成下拉動(dòng)作便可以了解最新訊息,碎片化表達(dá)則是人們趨向于使用簡(jiǎn)略的語(yǔ)言來(lái)傳遞表達(dá)信息,而時(shí)間流則導(dǎo)致新鮮事具有霸權(quán)性,只要有新的狀態(tài),舊的狀態(tài)就會(huì)被覆蓋,最新的東西永遠(yuǎn)在上面,無(wú)形中增強(qiáng)了每個(gè)時(shí)刻的重要性。在時(shí)間流的模式下,為了使碎片化的情緒分享更具吸引力,人們正在變成會(huì)講故事的人。
(五)話語(yǔ)權(quán)的轉(zhuǎn)移
話語(yǔ)權(quán)可以簡(jiǎn)單地理解為話語(yǔ)的影響力,也就是控制輿論的權(quán)力。話語(yǔ)權(quán)由誰(shuí)掌握,決定了社會(huì)輿論的走向[3]。以前,充當(dāng)意見領(lǐng)袖的往往是國(guó)家機(jī)關(guān)或者是權(quán)威機(jī)構(gòu),話語(yǔ)權(quán)主體是上層精英人士。而自媒體的出現(xiàn),沖擊了這種傳播方式,話語(yǔ)權(quán)開始從精英群體向普通大眾轉(zhuǎn)移,個(gè)體在公共空間表達(dá)心聲成為一種常態(tài),其話語(yǔ)權(quán)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強(qiáng)。微信“朋友圈”推動(dòng)了話語(yǔ)權(quán)的平民化,開辟了一個(gè)信息高速交換的平臺(tái),它在社會(huì)熱點(diǎn)和公共話題中的活躍程度已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傳統(tǒng)媒體。
二、個(gè)體生活意義的建構(gòu)
人的存在從來(lái)就不是純粹的存在,它總是牽涉到意義。人所開展的一切生命活動(dòng),都必須建立在把握自身價(jià)值意義的基礎(chǔ)上。生活是尋求意義的生命活動(dòng),過(guò)有意義的生活是人存在的目的。自媒體時(shí)代下,個(gè)體通過(guò)虛實(shí)世界的溝通與協(xié)調(diào)來(lái)記錄自己的生命歷程,在傳統(tǒng)互動(dòng)與新型網(wǎng)絡(luò)互動(dòng)的張力結(jié)構(gòu)中維系人際關(guān)系,在充分流露自我意識(shí)的過(guò)程中兼顧公共生活,實(shí)現(xiàn)共同生存,建構(gòu)生活意義。
(一)虛實(shí)世界的溝通與協(xié)調(diào)
人們的生活場(chǎng)域在當(dāng)下呈現(xiàn)出“虛實(shí)共生”的特征,其生活的真實(shí)世界與虛擬的網(wǎng)絡(luò)情境相融合,人們身處其中建構(gòu)生活意義。人們?cè)凇芭笥讶Α被蛴涗浫粘I睿虮磉_(dá)情感宣泄情緒,或塑造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或分享知識(shí)傳遞快樂,人們所進(jìn)行的這一系列活動(dòng)都是在追尋、建構(gòu)屬于自己的生活意義。
(二)體驗(yàn)全新的互動(dòng)形式
隨著生活場(chǎng)域的轉(zhuǎn)換,互動(dòng)形式也發(fā)生了變化,如前所述,自媒體時(shí)代的互動(dòng)呈現(xiàn)出跨越時(shí)空限制的特性,互動(dòng)主體更加自由,互動(dòng)內(nèi)容更加多元化,人們正在體驗(yàn)這一變化。在“朋友圈”中,所有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附加在人身上的各種社會(huì)屬性基本都被忽略了,人性趨于自然。虛擬情境中的互動(dòng)彌補(bǔ)了現(xiàn)實(shí)互動(dòng)的不足,有助于個(gè)體實(shí)現(xiàn)一定意義上的平等互動(dòng)。
(三)維系人際關(guān)系
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起初是以陌生人互動(dòng)交往為主的,隨著自媒體的發(fā)展,熟人之間在網(wǎng)絡(luò)情境中的互動(dòng)更加頻繁。“朋友圈”所連接的基本是產(chǎn)生于個(gè)人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人際關(guān)系,人們?cè)凇芭笥讶Α敝型ㄟ^(guò)一些共同話題形成交集,有助于拉近現(xiàn)實(shí)中彼此之間的距離。“朋友圈”匯聚了自己的生活記錄和他人的生活動(dòng)態(tài),人們通過(guò)這個(gè)平臺(tái)了解彼此的生活近況,進(jìn)行情感表達(dá),一定程度上維系了人際關(guān)系,有助于建構(gòu)生活意義。
(四)表達(dá)自我與關(guān)注公共生活
自媒體時(shí)代下,為了獲得關(guān)注和認(rèn)可,人們發(fā)布新鮮事時(shí)常常會(huì)仔細(xì)斟酌,預(yù)先估計(jì)自己所講的故事是否具有吸引力,能否引起他人的注意。“朋友圈”擴(kuò)展了人們表達(dá)思想觀點(diǎn)的渠道,使得人們?cè)诔浞直磉_(dá)自我的過(guò)程中獲得存在感。如今自媒體在社會(huì)熱點(diǎn)和公共話題的討論與傳播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充分發(fā)揮其方便快捷的優(yōu)勢(shì),整合人們零散瑣碎的時(shí)間,使得人們只要?jiǎng)觿?dòng)手指就能滿足自己的表達(dá)訴求。“朋友圈”里親朋好友、師長(zhǎng)同學(xué)、同事討論某一熱點(diǎn)話題,交流看法,參與到公共生活當(dāng)中,在公共空間中追尋生命意義。
三、個(gè)體所面臨的意義困境
面對(duì)生活世界的變化,人的存在感不再是確定和唯一的,在建構(gòu)生活意義時(shí)出現(xiàn)了一系列問題。
(一)虛擬導(dǎo)致的虛無(wú)
進(jìn)入自媒體時(shí)代,人們存在的意義和空間、時(shí)間都有所分離,嵌入真實(shí)社會(huì)關(guān)系中的互動(dòng)如今大部分在虛擬世界中開展,人們?cè)谔摂M空間中進(jìn)行角色扮演。但不能忽略的是這種虛擬導(dǎo)致了新的虛無(wú)。
一方面表現(xiàn)在人與人關(guān)系的變化上。“朋友圈”雖然可以將分離兩地的人們的生活展示給對(duì)方,使相隔萬(wàn)里的互動(dòng)成為可能,但它卻消解了傳統(tǒng)情感互動(dòng)的意義。當(dāng)朋友只不過(guò)是一次點(diǎn)擊,那么有些關(guān)系的存在對(duì)人而言就變成了存在著的無(wú)。
另一方面表現(xiàn)在人心靈的空虛。自媒體的發(fā)展,讓世界變成“我”的,也讓“我”的變成世界的,這導(dǎo)致許多人對(duì)虛擬空間中活動(dòng)的關(guān)注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了對(duì)身邊人真實(shí)境況的關(guān)注。人們通過(guò)智能手機(jī)隨時(shí)隨地與自媒體相連接,進(jìn)而觸摸這個(gè)世界,這導(dǎo)致人們總是頻繁地查看手機(jī),一會(huì)兒不看手機(jī),就會(huì)錯(cuò)過(guò)很多新鮮事,仿佛離開手機(jī)就找不到存在感。
(二)在虛擬和現(xiàn)實(shí)的交疊中顯現(xiàn)認(rèn)同危機(jī)
拉扎斯菲爾德認(rèn)為大眾傳媒具有“麻醉作用”,過(guò)度沉溺于媒體提供的表層娛樂和虛擬滿足中,會(huì)逐漸喪失社會(huì)行動(dòng)力[4]。自媒體時(shí)代,加深了人們對(duì)網(wǎng)絡(luò)的依賴程度。人們?cè)凇芭笥讶Α备鶕?jù)自己的主觀意志塑造各種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制造人際關(guān)系活躍的假象。當(dāng)退出虛擬空間,回到現(xiàn)實(shí)世界中時(shí),面對(duì)并沒有因想象而變好的真實(shí)情況,面對(duì)瑣碎的事務(wù),難免會(huì)產(chǎn)生失落感,甚至出現(xiàn)自我認(rèn)同的危機(jī)。虛實(shí)交疊中,人們更容易將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行為帶入到虛擬空間中,如把一些商業(yè)化行為裹挾到自媒體當(dāng)中。“朋友圈”當(dāng)中的集贊換商品、微代購(gòu)等行為,會(huì)增加用戶的不適感,引發(fā)厭惡心理和負(fù)面情緒。這種負(fù)面情緒可能會(huì)延伸到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導(dǎo)致人們對(duì)社會(huì)的信任度下降,出現(xiàn)社會(huì)認(rèn)同的危機(jī)。
(三)理性精神的缺失
自媒體時(shí)代,人們?cè)诔浞窒硎芫W(wǎng)絡(luò)社會(huì)方便、快捷收發(fā)信息的同時(shí),也面臨著理性精神的缺失問題。
1.過(guò)度娛樂化現(xiàn)象。自媒體時(shí)代娛樂化傾向更加明顯,時(shí)至今日已經(jīng)發(fā)展為過(guò)度娛樂化。如“朋友圈”里人為制造的各種笑料、調(diào)侃戲謔、惡搞社會(huì)事件等。起初人們只是單純娛樂,當(dāng)這種趨勢(shì)愈演愈烈時(shí),便形成了一股不良風(fēng)氣。
2.傳播的信息真假難辨。自媒體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的開放性更上一個(gè)臺(tái)階。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接收和發(fā)布信息,使得各類網(wǎng)絡(luò)信息洶涌而至。很多虛假信息經(jīng)過(guò)有心人的包裝,常常令人難辨真假。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朋友圈”有時(shí)會(huì)謠言四起,如一些易造成社會(huì)恐慌、影響社會(huì)公共秩序的虛假消息,違背科學(xué)知識(shí)的信息等。
3.網(wǎng)絡(luò)圍觀和盲目起哄。隨著自媒體的發(fā)展,人們對(duì)這種現(xiàn)象更加習(xí)以為常。面對(duì)各種被曝光的事件,人們?cè)絹?lái)越不去理性思考事件或行為的真實(shí)性,不經(jīng)求證直接轉(zhuǎn)發(fā)評(píng)論進(jìn)行道德審判。這種非理性的舉動(dòng)往往影響了事態(tài)的正常發(fā)展,甚至擴(kuò)大了事態(tài)的嚴(yán)重性。
四、走出意義困境
每一種事物都必然存在漏洞和缺陷,自媒體在高速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滋長(zhǎng)了許多負(fù)面問題,需要調(diào)適以走出意義困境,使人們更好地生活。
首先,訴諸自律,包括三方面:一是自覺到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融合,培養(yǎng)自身的網(wǎng)絡(luò)公共意識(shí)。當(dāng)一個(gè)人變身為媒體元的時(shí)候,事實(shí)上他就與其他人形成了一種共生關(guān)系,那么他就需要有一種責(zé)任意識(shí)來(lái)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時(shí)刻提醒自己,不管生活場(chǎng)域如何轉(zhuǎn)換,始終離不開自我與他者共存這一生活要素。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duì)自我的認(rèn)識(shí),而這種認(rèn)識(shí)主要是通過(guò)與他人的社會(huì)互動(dòng)形成的,他人對(duì)自己的評(píng)價(jià)、態(tài)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鏡子”,自我是在與他人的聯(lián)系中,透過(guò)他人這面“鏡子”來(lái)認(rèn)識(shí)和把握自己的[5]。所以即使是在虛擬情境中,我們也要注意處理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二是關(guān)注人本身,尋找自己是誰(shuí)和能夠是誰(shuí)的答案,拉近心靈之間的距離,關(guān)注生活本身。自媒體仿佛催生了一個(gè)“影子世界”,一旦人們熟悉了“影子世界”并欣然接受它,真實(shí)的世界就可能會(huì)遭到拒絕,所以人們應(yīng)當(dāng)僅把“朋友圈”等社交平臺(tái)當(dāng)做分享傳遞信息、放松身心的地方,堅(jiān)持適度原則,不要給予過(guò)多的關(guān)注,實(shí)現(xiàn)虛實(shí)世界的溝通與協(xié)調(diào),生活的重心應(yīng)該回歸到真實(shí)世界當(dāng)中;三是回歸到現(xiàn)實(shí)的人際交往。在自媒體營(yíng)造的網(wǎng)絡(luò)空間中,活生生的人在交往中退到了終端背后,真實(shí)的自我隱藏在幕后,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只是符號(hào),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互動(dòng)的意義,影響現(xiàn)實(shí)的人際關(guān)系。
自媒體在一定程度上擴(kuò)大了人們的互動(dòng)范圍,增加了人們之間的互動(dòng)頻率,但有時(shí)也使得人際互動(dòng)異化為膚淺的面子上的互動(dòng)。例如“朋友圈”里的點(diǎn)贊行為,使用初期表達(dá)的是一種欣賞和密切關(guān)注,后來(lái)演變成簡(jiǎn)單的回饋和反應(yīng),發(fā)展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敷衍的行為。人們應(yīng)當(dāng)更注重與身邊人面對(duì)面的溝通交流,不再依賴于自媒體制造“臨場(chǎng)感”,去構(gòu)筑和維系真實(shí)的朋友圈。
其次,訴諸他律,包括兩方面:一是政府介入自媒體管理,制定具體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范網(wǎng)絡(luò)自媒體的運(yùn)行,不給各類虛假信息可乘之機(jī);二是塑造公共道德意識(shí),在公共道德意識(shí)的指引下,社會(huì)主體將把生活中的各種規(guī)則和要求當(dāng)作自身必須遵奉的道德要求且能在現(xiàn)實(shí)中自覺自愿的遵守,從而更加理性地建構(gòu)生活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 徐志宏.生活的彰顯或消逝:自媒體生活之遭遇初探[J].教學(xué)與研究.2014(12):32-38.
[2] 知名媒體研究學(xué)者胡泳在題為《媒體與時(shí)間》的演講中提到的觀點(diǎn).
[3] 陳偉球.新媒體時(shí)代話語(yǔ)權(quán)社會(huì)分配的調(diào)整[J].國(guó)際新聞界,2014(5):79-91.
[4] 胡申生,李遠(yuǎn)行,章友德等.傳播社會(huì)學(xué)導(dǎo)論[M].上海:上海大學(xué)出版社,2002.
[5] 郭慶光.傳播學(xué)教程[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1999:82-84.
[責(zé)任編輯: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