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玉龜
楊愛民+胡云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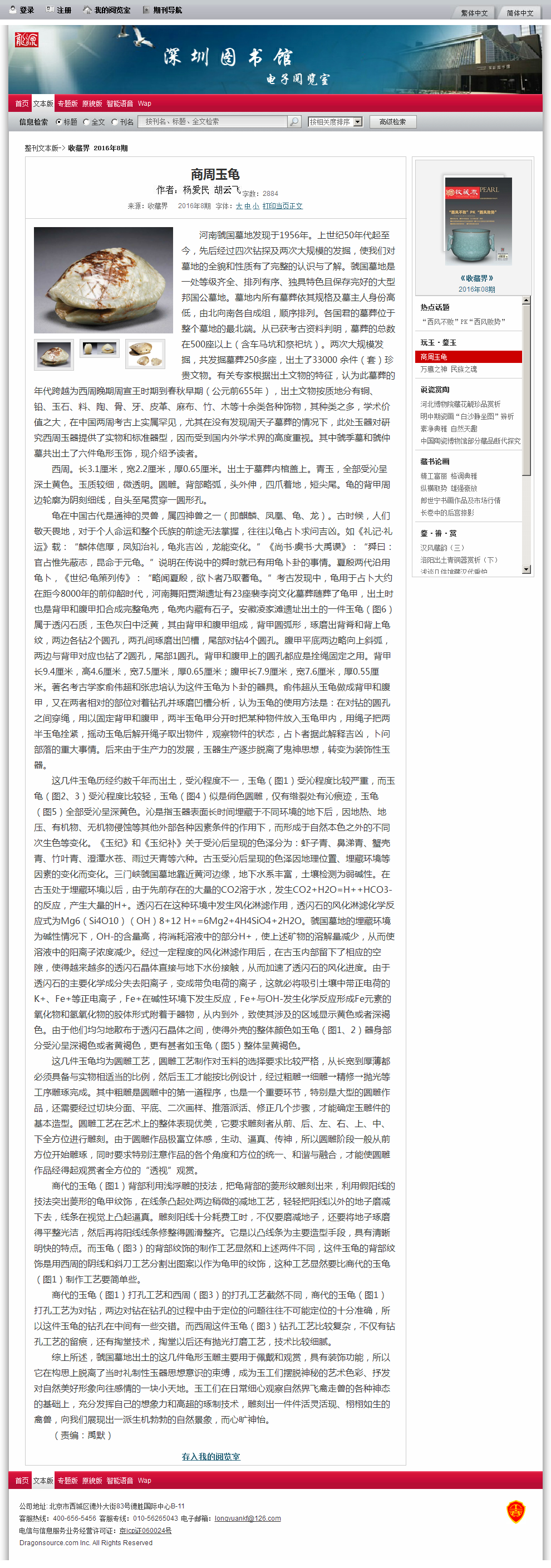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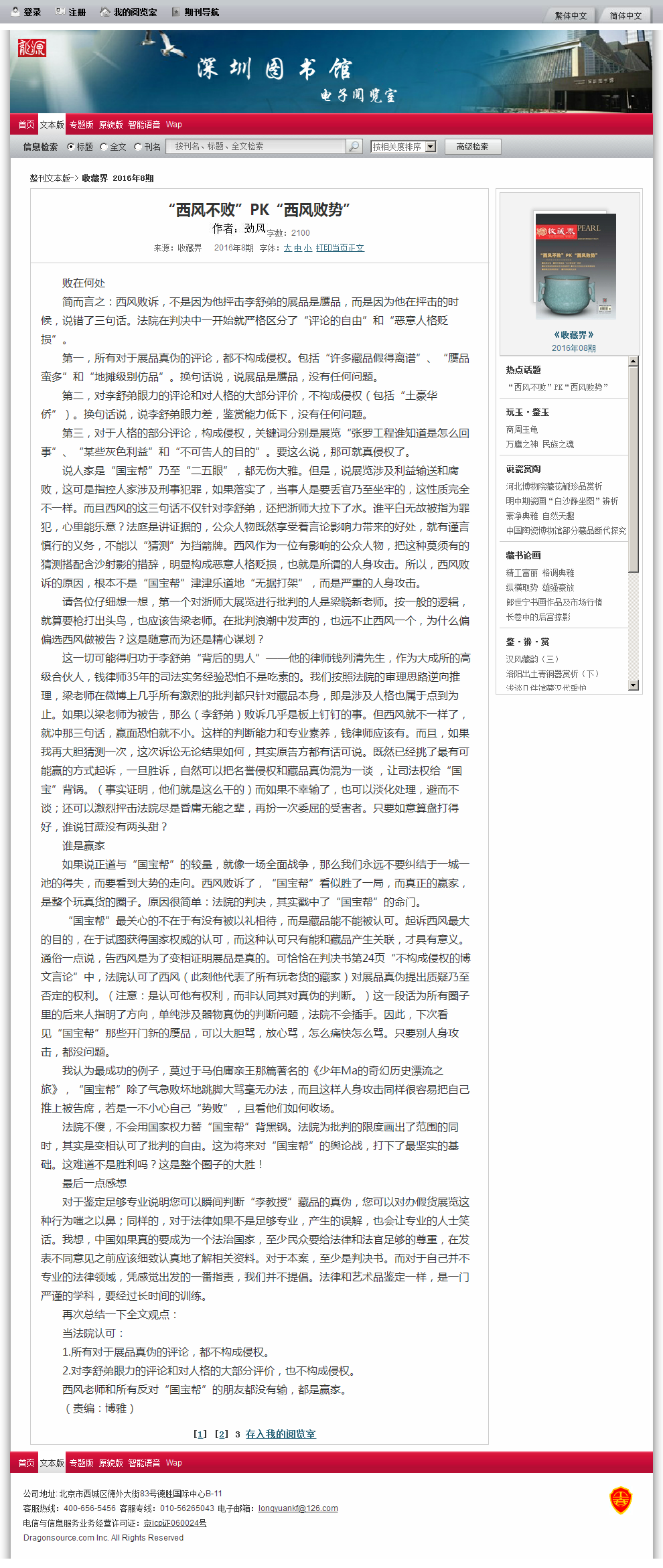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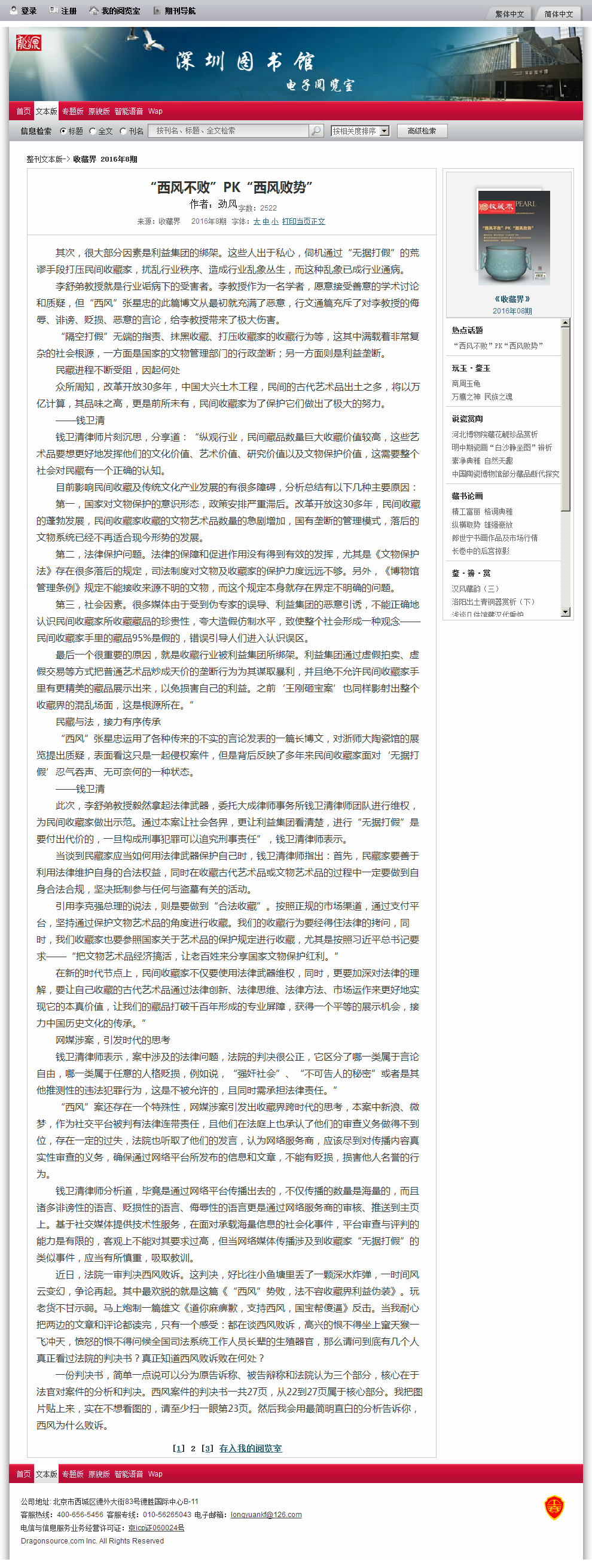
河南虢國墓地發現于1956年。上世紀50年代起至今,先后經過四次鉆探及兩次大規模的發掘,使我們對墓地的全貌和性質有了完整的認識與了解。虢國墓地是一處等級齊全、排列有序、獨具特色且保存完好的大型邦國公墓地。墓地內所有墓葬依其規格及墓主人身份高低,由北向南各自成組,順序排列。各國君的墓葬位于整個墓地的最北端。從已獲考古資料判明,墓葬的總數在500座以上(含車馬坑和祭祀坑)。兩次大規模發掘,共發掘墓葬250多座,出土了33000 余件(套)珍貴文物。有關專家根據出土文物的特征,認為此墓葬的年代跨越為西周晚期周宣王時期到春秋早期(公元前655年),出土文物按質地分有銅、鉛、玉石、料、陶、骨、牙、皮革、麻布、竹、木等十余類各種飾物,其種類之多,學術價值之大,在中國兩周考古上實屬罕見,尤其在沒有發現周天子墓葬的情況下,此處玉器對研究西周玉器提供了實物和標準器型,因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其中虢季墓和虢仲墓共出土了六件龜形玉飾,現介紹予讀者。
西周。長3.1厘米,寬2.2厘米,厚0.65厘米。出土于墓葬內棺蓋上。青玉,全部受沁呈深土黃色。玉質較細,微透明。圓雕。背部略弧,頭外伸,四爪著地,短尖尾。龜的背甲周邊輪廓為陰刻細線,自頭至尾貫穿一圓形孔。
龜在中國古代是通神的靈獸,屬四神獸之一(即麒麟、鳳凰、龜、龍)。古時候,人們敬天畏地,對于個人命運和整個氏族的前途無法掌握,往往以龜占卜求問吉兇。如《禮記·禮運》載:“麟體信厚,鳳知治禮,龜兆吉兇,龍能變化。”《尚書·虞書·大禹謨》:“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說明在傳說中的舜時就已有用龜卜卦的事情。夏殷兩代沿用龜卜,《世紀·龜策列傳》:“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考古發現中,龜用于占卜大約在距今8000年的前仰韶時代,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有23座裴李崗文化墓葬隨葬了龜甲,出土時也是背甲和腹甲扣合成完整龜殼,龜殼內藏有石子。安徽凌家灘遺址出土的一件玉龜(圖6)屬于透閃石質,玉色灰白中泛黃,其由背甲和腹甲組成,背甲圓弧形,琢磨出背脊和背上龜紋,兩邊各鉆2個圓孔,兩孔間琢磨出凹槽,尾部對鉆4個圓孔。腹甲平底兩邊略向上斜弧,兩邊與背甲對應也鉆了2圓孔,尾部1圓孔。背甲和腹甲上的圓孔都應是拴繩固定之用。背甲長9.4厘米,高4.6厘米,寬7.5厘米,厚0.65厘米;腹甲長7.9厘米,寬7.6厘米,厚0.55厘米。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和張忠培認為這件玉龜為卜卦的器具。俞偉超從玉龜做成背甲和腹甲,又在兩者相對的部位對著鉆孔并琢磨凹槽分析,認為玉龜的使用方法是:在對鉆的圓孔之間穿繩,用以固定背甲和腹甲,兩半玉龜甲分開時把某種物件放入玉龜甲內,用繩子把兩半玉龜拴緊,搖動玉龜后解開繩子取出物件,觀察物件的狀態,占卜者據此解釋吉兇,卜問部落的重大事情。后來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玉器生產逐步脫離了鬼神思想,轉變為裝飾性玉器。
這幾件玉龜歷經約數千年而出土,受沁程度不一,玉龜(圖1)受沁程度比較嚴重,而玉龜(圖2、3)受沁程度比較輕,玉龜(圖4)似是俏色圓雕,僅有綹裂處有沁痕跡,玉龜(圖5)全部受沁呈深黃色。沁是指玉器表面長時間埋藏于不同環境的地下后,因地熱、地壓、有機物、無機物侵蝕等其他外部各種因素條件的作用下,而形成于自然本色之外的不同次生色等變化。《玉紀》和《玉紀補》關于受沁后呈現的色澤分為:蝦子青、鼻涕青、蟹殼青、竹葉青、澄潭水蒼、雨過天青等六種。古玉受沁后呈現的色澤因地理位置、埋藏環境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三門峽虢國墓地靠近黃河邊緣,地下水系豐富,土壤檢測為弱堿性。在古玉處于埋藏環境以后,由于先前存在的大量的CO2溶于水,發生CO2+H2O=H++HCO3-的反應,產生大量的H+。透閃石在這種環境中發生風化淋濾作用,透閃石的風化淋濾化學反應式為Mg6(Si4O10)(OH)8+12 H+=6Mg2+4H4SiO4+2H2O。虢國墓地的埋藏環境為堿性情況下,OH-的含量高,將消耗溶液中的部分H+,使上述礦物的溶解量減少,從而使溶液中的陽離子濃度減少。經過一定程度的風化淋濾作用后,在古玉內部留下了相應的空隙,使得越來越多的透閃石晶體直接與地下水份接觸,從而加速了透閃石的風化進度。由于透閃石的主要化學成分失去陽離子,變成帶負電荷的離子,這就必將吸引土壤中帶正電荷的K+、Fe+等正電離子,Fe+在堿性環境下發生反應,Fe+與OH-發生化學反應形成Fe元素的氧化物和氫氧化物的膠體形式附著于器物,從內到外,致使其涉及的區域顯示黃色或者深褐色。由于他們均勻地散布于透閃石晶體之間,使得外殼的整體顏色如玉龜(圖1、2)器身部分受沁呈深褐色或者黃褐色,更有甚者如玉龜(圖5)整體呈黃褐色。
這幾件玉龜均為圓雕工藝,圓雕工藝制作對玉料的選擇要求比較嚴格,從長寬到厚薄都必須具備與實物相適當的比例,然后玉工才能按比例設計,經過粗雕→細雕→精修→拋光等工序雕琢完成。其中粗雕是圓雕中的第一道程序,也是一個重要環節,特別是大型的圓雕作品,還需要經過切塊分面、平底、二次畫樣、推落派活、修正幾個步驟,才能確定玉雕件的基本造型。圓雕工藝在藝術上的整體表現優美,它要求雕刻者從前、后、左、右、上、中、下全方位進行雕刻。由于圓雕作品極富立體感,生動、逼真、傳神,所以圓雕階段一般從前方位開始雕琢,同時要求特別注意作品的各個角度和方位的統一、和諧與融合,才能使圓雕作品經得起觀賞者全方位的“透視”觀賞。
商代的玉龜(圖1)背部利用淺浮雕的技法,把龜背部的菱形紋雕刻出來,利用假陽線的技法突出菱形的龜甲紋飾,在線條凸起處兩邊稍微的減地工藝,輕輕把陽線以外的地子磨減下去,線條在視覺上凸起逼真。雕刻陽線十分耗費工時,不僅要磨減地子,還要將地子琢磨得平整光潔,然后再將陽線線條修整得圓滑整齊。它是以凸線條為主要造型手段,具有清晰明快的特點。而玉龜(圖3)的背部紋飾的制作工藝顯然和上述兩件不同,這件玉龜的背部紋飾是用西周的陰線和斜刀工藝分割出圖案以作為龜甲的紋飾,這種工藝顯然要比商代的玉龜(圖1)制作工藝要簡單些。
商代的玉龜(圖1)打孔工藝和西周(圖3)的打孔工藝截然不同,商代的玉龜(圖1)打孔工藝為對鉆,兩邊對鉆在鉆孔的過程中由于定位的問題往往不可能定位的十分準確,所以這件玉龜的鉆孔在中間有一些交錯。而西周這件玉龜(圖3)鉆孔工藝比較復雜,不僅有鉆孔工藝的留痕,還有掏堂技術,掏堂以后還有拋光打磨工藝,技術比較細膩。
綜上所述,虢國墓地出土的這幾件龜形玉雕主要用于佩戴和觀賞,具有裝飾功能,所以它在構思上脫離了當時禮制性玉器思想意識的束縛,成為玉工們擺脫神秘的藝術色彩、抒發對自然美好形象向往感情的一塊小天地。玉工們在日常細心觀察自然界飛禽走獸的各種神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琢制技術,雕刻出一件件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的禽獸,向我們展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自然景象,而心曠神怡。
(責編:禹默)
其次,很大部分因素是利益集團的綁架。這些人出于私心,伺機通過“無據打假”的荒謬手段打壓民間收藏家,擾亂行業秩序、造成行業亂象叢生,而這種亂象已成行業通病。
李舒弟教授就是行業詬病下的受害者。李教授作為一名學者,愿意接受善意的學術討論和質疑,但“西風”張星忠的此篇博文從最初就充滿了惡意,行文通篇充斥了對李教授的侮辱、誹謗、貶損、惡意的言論,給李教授帶來了極大傷害。
“隔空打假”無端的指責、抹黑收藏、打壓收藏家的收藏行為等,這其中滿載著非常復雜的社會根源,一方面是國家的文物管理部門的行政壟斷;另一方面則是利益壟斷。
民藏進程不斷受阻,因起何處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大興土木工程,民間的古代藝術品出土之多,將以萬億計算,其品味之高,更是前所未有,民間收藏家為了保護它們做出了極大的努力。
——錢衛清
錢衛清律師片刻沉思,分享道:“縱觀行業,民間藏品數量巨大收藏價值較高,這些藝術品要想更好地發揮他們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研究價值以及文物保護價值,這需要整個社會對民藏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目前影響民間收藏及傳統文化產業發展的有很多障礙,分析總結有以下幾種主要原因:
第一,國家對文物保護的意識形態,政策安排嚴重滯后。改革開放這30多年,民間收藏的蓬勃發展,民間收藏家收藏的文物藝術品數量的急劇增加,國有壟斷的管理模式,落后的文物系統已經不再適合現今形勢的發展。
第二,法律保護問題。法律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尤其是《文物保護法》存在很多落后的規定,司法制度對文物及收藏家的保護力度遠遠不夠。另外,《博物館管理條例》規定不能接收來源不明的文物,而這個規定本身就存在界定不明確的問題。
第三,社會因素。很多媒體由于受到偽專家的誤導、利益集團的惡意引誘,不能正確地認識民間收藏家所收藏藏品的珍貴性,夸大造假仿制水平,致使整個社會形成一種觀念——民間收藏家手里的藏品95%是假的,錯誤引導人們進入認識誤區。
最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藏行業被利益集團所綁架。利益集團通過虛假拍賣、虛假交易等方式把普通藝術品炒成天價的壟斷行為為其謀取暴利,并且絕不允許民間收藏家手里有更精美的藏品展示出來,以免損害自己的利益。之前‘王剛砸寶案也同樣影射出整個收藏界的混亂場面,這是根源所在。”
民藏與法,接力有序傳承
“西風”張星忠運用了各種傳來的不實的言論發表的一篇長博文,對浙師大陶瓷館的展覽提出質疑,表面看這只是一起侵權案件,但是背后反映了多年來民間收藏家面對‘無據打假忍氣吞聲、無可奈何的一種狀態。
——錢衛清
此次,李舒弟教授毅然拿起法律武器,委托大成律師事務所錢衛清律師團隊進行維權,為民間收藏家做出示范。通過本案讓社會各界,更讓利益集團看清楚,進行“無據打假”是要付出代價的,一旦構成刑事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責任”,錢衛清律師表示。
當談到民藏家應當如何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時,錢衛清律師指出:首先,民藏家要善于利用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在收藏古代藝術品或文物藝術品的過程中一定要做到自身合法合規,堅決抵制參與任何與盜墓有關的活動。
引用李克強總理的說法,則是要做到“合法收藏”。按照正規的市場渠道,通過支付平臺,堅持通過保護文物藝術品的角度進行收藏。我們的收藏行為要經得住法律的拷問,同時,我們收藏家也要參照國家關于藝術品的保護規定進行收藏,尤其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把文物藝術品經濟搞活,讓老百姓來分享國家文物保護紅利。”
在新的時代節點上,民間收藏家不僅要使用法律武器維權,同時,更要加深對法律的理解,要讓自己收藏的古代藝術品通過法律創新、法律思維、法律方法、市場運作來更好地實現它的本真價值,讓我們的藏品打破千百年形成的專業屏障,獲得一個平等的展示機會,接力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
網媒涉案,引發時代的思考
錢衛清律師表示,案中涉及的法律問題,法院的判決很公正,它區分了哪一類屬于言論自由,哪一類屬于任意的人格貶損,例如說,“強奸社會”、“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是其他推測性的違法犯罪行為,這是不被允許的,且同時需承擔法律責任。”
“西風”案還存在一個特殊性,網媒涉案引發出收藏界跨時代的思考,本案中新浪、微夢,作為社交平臺被判有法律連帶責任,且他們在法庭上也承認了他們的審查義務做得不到位,存在一定的過失,法院也聽取了他們的發言,認為網絡服務商,應該盡到對傳播內容真實性審查的義務,確保通過網絡平臺所發布的信息和文章,不能有貶損,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為。
錢衛清律師分析道,畢竟是通過網絡平臺傳播出去的,不僅傳播的數量是海量的,而且諸多誹謗性的語言、貶損性的語言、侮辱性的語言更是通過網絡服務商的審核、推送到主頁上。基于社交媒體提供技術性服務,在面對承載海量信息的社會化事件,平臺審查與評判的能力是有限的,客觀上不能對其要求過高,但當網絡媒體傳播涉及到收藏家“無據打假”的類似事件,應當有所慎重,吸取教訓。
近日,法院一審判決西風敗訴。這判決,好比往小魚塘里丟了一顆深水炸彈,一時間風云變幻,爭論再起。其中最歡脫的就是這篇《“西風”勢敗,法不容收藏界利益偽裝》。玩老貨不甘示弱。馬上炮制一篇雄文《道你麻痹歉,支持西風,國寶幫傻逼》反擊。當我耐心把兩邊的文章和評論都讀完,只有一個感受:都在談西風敗訴,高興的恨不得坐上竄天猴一飛沖天,憤怒的恨不得問候全國司法系統工作人員長輩的生殖器官,那么請問到底有幾個人真正看過法院的判決書?真正知道西風敗訴敗在何處?
一份判決書,簡單一點說可以分為原告訴稱、被告辯稱和法院認為三個部分,核心在于法官對案件的分析和判決。西風案件的判決書一共27頁,從22到27頁屬于核心部分。我把圖片貼上來,實在不想看圖的,請至少掃一眼第23頁。然后我會用最簡明直白的分析告訴你,西風為什么敗訴。
敗在何處
簡而言之:西風敗訴,不是因為他抨擊李舒弟的展品是贗品,而是因為他在抨擊的時候,說錯了三句話。法院在判決中一開始就嚴格區分了“評論的自由”和“惡意人格貶損”。
第一,所有對于展品真偽的評論,都不構成侵權。包括“許多藏品假得離譜”、“贗品蠻多”和“地攤級別仿品”。換句話說,說展品是贗品,沒有任何問題。
第二,對李舒弟眼力的評論和對人格的大部分評價,不構成侵權(包括“土豪華僑”)。換句話說,說李舒弟眼力差,鑒賞能力低下,沒有任何問題。
第三,對于人格的部分評論,構成侵權,關鍵詞分別是展覽“張羅工程誰知道是怎么回事”、“某些灰色利益”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這么說,那可就真侵權了。
說人家是“國寶幫”乃至“二五眼”,都無傷大雅。但是,說展覽涉及利益輸送和腐敗,這可是指控人家涉及刑事犯罪,如果落實了,當事人是要丟官乃至坐牢的,這性質完全不一樣。而且西風的這三句話不僅針對李舒弟,還把浙師大拉下了水。誰平白無故被指為罪犯,心里能樂意?法庭是講證據的,公眾人物既然享受著言論影響力帶來的好處,就有謹言慎行的義務,不能以“猜測”為擋箭牌。西風作為一位有影響的公眾人物,把這種莫須有的猜測搭配含沙射影的措辭,明顯構成惡意人格貶損,也就是所謂的人身攻擊。所以,西風敗訴的原因,根本不是“國寶幫”津津樂道地“無據打架”,而是嚴重的人身攻擊。
請各位仔細想一想,第一個對浙師大展覽進行批判的人是梁曉新老師。按一般的邏輯,就算要槍打出頭鳥,也應該告梁老師。在批判浪潮中發聲的,也遠不止西風一個,為什么偏偏選西風做被告?這是隨意而為還是精心謀劃?
這一切可能得歸功于李舒弟“背后的男人”——他的律師錢列清先生,作為大成所的高級合伙人,錢律師35年的司法實務經驗恐怕不是吃素的。我們按照法院的審理思路逆向推理,梁老師在微博上幾乎所有激烈的批判都只針對藏品本身,即是涉及人格也屬于點到為止。如果以梁老師為被告,那么(李舒弟)敗訴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但西風就不一樣了,就沖那三句話,贏面恐怕就不小。這樣的判斷能力和專業素養,錢律師應該有。而且,如果我再大膽猜測一次,這次訴訟無論結果如何,其實原告方都有話可說。既然已經挑了最有可能贏的方式起訴,一旦勝訴,自然可以把名譽侵權和藏品真偽混為一談 ,讓司法權給“國寶”背鍋。(事實證明,他們就是這么干的)而如果不幸輸了,也可以淡化處理,避而不談;還可以激烈抨擊法院盡是昏庸無能之輩,再扮一次委屈的受害者。只要如意算盤打得好,誰說甘蔗沒有兩頭甜?
誰是贏家
如果說正道與“國寶幫”的較量,就像一場全面戰爭,那么我們永遠不要糾結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要看到大勢的走向。西風敗訴了,“國寶幫”看似勝了一局,而真正的贏家,是整個玩真貨的圈子。原因很簡單:法院的判決,其實戳中了“國寶幫”的命門。
“國寶幫”最關心的不在于有沒有被以禮相待,而是藏品能不能被認可。起訴西風最大的目的,在于試圖獲得國家權威的認可,而這種認可只有能和藏品產生關聯,才具有意義。通俗一點說,告西風是為了變相證明展品是真的。可恰恰在判決書第24頁“不構成侵權的博文言論”中,法院認可了西風(此刻他代表了所有玩老貨的藏家)對展品真偽提出質疑乃至否定的權利。(注意:是認可他有權利,而非認同其對真偽的判斷。)這一段話為所有圈子里的后來人指明了方向,單純涉及器物真偽的判斷問題,法院不會插手。因此,下次看見“國寶幫”那些開門新的贗品,可以大膽罵,放心罵,怎么痛快怎么罵。只要別人身攻擊,都沒問題。
我認為最成功的例子,莫過于馬伯庸親王那篇著名的《少年Ma的奇幻歷史漂流之旅》,“國寶幫”除了氣急敗壞地跳腳大罵毫無辦法,而且這樣人身攻擊同樣很容易把自己推上被告席,若是一不小心自己“勢敗”,且看他們如何收場。
法院不傻,不會用國家權力替“國寶幫”背黑鍋。法院為批判的限度畫出了范圍的同時,其實是變相認可了批判的自由。這為將來對“國寶幫”的輿論戰,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這難道不是勝利嗎?這是整個圈子的大勝!
最后一點感想
對于鑒定足夠專業說明您可以瞬間判斷“李教授”藏品的真偽,您可以對辦假貨展覽這種行為嗤之以鼻;同樣的,對于法律如果不是足夠專業,產生的誤解,也會讓專業的人士笑話。我想,中國如果真的要成為一個法治國家,至少民眾要給法律和法官足夠的尊重,在發表不同意見之前應該細致認真地了解相關資料。對于本案,至少是判決書。而對于自己并不專業的法律領域,憑感覺出發的一番指責,我們并不提倡。法律和藝術品鑒定一樣,是一門嚴謹的學科,要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再次總結一下全文觀點:
當法院認可:
1.所有對于展品真偽的評論,都不構成侵權。
2.對李舒弟眼力的評論和對人格的大部分評價,也不構成侵權。
西風老師和所有反對“國寶幫”的朋友都沒有輸,都是贏家。
(責編:博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