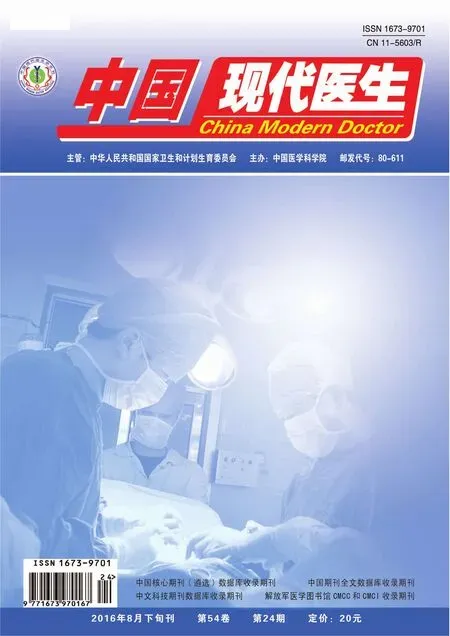椎間盤造影在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診治中的應用效果研究
羅建軍 周玉林 陳 宏
長沙市第八醫院外二科(骨科),湖南長沙410000
椎間盤造影在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診治中的應用效果研究
羅建軍周玉林陳宏
長沙市第八醫院外二科(骨科),湖南長沙410000
目的探討椎間盤造影在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診治中的應用效果。方法選取2010年1月~2015年1月我院收治的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患者130例,隨機分為對照組及研究組各65例,對照組患者予常規診療,研究組患者予椎間盤造影診療,對比兩組患者的治療結果。結果在兩組患者的治療結果方面,研究組患者的VSA評分以及ODI評分均顯著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兩組患者的并發癥發生情況方面,研究組患者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椎間盤造影在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診治中的應用效果理想,有利于改善患者預后,臨床上應當推廣應用。
椎間盤造影;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診治;功能障礙指數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iscography in the treatment and diagnosis of lumbar multisegment degenerative diseases.Methods A total of 130 patients with lumbar multi-segment degenerative disease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January 2015 were selected.The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with 65 patient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egular treatment and diagnosis,and the research group was given discography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The curative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In terms of the curative results in the two groups,VSA scores and ODI score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In terms of the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the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disc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umbar multi-segment degenerative diseases are ideal,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patients'prognosi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Discography;Lumbar multi-segment degenerative diseases;Treatment and diagnosis;ODI
椎間盤造影在過去被看作一種操作比較復雜甚至可能造成并發癥的檢查手段,在臨床應用過程當中遭到比較嚴格的限制。腰椎間盤退變性疾病可以說是骨科的常見病和多發病,近年來隨著MRI以及CT技術的進步,從影像學角度為患者的診斷治療提供依據。國內研究顯示,椎間盤造影作為MRI以及CT檢查的補充,在腰椎間盤退變治療方面有重要的應用價值[1]。本研究探討椎間盤造影在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診治中的應用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0年1月~2015年1月我院收治的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患者130例,男69例,女61例,年齡40~59歲,平均(50.1±1.2)歲。病程1~24年,平均(8.1±0.9)年。入選標準:①具有明顯的腰痛癥狀,伴有一側或雙側下肢疼痛、麻木或間歇性跛行癥狀;②影像學檢查提示腰椎多節段退變。排除標準:①不伴有明顯腰痛癥狀者;②影像學檢查提示腰椎僅存在單一節段退變者或所有節段退變者。將130例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及研究組各65例,兩組患者在年齡、性別以及病程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對照組對照組患者常規拍攝腰椎正側位、雙側斜位、過伸過屈位,術前腰椎過伸過屈位X片支持腰椎失穩,根據檢查結果擬手術干預節段及手術方式,均采用改良經椎間孔腰椎椎間融合術。
1.2.2研究組對研究組患者提示影像學退變的節段以及鄰近的正常椎間盤行造影檢查[2]。操作之前對患者提供教育培訓,做好溝通從而消除其恐懼心理,造影之前使用魯米那鎮靜。檢查過程當中,患者取俯臥位,核實穿刺椎間隙之后消毒鋪單,使用2%的利多卡因沿著需要穿刺的路徑進行局部麻醉[3]。使用18號穿刺針,其中進針點建立中線10 cm的位置向椎間隙穿刺,透視條件下刺入患者的纖維環以及髓核,確認針尖的位置位于患者椎間盤的中間[4]。髂翼發育異常的患者可使用彎針穿刺完成椎間盤的穿刺。注入碘水溶性造影劑3 mL,造影之后患者臥床休息,術后3 d進行腰椎后路的減壓融合手術治療[5]。
1.2.3結果判斷使用Walsh椎間盤造影診斷標準。造影顯示患者椎間盤結構存在形態變化:誘發疼痛與患者平時較為類似:有1個相鄰的間盤為陰性[6]。對該病患者而言,椎間盤形態變化只能作為參考標準,誘發疼痛的性質以及腰痛癥狀是判斷陽性與否的主要標準。對造影結果為陽性的節段進行減壓融合內固定手術治療[7]。對照組患者根據影像學的檢查結果以及醫師經驗確定手術節段,研究組患者干預節段以及手術方式均使用改良的經椎間孔腰椎椎間融合手術治療[8]。1.2.4經椎間孔腰椎椎間融合手術操作患者全身麻醉后取俯臥位,腹部懸空,使用C形臂X線機定位后逐層切開患者的皮膚、皮下組織還有腰背筋膜,沿著節段棘突剝離椎旁肌,從而暴露椎板以及關節突[9]。使用椎弓根釘并且咬除患側椎體椎板與關節突,切除患者的黃韌帶以及增生內聚的關節面,充分顯露硬膜囊[10]。椎管減壓之后處理椎間隙,取患者下骨質結構后植骨,填充顆粒狀的碎骨到融合器當中,側斜向置入椎間融合器[11]。如果患者屬于雙側下肢癥狀,需要開窗減壓對應的神經根。常規置入鈦棒之后縫合手術切口,術后使用羅哌卡因、嗎啡以及倍他米松液浸潤手術切口,設置負壓引流管[12]。患者在術后預防性使用抗生素頭孢唑啉3.0 g,2次/d,靜脈滴注給藥,同時輔以甲基強的松龍、甘露醇以及甲鈷胺等治療[13]。術后5 h鼓勵患者下床活動,術后3 d拔除引流管,指導患者嘗試腰背肌鍛煉;2周內建議患者臥床休息為主,2個月內在腰圍保護下進行鍛煉[14]。
1.3評價指標
兩組患者分別進行疼痛模擬量表(VAS)評分以及功能障礙指數(ODI)評價(總分45分,得分越高,功能障礙越嚴重)。VAS評分(總分10分,得分越高,疼痛越明顯)標準0分,無痛,無任何疼痛感覺;1~3分,輕度疼痛,不影響工作、生活;4~6分,中度疼痛,影響工作,不影響生活;7~10分,重度疼痛,疼痛劇烈,影響工作及生活。使用功能障礙指數問卷進行ODI評分[15]。分別記錄兩組患者術前、術后3個月、術后6個月以及術后12個月VAS評分、ODI評分的變化。同時觀察記錄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處理,計數資料以[n(%)]表示,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及方差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兩組不同時點VAS、ODI評分比較
研究組患者術后不同時點的VAS評分以及ODI評分均顯著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2。
表1 兩組患者不同時點VAS評分比較(±s,分)

表1 兩組患者不同時點VAS評分比較(±s,分)
組別n術前術后3個月術后6個月術后12個月F值P對照組研究組t值P 65 65 6.8±1.4 7.2±1.3 0.126>0.05 2.6±0.3 1.2±0.2 4.437<0.05 2.2±0.6 1.1±0.2 5.233<0.05 2.1±0.2 0.8±0.2 5.256<0.05 19.294 20.915<0.05<0.05
表2 兩組患者不同時點ODI評分比較(±s,分)

表2 兩組患者不同時點ODI評分比較(±s,分)
組別n術前術后3個月術后6個月術后12個月F值P對照組研究組t值P 65 65 62.6±4.4 62.5±4.3 0.268>0.05 24.3±3.6 15.1±3.8 2.256<0.05 19.1±3.2 11.2±3.6 3.258<0.05 17.4±2.6 8.6±1.2 8.264<0.05 8.496 5.396<0.05<0.05
2.2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研究組患者并發癥發生率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3 討論
近三十多年來,我國腰椎退變性疾病的臨床診療水平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目前臨床存在的診斷技術包括X線、CT、MRI等常規影像學檢查,亦包括神經電生理檢查[肌電圖(electromyography,EMG)]以及脊髓造影、椎間盤造影、關節突關節封閉及神經根阻滯等侵入性檢查技術。常規影像學檢查可以較好地顯示腰椎退變的形態學改變,對退變局限于某一節段或部位的病例具有直接的定位診斷價值,對大多數腰椎退變性疾病患者的臨床診斷僅需進行常規影像學檢查即可。隨著對椎間盤源性腰痛發病機制、病理生理學變化的不斷研究,MRI檢查T2加權像上椎間盤纖維環后方存在的局限性高信號區(high intensity zone,HIZ)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其對青壯年單節段椎間盤退變患者椎間盤源性腰痛具有良好的提示性意義[16],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椎間盤造影在椎間盤疾病診斷、檢查、確定病變程度以及選擇治療措施等領域的價值[17]。許多醫務工作人員認為椎間盤造影對于確定病變的節段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椎間盤造影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確診,而旨在手術之前準確定位。有研究人員認為存在坐骨神經痛但脊髓造影檢查為陰性的患者,椎間盤造影應當作為手術之前的補充檢查,并且認為椎間盤造影對于慢性腰痛病治療方案的選擇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8]。兩個以上的椎間盤突出而發病節段不夠明確的患者,往往可以通過椎間盤造影來準確定位。對于那些癥狀性的椎間盤退變患者,腰椎MRI往往提示多節段的退變,可以使用椎間盤造影來確定融合的范圍[19]。椎間盤造影是確定椎間盤下腰痛最為主要的手段之一,可以確定誘發患者疼痛的椎間盤。多節段椎間盤退變的患者在術前使用椎間盤造影檢查,一方面可以進一步確定病變的節段,另一方面還能在手術之前充分確定置換節段的病變水平,特別是后纖維環以及后縱韌帶是否完整以及椎間盤的突出方向,從而為手術操作提供定性以及定位指導[20,21]。椎間盤造影在判斷椎間盤的退變程度方面,包含客觀因素以及主觀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兩組患者的治療結果方面,術后研究組患者的VAS評分以及ODI評分均顯著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兩組患者的并發癥發生情況方面,研究組患者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椎間盤造影在腰椎多節段退變性疾病診治中的應用效果理想,能幫助患者早期確診,有利于改善患者預后,臨床上應當推廣應用。
[1]彭寶淦,吳聞文,侯樹勛,等.腰椎間盤內破裂的診斷和治療[J].中華外科雜志,2015,41(8):564-566.
[2]馬昕,王洪立,姜建元,等.HIZ與椎間盤造影在椎間盤源性腰痛診斷中的對比研究[J].脊柱外科雜志,2014,7(2):75-77.
[3]王華東,侯樹勛,王曉寧,等.MRI高信號區與椎間盤造影在椎間盤源性腰痛診斷中的相關性研究[J].中華外科雜志,2014,40(13):973-976.
[4]康南,王慶一,魯世保,等.椎間盤造影在多節段腰椎間盤退變性疾病治療中的作用[J].中國骨腫瘤骨病,2015,5(3):164-167.
[5]張曉陽,茂守木三男,董宏謀,等.腰椎間盤造影及其臨床意義[J].中華骨科雜志,2015,27(10):664-666.
[6]陳興燦,劉乃芳,李曉紅等.MRI和CT椎間盤造影對腰椎間盤破裂診斷的比較研究[J].中華放射學雜志,2015,11(39):1161-1164.
[7]劉淼,陳興燦,李曉紅,等.CT椎間盤造影對腰椎間盤內破裂的診斷價值[J].介入放射學雜志,2014,17(8):497-499.
[8]劉施巍,王昕.椎間盤造影與椎間盤源性下腰痛診斷[J].國外醫學·骨科學分冊,2015,26(6):331-333.
[9]吳祖堯.從髓核造影觀察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病理[J].中華外科雜志,2015,41(2):244-245.
[10]何東,陳興燦,劉淼,等.青年軍人軟骨板破裂型腰椎間盤突出癥的CT診斷[J].東南國防醫藥,2014,13(6):523-525.
[11]郭家川,杜勇.椎間盤源性下腰痛的影像診斷進展與展望[J].臨床放射學雜志,2015,29(8):1140-1142.
[12]王子軒,陳祥民,胡有谷.腰椎間盤MR/局限性高信號區的影像學分析[J].中國醫學影像技術,2014,24(5):743-746.
[13]游箭,邵陽,李春平,等.經皮腰椎間盤穿刺后外側入路的影像學觀察[J].中國醫學影像技術,2015,25(5):1013-1016.
[14]王新偉,袁文,陳德玉,等.不穩定型下頸椎損傷的手術治療(附56例分析)[J].中華創傷骨科雜志,2014,6(6):644-648.
[15]蔡治安,高世榮.無脊髓損傷的下頸推嚴重骨折脫位11例分析[J].實用骨科雜志,2015,3(2):101-102.
[16]朱鍇,陳其昕.不同MRI特征在下頸椎韌帶結構損傷中的診斷價值[J].浙江醫學,2014,30(7):671-674.
[17]張繼東,夏群.慢性腰腿痛患者椎間盤造影的形態學特點及相關因素分析[J].中華骨科雜志,2015,27(7):489-493.
[18]吳聞文,吳葉,侯樹勛.腰椎間盤源性腰痛與炎癥介質關系的臨床研究[J].中國疼痛醫學雜志,2015,12(3):105-106.
[19]郭鈞,陳仲強.椎間盤源性下腰痛的影像學診斷[J].頸腰痛雜志,2014,24(l):56-58.
[20]彭寶淦,侯樹勛.腰椎間盤Mm高信號區在診斷椎間盤源性下腰痛中的意義[J].中國脊柱脊髓雜志,2014,14(6):331-333.
[21]葉曉健,李家順,胡玉華,等.頸椎間盤壓力的測定及其臨床意義[J].第二軍醫大學學報,2015,18(6):588-590.
Study of application effects of discography in the treatment and diagnosis of lumbar multi-segment degenerative diseases
LUO JianjunZHOU YulinCHEN Hong
No.2 Department of Surgery(Orthopedics),Changsha Eighth Hospital,Changsha410000,China
R681.53
B
1673-9701(2016)24-0067-03
2016-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