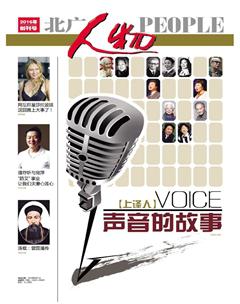黃潔夫有溫度的推手

沒有什么可以失去,我最少還是個有尊嚴的醫生。
2013年國家衛生部撤銷變為衛計委時,黃潔夫從衛生部副部長任上退休。
一個直言不諱的高官
黃潔夫第一次一言震驚四座,是在2005年7月。這年,黃潔夫以中國衛生部副部長和著名移植醫生的雙重身份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層會議,并被選為整個西太平洋區主席。會上,其他國家代表緊追不舍地問:“你們每年九千個器官移植,移植器官從哪里來?”面對與會者明顯不夠友好的態度,黃潔夫坦然作答:“主要來自于死囚,一部分來自親屬間移植。”一語未畢,會場一片嘩然。一些關系比較好的同事和黃潔夫開玩笑:“你捅了馬蜂窩,副部長當不成了。”
黃潔夫絲毫不畏懼:“身為大會主席,我要主持會議,要面對與會代表,我不能不答,必須面對。只有我說實話,中國的器官移植事業才可以擺脫來自醫學倫理和國際學術界的雙重壓力,才能使普通人民群眾享受到這種醫療技術服務。丟官沒事,大不了回去做醫生。”黃潔夫再度就中國器官移植問題大膽直言是在七年后,中國器官捐獻事業迎來拐點,黃潔夫也受命擔任改革的領軍人。此后黃潔夫極力推進公民自愿捐獻,讓中國公民的器官捐獻逐步邁向法制化。2012年9月,在深入調查中國器官捐獻制度不盡如人意的真實原因后,黃潔夫毫不隱晦地說:“管理體制是器官捐獻事業的最大制約!沒有反腐敗,沒有打老虎、打蒼蠅,就不會有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經過十年艱苦努力,2015年1月1日,中國宣布全面停用死刑犯器官。
在器官移植上黃潔夫直言不諱,在醫療體制改革上也不遜色。2009年,醫改方案即將實施,黃潔夫在全國“兩會”上諫言充分利用市場機制走革新道路:“不少人推崇對公立醫院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曾經采用過的‘收支兩條線的路徑,很不理智!我在醫院很多年,太了解‘大鍋飯體制下的后果了!”兩年后,黃潔夫以全國政協委員身份親自策劃公立醫院改革意見會,直指醫改進展緩慢:“醫改的難點在公立醫院改革,但現尚未觸碰核心!”
如今,黃潔夫雖然從衛生部副部長的位置上退休,但依然全心打理中國人體囂官移植基金會。
一個仁心仁術的醫生
作為部長級高官,黃潔夫的敢言常常讓大眾為之一振,他給出的理由是:“我首先是一名醫生,我的敢言,是出于外科醫生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職業習慣——你把肚子一切開,是肝癌就是肝癌,是闌尾炎就是闌尾炎,騙不了人,所以你必須得實事求是。”黃潔夫出生于江西吉安,14歲那年,黃潔夫的父親身患急性暴發性肝炎過世。從生病到過世,父親遭受了很多折磨,彌留之際,父親對黃潔夫說:“你將來學醫吧,救治像我這樣的病人……”帶著父親的臨終期許,黃潔夫從此義無反顧地踏入醫學殿堂。
23歲時,黃潔夫從廣州中山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貧困邊遠的云南礦山工作,在近九個年頭里,他既是醫生也是礦工。雖然條件艱苦、環境惡劣,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心中做個好醫生的夢。為了更好地服務百姓,從云南礦山調往廣州后,黃潔夫一邊工作,一邊完成了中山醫科大學外科學的碩士學位,隨后又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醫學院外科作博士后研究,并成為澳洲國立肝臟移植中心外科骨干醫師。在黃潔夫看來,外科醫生是一個很有樂趣的職業。1998年一個香港著名人士換腎后并發后遺癥,被香港醫生判了“死刑”,中央點名讓黃潔夫赴港參加會診搶救。研究之后,黃潔夫認為還有5%的希望,決定把病人接到廣州。當時香港的醫療技術比內地先進,業內以及媒體都不看好黃潔夫的冒險舉動。但黃潔夫組織二十多名專家制定救治方案,搶救66天后,病人如愿脫離危險。“那66天里,一大幫香港記者天天守在醫院樓下,就等著發布病人的死訊。”
2001年,黃潔夫調往北京擔任衛生部副部長。調令下來前,黃潔夫只提了一個要求:保留他作為一名外科醫生的身份。最終他的醫生資質被保留,他在北京協和醫院定期坐診,直到如今70歲高齡,他還是協和醫院的外科醫生,每周都上手術臺。黃潔夫對病人一直心懷感激。
一個大筆書寫的“人”
黃潔夫覺得一個人的尊嚴最重要,尊重他人的尊嚴是做人的底線,所以面對病人送紅包這種尷尬他總會很得體地化解,但面對損害醫生尊嚴的事時,他則會拍案而起。因為醫患關系緊張,2014年國家衛生計生委出臺新規,規定從2014年5月1日起,患者一入院,醫生就必須簽署《醫患雙方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新規出臺后,黃潔夫不留情面地連續發問:“簽那個字有效嗎?能制止紅包嗎?能制止回扣嗎?這只不過是對醫生尊嚴的侮辱!解決醫生收紅包問題,解決醫患關系問題,需要的不是這一紙協議,而是醫院體系的深度改革。”對黃潔夫而言,“尊重、尊嚴即底線”原則,適用于一個人、一個群體,甚至一個國家。黃潔夫數十年如一日不遺余力地推進中國人體器官移植的變革,就是為了“尊嚴”二字。
2005年黃潔夫在國際會議上那破釜沉舟的一舉曾讓很多人不解,他無數次地被問:“既然每年可以順利完成數千例移植手術,為何還要去改變現狀?”黃潔夫多次從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解釋,內在動力之一就是他作為醫生的道德壓力。“醫生這個職業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而這件事嚴重違背了作為醫生的道德底線……”另一個動力來自醫療系統內部。由于移植器官來源不明,國際上對中國移植科醫生采取“三不”政策:不允許中國醫生參加世界移植專業的組織;國際權威期刊不發表中國器官移植相關的臨床科研論文:中國器官移植學者不能在權威會議上公開演講。產生的直接結果是,盡管中國醫生的技術與發達國家同行不相上下,但成就卻無法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
最關鍵的是更加廣泛的民眾利益。所以回國后,面對各方壓力,黃潔夫只有—句話:“我們不能采取鴕鳥政策,不能掩耳盜鈴。中國的器官移植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要改革,要建立一個符合倫理和中國國情的器官捐贈移植體系。”
十年奮斗之后,中國正式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器官捐獻的唯一途徑。2015年10月17日,全球器官捐獻大會理事會全票通過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結束了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長期受排斥和孤立的歷史。一個月后,“顧氏國際和平獎”頒給了黃潔夫。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公開贊譽說:“器官捐獻超越了醫療服務本身,其發展方向代表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方向,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中國移植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也是國家的進步。”對這段話黃潔夫心有戚戚:“一個國家的尊嚴與每一個公民的尊嚴緊密聯系在一起,當每個公民都擁有尊嚴時,國家才有尊嚴,公民才之所以成為‘人。”
董巖據《莫愁·天下男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