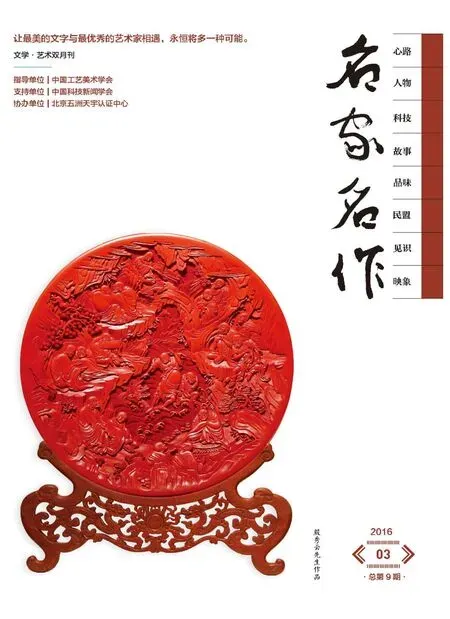楊忠明與他的篆刻藝術
沈嘉祿
楊忠明與他的篆刻藝術
沈嘉祿

《佛像印》楊忠明、陸 康/作
上海人對動手能力強的人多有贊譽,稱之為“多面手”,語近戲謔的則是“三腳貓”,而對博聞強記、視野開闊的人也有比喻:“萬寶全書缺只角”。在獲取常識主要靠百度、獲取信息主要靠微信,表達感情主要靠段子,約飯購物主要靠淘寶的當下,楊忠明完全有資格承當這樣的夸贊,稀缺人才,無可爭議。
劉旦宅夸他為“二楊并舉”
十年動亂時,上海有不少老作家、老藝術家受到狂風暴雨般的沖擊,含冤忍辱,斯文掃地,不是被驅趕到干校勞動就是被邊緣化,親朋好友之間也不便走動,獨居寒舍孤苦清寂,生活上也有諸多困難,青春年少的楊忠明卻不懼嫌疑,經常去“遺老遺少”們家中噓寒問暖,傳遞消息,順便請教學問,也可紓解老前輩的郁結心情,給予一番慰藉。他與陳巨來先生來往,不僅得窺篆刻門徑,還聽他暢談舊上海文壇的奇聞名逸事,回家后就記在小本子上,關鍵之處常用暗語,以防不測。他刻印鈕是向陸明良學的,同時還參考漢晉的石刻藝術,無論避邪還是螭首,都能刻得栩栩如生,凜凜威風,雖不足方寸而聚集風云,呈現盛世氣象。不少篆刻家以為是雕蟲小技,不屑染指,他卻刻得不亦樂乎,甘當印壇方家的綠葉。
陳巨來在大氣候有所回暖時便主動為文藝界朋友治印,出手相當慷慨,需要有鈕式的印石就囑楊忠明加工,一刻就是十多方,這說明陳巨來對楊忠明是非常認可的。后來,劉旦宅還為楊忠明題了“二楊并舉”的匾額,等于把他與康熙年間的壽山石雕藝人楊玉璇并列。但楊忠明素來低調,從不對外自夸。
事實上,楊忠明在傳統書畫藝術被視作“四舊”的荒唐年代里,刻印鈕不僅要避人耳目,而且費時費力,在經濟上的收入幾乎等同于賣炭翁,遠不及今天篆刻家那般瀟灑。“但我覺得蠻開心,也不會跟人家討價還價,自視為練把式的極佳機會。畫壇大家謝之光在文革后期,白石素餐而灑脫從容,凡求畫者上門,有求必應,題材自定,當場潑墨,毫無架子,當時他也認為求畫者帶宣紙來,就是買來炮仗給他放。前輩大師如此心態,我還有什么可說的呢?”他說。
楊忠明向年齡相近的陸康、陸大同伯仲學書法繪畫,結為莫逆,情同手足,還經常去陸澹安、鄭逸梅、錢君匋、陳左高、朱大可、葉露淵、魏紹昌、蘇局仙等老前輩府上請教藝事,關起門來聽他們暢談舊上海的故事,感受他們身上的儒雅與睿智。日積月累,楊忠明也裝了一肚皮舊上海軼聞趣事,近年來經常在新民晚報撰寫饒有情趣的文飯小品,上海的前塵往事與風云際會,前輩文人的風范與市民階層的智慧,如涓涓細流滋潤著讀者心田。
前幾年,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推出一套老上海叢書,其中有他的掌故隨筆集《雅玩》和管繼平兄的市井風俗文化隨筆集《游嬉》,我的美食隨筆集《風味》忝列其中。叢書既出,在上海書展上亮相,簽售當天讀者相當踴躍,規定的簽名時間飛一樣過去,而讀者不愿散去,主辦方不得不更換地方繼續操練。據編輯信息反饋,許多年輕讀者看了《雅玩》后大呼過癮,想不到舊上海的文人這么會玩,玩出了情調,玩出了文化。
“外婆的魚”別有一番況味
后來楊忠明又出版了隨筆集《外婆買條魚來燒》,也受到讀者的一致好評。楊忠明寫美食,不是得意于吃到了魚翅海參,而是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饋贈,銘記父母的哺育之恩,感喟許多存在于老風俗之中的民間小吃在今天的喧囂中漸行漸遠。我以為,這樣的美食文章就超越了味覺體驗的層面,而上升至文化思考的境界。
比如楊忠明寫到上海人“吃食堂”,上海中年以上的人大都有這方面的經驗。居民食堂一般開在弄堂里,由家庭婦女操持,這是特定時期為了解放生產力、用社會力量解決居民吃飯問題的舉措。但吃過食堂的人,或受制于計劃經濟的市場狀況,或受制于自身的經濟能力,均能品味出絲絲縷縷的甜酸苦辣。“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買了饅頭拿在手里,走到重慶北路上,突然從對面四樓屋頂上飛下一只麻雀,對著我手里的白饅頭直沖下來就毫不客氣地用嘴啄來吃。我一看,哈哈,從來也沒有過的奇怪事,野生麻雀竟然不怕人。我讓它吃個飽,它站在我手上不想離開。同學看見說,這個麻雀是你養熟的吧!那麻雀好像聽得懂人話,又吃了幾口饅頭,翅膀一振,連叫幾聲,仿佛是感謝的鳴聲,呼的一下飛走啦。后來我明白,這只饑餓至極的麻雀,不顧一切地搶人的食品吃,即所謂‘鳥為食亡’,今天我看到了這一幕!”
這能簡單地視作美食文章嗎?這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苦食文章”!
上海人嗜吃大閘蟹,每年金風送爽菊黃時節,談吃蟹的文章連篇累牘,熱灶頭炒冷飯,但楊忠明卻寫出另一番滋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去滬上刻印大家陳巨來先生家,只見他老人家正在方桌上拆蟹粉。巨老說:楊忠明,圖章刻到一半,有人送來二串太湖大閘蟹,你知道嗎,蘇州太湖蟹要比昆山陽澄湖里的蟹味道更鮮,陽澄湖里的蟹都是從太湖里爬過去的!我拆蟹粉的水平一等一流,我把刻元朱文的功夫用在拆蟹粉上,今朝蟹粉拆得我手要斷脫,人要昏過去了!小蟹腳里一點點蟹肉我都把它剔出來。有人拆蟹粉,小腳都丟掉,其實,小腳里的蟹肉最鮮,這是秘密,別人是不知道的!還有,拆蟹粉絕不能用死蟹拆,否則叫‘叫花子吃死蟹’。吃了死蟹,人就死蟹一只,圖章就刻不動了……”
苦中作樂而不乏自嘲精神,這就是陳巨來等文化老人彼時的集體心態。
楊忠明寫到一些正在離我們遠去的風味,心懷惆悵,戀戀不舍,在《漸行漸遠的風味》一文中,他勾沉了“花露”等物。“‘花露’可以解暑渴,增酒味,制糕點,入藥方。上海人對此恐怕很陌生,我聽鄭逸梅先生說;‘蘇州有花露茶,味香極,為文人雅士所好。’所謂花露茶,就是把鮮花放在茶葉中,讓茶葉汲取花中的精氣,或用花提取的液汁來點茶。老上海人喜歡在夏日飲用‘金銀花露’清熱祛暑無上妙品。沈復《浮生六記》記:‘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蕓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這是多么雅逸的文人閑趣啊!花露食之可以養顏延年。冒辟疆《影梅庵憶語》記董小宛擅制花露時稱:‘釀飴為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時采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艷’。”

楊忠明自繪自刻的紫砂壺
去年,楊忠明又推出一本掌故類的隨筆集《上海什錦》,品評人物,回想舊事,勾沉史料,暢想未來,依然趣味盎然,深得“補白大王”鄭逸梅神韻!
佛像印、肖像印,還有抗日英雄譜
楊忠明除了刻印鈕,還擅長刻佛像印和肖像印。

《雕虎穿環鈕章》楊忠明/作
佛像印是古今不少篆刻家屬意而專注的題材,楊忠明早就有不俗的成績,而且形成自己的風格特征。據我有限的藝術經驗來觀之,至少有三個特點。其一,體現了中國藝術家一貫的世俗趣味。忠明在方寸之間傳神地表現了菩薩的各種姿態,或三曲而立,或交腳而坐,或半跏而坐,或施以含義豐富的手印,一點一滴,源遠流長,將中國民間版畫的思路體現在精心安排中。其二,構圖美觀,麗姿典雅。忠明根據印面的長短寬窄布局菩薩的姿態,并飾以菩提或須彌座,還能通過衣紋和纓絡體現吳帶當風的動感,使整個畫面更加空靈活泛。其三,體現了民族化的追求。同樣是因為芥子之微的局限,一般人難以精細刻劃菩薩的寶相,但忠明卻把握住了中國佛像藝術的精髓,采取頭頂肉髻,飾以背光及面容的正側轉勢等手段以簡勝繁,以靜制動,并以慈愛嫵媚的笑容和妖嬈婀娜的身段來表現“菩薩如宮娃”的美學觀念。特別是觀音大士的立像,因為賦予了鮮明的女性特征,在中國民眾中能夠獲得更大的認同。我有幸從忠明處迎回一方佛像印,供養于城南寄廬,與忠明共沐無邊佛光,誠為無上喜悅。
有一次,我在朋友家里欣賞到忠明篆刻在大塊壽山石、雞血石上的十八尊羅漢,每尊足有掌心之巨,不僅布局妥帖,相互照顧呼應,而且每尊羅漢各具表情,姿態生動,背面則由著名書法篆刻家陸康刻一首詩。每葉如石版畫一般,有很強的表現力。
每方羅漢像經忠明精心蛻成印花,裝裱成二十冊分贈友好,我又有幸獲贈一冊。沐手焚香靜心拜觀時,室內似有寶光從窗外射進,令我心靈騰飛于祥云之間。后來忠明還將羅漢像的印譜敬獻于玉佛禪寺,經大和尚覺醒法師及書法篆刻家劉一聞先生、畫家戴逸如先生題詞祝賀,以遂夙愿。

《十八羅漢之一》(右圖)楊忠明/作
迦諾迎伐蹉尊者(喜慶羅漢)
頂笠閑余步
持珠獨自行
橋邊流水急
廓爾悟吾生
忠明在篆刻佛像印的同時,還為多位朋友刻肖像印。肖像印自古就有,先秦及兩漢的肖形印,內容也相當豐富,表現手法簡練,寥寥數筆足可傳神會意。我們在存世的漢印中就可以看到“鼓樂”“歌舞”“戲獸”“雜技”“牛耕”“門樓”“屋廬”等內容,不僅有獨特的藝術價值,還是古代社會生產和精神活動的典型實錄。但是在今天,這一路功夫少有人染指,而忠明卻情有獨鐘,倚馬可待,往往在喝茶時一口承諾,次日一早,鮮紅的印蛻就曬在博客和微信上了。
楊忠明在跟我聊起肖像印時曾感慨地說:古人在兩千年前就能稔熟地把握這種題材了,他們在狹小空間內,對肖像加以恰當的變形處理,化解種種局限,使之妥帖地安置在這個構圖中,又表現得如此概括簡練,很了不起啊。這是忠明對肖像印創作的認識,也是對自己的要求。所以他為巴金、姚明、劉翔、曹可凡等文體界名人篆刻的肖像印,生動體現了人物的氣質與性格,他為作家朋友刻的肖像印也成了他們專欄文章的logo。
去年秋天我提醒他:“今年9月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你何不刻一套抗戰名將譜?”他一聽叫好。不出一個月,當他將第一批“8方”抗戰名將肖像印曬到網上后,網友紛紛點贊。
去年春天,當他得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會計劃在8月份舉辦《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與全民抗日戰爭文物圖片展》,同時還要召開中共著名抗日將領后人座談會,就毛遂自薦,向張黎明館長請纓,希望為《新民晚報》準備刊登的名將后代回憶文章配發印章,為版面增色。張館長一聽非常高興,就將相關抗戰名將的名單給他作為創作依據。
楊忠明專程到浙江青田采購上佳石材,加工成統一規格,磨平、拋光。挑選人物的最佳照片,用毛筆勾勒臉型,用墨色調節人像的陰陽對比,光影層次,強調人物的精神氣質與性格特征。
忠明說:肖像印創作必須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以再現人物精神世界為第一要務。在具體操作時,不可粗心大意,若是刻斷一根線條,整件作品就功虧一簣。
創作這33方印前前后后用了幾個月時間,為了能夠趕在8月中旬完成任務,最后幾方是在大暑高溫中“赤膊上陣”,其中有幾方他覺得不甚滿意,又磨去返工。為了趕工,他每天只睡幾小時。
這組彪炳史冊的中共抗日名將的肖像印,線條粗獷,布局得當,朱白兩色對比強烈,金石氣十足,人物形象健碩飽滿,眼神、鼻梁、嘴角、額面,藝術地再現了中華民族英雄兒女不畏強虜,不怕犧牲,奮勇進擊,爭取獨立自由、民族解放,維護世界和平,迎接新中國橫空出世的光輝形象與時代精神。楊忠明將這批肖像印的朱紅印蛻呈現在我面前時,我仿佛聽到了軍馬的嘶鳴,看到了硝煙的騰起,想象到中國軍魂與日月同輝的恒久呈現。
楊忠明精心創作的這組抗日將領肖像印一共拓了兩本,一本由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收藏,一本由自己保存,并請來滬參加座談會的中共著名抗日將領后人一簽了大名,彌足珍貴。通過這組抗日將領肖像印創作,楊忠明不僅積累了寶貴的藝術經驗,在歷史認識及思想感情方面收獲良多。

楊忠明簡介:
楊忠明,上海作家,篆刻、雕刻家。祖籍江蘇昆山。1951年出生。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協會會員。別署霽光、明壺堂。20世紀70年代師從陸康、陳茗屋先生學習書法篆刻。后又師隨鄭逸梅先生學習“舊聞”寫作,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報刊發表文章至今。現在為《新民晚報》 “夜光杯”版面、《食品與生活》、中國電信《翼時代》《旅游時報》《科學與生活》等報紙雜志寫古玩、收藏、美食、旅游等專欄文章。現任澳門《印緣》雜志編輯,澳門美術出版社副社長,澳門印社理事,浙江方山印社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