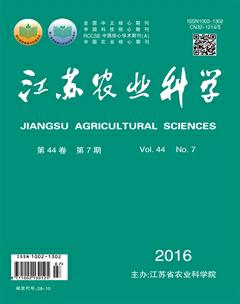基于生態位的鄱陽湖地區農業現代化空間分異及類型
仲亞美 葉長盛
摘要:根據Hutchinson的“多維超體積”理論建立農業現代化生態位評價綜合指標體系,基于改進的生態位態勢理論以及生態位重疊度理論,測算競爭力大小及競爭關系,并分析其空間分布規律,劃分發展類型。結果表明,(1)農業類型主要為均衡型,競爭較激烈,生態位寬度差別顯著。江西省南昌縣綜合生態位寬度最大,為0.015 1;江西省萬年縣最小,僅為0.005 0。Pinaka指數均值大于0.815 7,約占總數的42.31%,小于0.647 7的僅占19.23%。(2)總體趨勢上,南北向呈倒“U”形分布,最高值都分布在中部,高值沿東北-西南向分布,低值分布于西北、東南。局部層面上,農業現代化水平在西北、中部、東南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性,在空間上呈現出中部高兩翼低的分布格局,與區域地形有著明顯的耦合關系。(3)HH型主要分布域鄱陽湖流域及中部平原帶,LL型則分布于兩側高丘低山等地勢較高區。(4)各類型綜合生態位均值0.011 4>0.008 7> 0.006 1;Pinaka指數均值0.917 5>0.802 5>0.678 8;即強勢類型>均衡類型>弱勢類型,二者呈正相關,均從中部平原,向兩翼山地遞減。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態勢理論;生態位重疊度;鄱陽湖生態經濟區
中圖分類號: F320.1;F32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6)07-0572-07
農業現代化是我國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其發展水平落后于發達國家100年左右,已成為我國現代化的短板[1]。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走現代農業發展道路。只有準確地評價、判斷各地農業現代化的真實發展水平,才能真實地判別出各地農業現代化究竟達到何種程度,才能把握影響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因素與具體的發展方向[2]。目前農業現代化研究大多從投入、產出以及農村經濟等方面構建指標體系,運用多指標綜合評價法、灰色關聯分析、熵值法等靜態數理分析方法進行評價。如辛嶺等從農業投入、產出、農村社會發展、農業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構建指標體系,運用綜合指標評價法、灰色優勢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3-5]。研究表明,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以“胡煥庸線”呈現“東高西低”的空間格局,在空間上呈現出一條稍被拉平的“S”形曲線的分異形態,且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差異。從區域角度看,中原經濟區發展水平大部分低于全國平均水平[6]。研究對于促進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農業現代化是一個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資料所構成的龐大的生態系統,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時空過程[7],現有研究只注重靜態的數理分析,無法準確反映現代化的真實情況,隔斷了農業現代化生態系統中種間、各生態因子間及其與內、外部環境的聯系,忽略了農業生態系統中的種間競爭關系。生態位理論通過對“態”與“勢”的結合可以真實反映農業現代化的動態變化,生態位重疊又可以準確量化競爭關系,從而克服現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已廣泛應用在耕地潛力評價、生態適宜性評價、企業競爭力評價等,在農業現代化的評價中還未涉足。為此,本研究以江西省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為例,在態勢理論及生態位重疊理論的基礎上,改進生態位寬度測算方法,測算出該區域農業現代化水平及競爭關系,利用GIS空間分析技術揭示不同縣域之間農業現代化水平的空間分異規律,為鄱陽湖地區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提供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鄱陽湖地區基礎條件良好、自然優勢明顯,是適宜優先開發的重點區域[9],地跨27°30′~30°06′N,114°29′~117°42′E,地勢較平坦。年均氣溫16~20 ℃,無霜期246~284 d,年降水量約1 500 mm[10]。區內包括江西省南昌、九江、景德鎮3市,以及鷹潭市、新余市、撫州市、宜春市、上饒市、吉安市的部分縣(市、區),包括鄱陽湖全部湖體在內,面積為5.12萬km2,占整個江西省面積的30.67%。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擁有全省47個商品糧基地中的19個,2013年區內耕地面積109.31萬hm2,農業從業人員311萬人,農機總動力1 093萬kW,農林牧漁增加值609.76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14.47%。糧食產量約1 078萬t,占全省糧食總產量 21.72%。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自2009、2013年《江西省統計年鑒》《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統計年鑒》以及各市統計年鑒,少數缺失數據通過指數平滑獲得。由于南昌市東湖區、西湖區、青云譜區、灣里區、青山湖區,九江市潯陽區、廬山市,景德鎮市昌江區、珠山區,鷹潭市月湖區,撫州市臨川區和新余市渝水區農業統計年鑒不完整,數據缺失嚴重,各區農業發展不具代表性,因此,選出有代表性的26個縣(市)作為研究對象,即南昌市南昌縣、新建區、安義縣、進賢縣,九江市九江縣、武寧縣、永修縣、德安縣、星子、都昌縣、湖口縣、彭澤縣、瑞昌市、共青城市,鷹潭市余江縣、貴溪市,上饒市鄱陽縣、萬年縣、余干縣,撫州市東鄉縣,宜春市豐城市、高安市、樟樹市,吉安市新干縣,景德鎮市樂平市、浮梁縣。
2.2 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生態位評價模型
2.2.1 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生態位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Hutchinson的“多維超體積”理論[11],以及科學性、系統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等原則,本研究構建了包括農業生產手段水平維、農業支撐力水平維、農業生產水平維、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維、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維5大生態位維度,以及16個具體測量指標在內的農業現代化生態位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AHP層次分析法獲得各維度與測量指標權重(表1)。
式中:n表示空間單元數量;xi、xj分別表示i、j的屬性值,wij表示空間權重矩陣。Morans I指數變化范圍為(-1,1),顯著性水平為0.01時,若GMI顯著為正,表明各維具有明顯的集聚態勢;相反,則有明顯的空間差異特征;若GMI接近于0,則空間分布沒有相關性[16]。
3 結果與分析
3.1 鄱陽湖地區農業現代化綜合生態位寬度
以2013年的數值作為態的測量指標,以2009—2013年各指標的年均增長量作為勢的測量指標,量綱轉換系數為1年,將數據代入式(2)、式(3),獲得(表2、圖1)。
從綜合生態位寬度來看,鄱陽湖地區各縣域發展極不均衡。南昌縣的綜合生態位寬度為0.015 1,農業現代化程度最高,萬年縣綜合生態位寬度僅為0.005 0,農業現代化水平最低,二者相差達0.010 1。各維度生態位寬度占比最大的是農業生產手段維,占總和的38.92%,最低的是農業經濟發展維,僅占13.06%。農業生產手段維上,南昌縣寬度最大,達到0.027 3,其次是浮梁縣、樂平市,分別是0.022 4、0.017 9,萬年縣寬度最低,僅為0.002 4。南昌縣與萬年縣相差 0.024 9,該維上波動最大。農業支撐力維上,南昌縣、德安縣生態位寬度較大,依次為0.011 3、0.010 2,安義縣最小,為 0.000 9。南昌縣與安義縣相差達0.010 4,其波動仍然很大。農業生產水平維上,樟樹市、余江縣綜合生態位寬度依次為0.014 0、0.012 4,排名靠前。星子縣最小,僅為0.003 8,其與樟樹市之間的差值為0.010 2。農業經濟發展維上,余江縣、余干縣寬度最大,分別為0.013 0、0.012 1,德安縣寬度最小,為0.003 3,其與余江縣僅相差0.009 7,其波動幅度僅小于農業經濟發展維。農業可持續發展維上,萬年縣、南昌縣分別為0.009 7、0.008 4,寬度較大,而瑞昌市、九江縣寬度最小,依次為0.001 3、0.000 9。萬年縣與九江縣之間的寬度相差 0.008 8,各縣域在該維度上寬度較小,波動也最小。
3.2 鄱陽湖地區農業現代化生態位重疊度
根據生態位理論,通常在相鄰的情況下,物種間才會因為資源、生存空間等問題產生競爭。因此本研究取相鄰縣域間的Pinaka指數均值(表3)。
各縣域生態位重疊度普遍較高,競爭強度相差大,農業資源分布并不均衡。生態位重疊度達到了0.80以上的占 42.31%。南昌縣、新建區、彭澤縣等均達到0.90以上,僅有九江縣、武寧縣、都昌縣、貴溪市、萬年縣的生態位重疊度小于0.70。峰值和谷值分別出現在南昌縣與萬年縣,分別為 0.945 0、0.647 7,相差0.297 3,差距較大。
從圖2可看出,縣域綜合生態位寬度與Pinaka指數均呈現從中部平原向兩翼遞減的趨勢,且呈正相關。高生態位寬度與高Pinaka指數分布于中部,從東南至西北呈帶狀,低生態位寬度則對稱分布于兩側。二者的最大值均位于中部、東北部,以及西南部,新建區、豐城市一帶。區域綜合生態位寬度值兩頭小中間大,主要處于中等水平,但重疊度普遍較大。綜合生態位寬度于0.010 1~0.015 1的有南昌縣、進賢縣等7縣,僅占總數的26.92%;介于0.008 3~0.007 8的占總數的5385%;小于0.007 8的縣域占總數19.23%。Pinaka指數均值小于0.6477,僅有九江縣、萬年縣、武寧縣等,僅占19.23%。
3.3 鄱陽湖地區農業現代化空間分異
3.3.1 總體趨勢分析 采用Arcgis 10.2中的趨勢分析工具,對縣域綜合生態位寬度與Pinaka指數趨勢進行三維通視分析。總體上看二者空間分布相似,二者最高值都分布在中部,南北向呈倒“U”形分布。高值沿東北-西南向分布,低值分布于西北、東南。說明鄱陽縣、新建區、南昌縣等中部平原地區數值較大,而武寧縣、貴溪市等兩側地勢較高區數值較小,即生態位寬度與重疊度低(圖3)。
3.3.2 空間自相關分析 (1)全局空間自相關。在ArcGIS 10.2中運用空間分析模塊對以下指標進行全局自相關指數Morans I測度,結果(表4)表明,研究區全局Morans I全部為正值,其中除農業支撐力維、可持續發展維P<0.05外,其他維度P<0.01,說明各指標表現出水平相似之間的聚集,空間存在正的空間相關性。
(2)局部空間自相關。GMI值考察了空間分布的整體關聯性,但未揭示局部空間集聚規律。因此,在GeoDA中加入空間權重矩陣,獲得LISA集聚圖,以清晰地說明區內集聚情況(圖4)。
各維度生態位寬度的HH(高高)集聚型主要分布在鄱陽湖流域的中部濱湖平原、以及少數西南、東北部丘陵地區,LL(低低)集聚型主要分布于區域兩翼,集中于西部丘陵中低山及東部崗地地區。
生產手段維中HH集聚型從東南至西北呈帶狀分布于鄱陽湖流域及東北及西南崗地帶,有南昌縣、新建區、鄱陽縣等,LL集聚型分布于兩側高丘低山區,有武寧縣、瑞昌市、九江縣、貴溪市等,這主要是由于鄱陽湖流域地勢平緩,有利于農機化的開展,同時灌溉條件優越等原因造成。從農機總動力來看,南昌縣與新建區分別達到了164萬、127萬kW,而貴溪市僅為59萬kW。
農業支撐力維集聚不顯著,區域內HH集聚型主要沿鄱陽湖分布于星子縣、德安縣一帶;LL集聚型分布東南部高丘低山帶,有貴溪市、余江縣、萬年縣。HH集聚型地區在農業投入方面較高,如在地均用電量方面,兩地均達到了 3 000 kW/hm2,而余江縣、萬年縣僅1 036、912 kW/hm2,相差巨大。
農業生產水平維的HH集聚型分布于中部平原濱湖平原,以及西南丘陵,包括鄱陽縣、南昌縣、余干縣等。LL集聚型位于西北部,如瑞昌市、德安縣、九江縣等。造成這種格局主要是因為平原地帶在灌溉、機械化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耕地充足,糧食產量高,南昌縣糧食產量達到921 358 t,而九江縣僅為65 728 t。
農業經濟發展維中的HH集聚型同樣是分布于中部濱湖平原帶,主要包括鄱陽縣、余干縣、進賢縣等;而LL集聚型位于西部崗地中低山帶,有武寧縣、瑞昌市、德安縣等。同樣,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中部平原帶水陸交通便捷,農業市場發達,利于農產品流通。如在農林牧漁商品率方面,余干縣為82%,德安縣僅為59%。
農業可持續發展維集聚并不顯著,主要是隨機分布。HH集聚型分布在余干縣周邊,LL型分布于兩側高丘,如貴溪市與德安縣。余干縣在該維度的生態位寬度為0.009 9,貴溪市僅為0.005 1,在旱澇保收率上二者分別為64%、54%,同樣相差較大。
綜合生態位寬度與Pinaka指數均值分布基本類似,即綜合生態位寬度大,與周邊縣域的競爭也激烈。其中,HH集聚型分布于中部,LL集聚型位于兩翼。HH集聚型都分布在鄱陽湖流域的濱湖平原以南部丘陵,如鄱陽縣、新建區;LL集聚型分布于東南高丘帶,如貴溪市,以及西北高丘崗地帶,如瑞昌市、德安縣。
3.4 鄱陽湖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分類
根據綜合生態位寬度及Pinaka指數均值,在SPSS 19.0中,對樣本數據進行聚類分析,得到鄱陽湖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系統聚類譜系(圖5)。
根據SPSS 19.0所得聚類結果樹狀圖,以及各縣的經濟發展狀況、空間地理位置等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區域內部空間結構相互作用等關系,將區域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劃分為以下3種類型(圖6)。
區域農業類型主要以均衡型為主,強勢型與弱勢型均占比較小。其中,強勢類型有南昌縣、新建區等7縣(市、區),分布在中部、北部;均衡類型有高安市、鄱陽縣、德安縣等12個縣(市、區),占46.15%,基本緊鄰強勢類型,分布在南部與中北部;弱勢類型包括九江縣、武寧縣等7個縣,主要分布在區域兩翼等地形較高區。
各類型綜生態位均值0.011 4>0.008 7>0.006 1;Pinaka指數均值0.917 5>0.802 5>0.678 8;即強勢類型>均衡類型>弱勢類型,二者呈正相關,均從中部平原,向兩翼山地遞減。
3.5 農業現代化不同類型區分析與發展策略
3.5.1 農業現代化強勢發展類型 該類型主要分布于東北部以及中部濱湖平原等地勢平緩地帶。包括南昌縣、新建區、進賢縣、彭澤、豐城市、浮梁縣、樂平市。各縣域生態位寬度高,生態位重疊度大,Pinaka指數均值為0.917 5。其中,南昌縣重疊度最大,Pinaka指數均值達到0.945 0。以上縣域在鄱陽湖地區農業現代化生態系統中舉足輕重。根據生態位理論,生態位寬度越大,在生態系統中影響力也越大,發展的潛力也就越低。因此,可采取以下發展策略:(1)生態位擴充策略。各地應積極發展劣勢維,擴充生態位寬度。如進賢縣生產手段維寬度較小,應大力發展農機化水平。樂平市、豐城市在農業支撐力維上寬度小,應從提高從業人員專業技能入手,擴充該維生態位寬度。農業經濟發展維與可持續發展維整體寬度低,是整個鄱陽湖地區所面臨的問題,各地應拓寬農產品流通渠道,提高商品化率,建設農業基礎設施,改善農業生態環境。(2)協同發展策略。各維度生態位大小差距較大,這表明資源分布不均是亟需解決的集體性問題。單個城市資源有限,在流通阻塞的情況下,必然導致農業現代化發展差距加大,無法實現均衡發展。因此,必須發揮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內的核心作用,合理整合區內農業資源,如建立農機互助機構等組織,實現與周邊城市的聯動。
3.5.2 農業現代化均衡發展類型 該類型主要分布于崗地、高丘帶,包括安義縣、德安縣、湖口縣、瑞昌市、共青城市、余江縣、新干縣、樟樹市、高安市、東鄉縣、余干縣、鄱陽縣。各維度在較高的水平上基本保持平衡,由此說明,該類型農業現代化水平相當,樟樹市(0.009 9)生態位寬度最大,共青城市(0.007 7)生態位寬度最小。各地Pinaka指數均值為 0.802 5,其中鄱陽縣、樟樹市、余干縣的Pinaka指數均值達到0.80以上,湖口縣的Pinaka指數均值最小,為0.779 3。該類縣域在與具有較大生態位的縣域競爭時,容易處于劣勢,宜采取以下策略:(1)生態位錯位分離策略。各地應在自身農業區位、自然條件等優勢的基礎上,發展具有區域特色的農業類型,避免在弱勢生態位維度上與其他縣競爭。(2)特色生態位。“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一部分物種壓縮了其生態位寬度,形成了單食性或窄食性,通過強化某一特殊功能,提高自身適應性,這就是生態位的特色”[17]。在農業中這種窄食性就是指農業類型的簡化,發展優勢農業類型,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態位。單食性是指只保留優勢農業類型,最大程度地集中資源,集中發展一類。使區域內各地形成“琴鍵”式的農業格局,避免生態位重疊,引發對資源的惡性競爭。
3.5.3 農業現代化發展弱勢類型 該類型分布于兩翼低山與中低山帶,及少數濱湖區,包括九江縣、武寧縣、永修縣、星子、都昌縣、貴溪市、萬年縣。總體呈現“低—低”的雙低發展形式。其中永修縣綜合生態位寬度最大,僅為0.007 7,萬年縣的Pinaka指數均值最小,為0.647 7。生態位寬度小,競爭力弱,但地區間仍存在競爭,不同的是,這種競爭是由于對資源的不完全開發引起的。宜采取以下策略:(1)生態位分離與特化策略。弱種通過分離與特化,是在競爭中發展的最優方式。該類型應選擇不同于其他縣域競爭力強的農業生態位,并特化這部分生態位。如九江縣可以借助自身旅游業的發展,規避競爭,大力發展觀光農業,拓寬生態位。(2)生態位擴充與協同發展策略。在強化各維度同時,各地應協同發展。根據地域距離,武寧縣、星子、九江縣可以建立農業發展聯盟,合理分配資源。同樣,萬年縣與貴溪市也可實現協同發展,而不是通過競爭來拓展生態位。
4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從生態位視角探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農業現代化水平,運用態勢理論與生態位重疊理論測算競爭力與競爭的關系,利用空間分析,探究空間分布規律,并劃分農業現代化發展類型,研究結果表明,(1)從總體趨勢看,綜合生態位寬度與Pinaka指數均值最高值都分布在中部,南北向呈倒“U”形分布。高值沿東北—西南向分布,低值分布于西北、東南。即鄱陽縣、新建區等中部平原地區數值較大,而武寧縣、貴溪市等兩側地勢較高區數值較小。(2)從局部層面看,區域農業現代化水平在西北、中部、東南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性,在空間上呈現出中部高兩翼低的分布格局,這說明農業現代化水平與地形有著明顯的耦合關系。(3)各維生態位寬度、綜合生態位寬度及Pinaka指數HH型主要分布于鄱陽湖流域及中部平原帶,LL型則分布于兩側丘陵崗地等地勢較高區。(4)農業類型以均衡型為主,強勢型與弱勢型均占比較小。強勢類型有南昌縣、新建區等7個縣(市、區),分布在中部、北部;均衡類型有高安市、鄱陽縣、德安縣等12個縣(市、區),占比46.15%,分布在南部與中北部;弱勢類型包括九江縣、武寧縣等7個縣(市、區),主要分布在區域兩翼。此外,縣域間競爭激烈,生態位寬度差別顯著。其中,南昌縣綜合生態位寬度最大,為0.015 1,萬年縣最小,僅為0.005 0。Pinaka指數均值大于0.815 7,占總數約42.31%,小于0.647 7的僅占19.23%。農業現代化生態系統是1個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資料所構成的龐大的生態系統,它是由其1個或者多個結構要素與對其有影響的環境要素構成的具有特定功能和相互作用的系統[18]。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實質上就是多層關系的調整,是農業不斷選擇和躍遷其生態位,拓展現代化農業生存空間的過程。
本研究嘗試將生態位態勢理論以及生態位重疊度理論應用到農業現代化評價當中,對農業現代化競爭力與競爭的關系進行研究,但這種嘗試只是初步性的,在后續的研究中如何從“態”和“勢”2個方面建立指標體系、如何細化到各生態因子之間的競爭關系,還有待研究。
參考文獻:
[1]何傳啟. 農業現代化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策略[J]. 中國科學基金,2012(4):223-229.
[2]呂 杰,趙紅巍. 遼寧省農業現代化水平測度及對策研究[J].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2(1):75-82.
[3]辛 嶺,蔣和平. 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測算[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10,31(6):646-650.
[4]龍冬平,李同昇,苗園園,等. 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分異及類型[J]. 地理學報,2014,69(2):213-226.
[5]李麗純. 基于灰色優勢分析的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測度與波動趨勢分析[J]. 經濟地理,2013,33(8):116-120.
[6]盧方元,王 茹. 中原經濟區農業現代化水平的綜合評價[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13,32(4):140-143.
[7]牛若峰. 中國農業現代化走什么道路[J]. 中國農村經濟,2001(1):4-11.
[8]朱春全. 生態位態勢理論與擴充假說[J]. 生態學報,1997,17(3):324-332.
[9]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印發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的通知[J]. 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報,2010 (4):5-26.
[10]謝花林,鄒金浪,彭小琳. 基于能值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耕地利用集約度時空差異分析[J]. 地理學報,2012,67(7):889-902.
[11]Hutchinson G E.Concluding remarks[J]. Cold Spring Harbor Symp Quant,1957,22:70-72.
[12]向延平. 基于生態位理論的旅游發展關系分析——以武陵源風景區為例[J]. 應用生態學報,2010,29(6):1315-1320.
[13]向延平,向昌國,陳友蓮. 生態位理論在張家界市主要旅游景區評價中的應用[J]. 經濟地理,2009,21(5):1048-1050.
[14]趙旭斌,郁二蒙,王廣軍,等. 基于生態位和水質因子的草魚兩種混養模式的比較[J]. 生態學雜志,2010,29(11):2187-2191.
[15]李 丁,李平安,王 鵬. 基于ESDA的甘肅省縣域經濟空間差異分析[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9,23(12):1-5.
[16]辛良杰,李秀彬,談明洪. 2000—2010年我國農業化肥施用的時空演變格局[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3,18(5):21-27.
[17]謝春訊,吳 忠,彭本紅. 基于生態位理論的第三方物流合作關系模型研究[J]. 商場現代化,2006(25):104-106.
[18]周 毅,劉常林. 基于生態位態勢理論的我國區域體育產業發展特征研究[J]. 體育科學,2013,33(11):5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