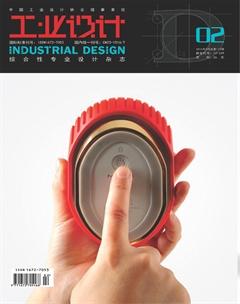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
王冰華
摘 要:如何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因素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一種方法是以源語文化為導向,另一種是以目的語文化為導向。本文通過分析對比《紅樓夢》兩個譯本中一些典型文化因素采用不同翻譯策略達成的不同效果,指明應依據具體的翻譯目的等情況來確定翻譯策略,并且同一作品中應主要遵循同一種策略。
關鍵詞:文學;文化因素;翻譯策略;異化;歸化
當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差異較大時,關于如何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翻譯界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提倡“異化”(alienation),以出發語為導向,另一種提倡“歸化”(adaptation),以譯入語為導向。文學翻譯采用“歸化”策略,還是“異化”策略,是每個譯者不可回避的問題。
1 文學翻譯的文化因素
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是文化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一部文學作品從一種文字轉換為另一種文字的過程中,原語文字中承載的文化信息也隨之進入了譯入語的文化系統,這就是文化因素。從文化因素的角度來分析“異化”和“規劃”這兩種策略,有助于我們認識這兩種策略的在翻譯活動中的作用。
隨著翻譯研究的深入,文化因素在翻譯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翻譯不只是一種語際轉化,在深層意義上它更是一種跨文化轉換。一般來說,來自異域的文化信息,在被轉換到另一種語言體系時,由于語言文化的不同,其意義都要經歷一定程度上的變化。比如“God”一詞, 在西方通指基督教所崇奉的人和萬物的創造者,是人格化的神,翻譯成中文是“上帝”。但對于大多數不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來說,“上帝”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同“God”在西方人腦海中的形象有非常大的區別。即使采用音譯這種被認為最“忠實的方法”,也不能實現文化因素的完全對應。
2 文化差異的緣由
語言是思維外化的載體,是思維的工具。思維方式的不同,影響著中西方語言的表達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的差異。許多人對中西方民族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做過研究,其中包括季羨林、錢穆等學貫中西的大家。季羨林先生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認為:“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相異者更為突出。據我個人的看法,關鍵在于思維方式,東方重綜合,西方重分析。”(謝龍,1995 :19-20)賈玉新先生認為,西方民族的思維模式以邏輯、分析、線形為特點,東方民族的思維以直覺的整體性與和諧的辯證性著稱于世。“西方人見長于分析和邏輯推理,因此思維模式呈線式;而東方人長于整體,他們豐富于想象和依靠直覺,因此可以講是一種圓式思維模式。”(賈玉新,1997:98-100)
由于所處的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環境不同,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語言表達自然也不同。即使有對等的意義,中西方語言上也體現出不同的表達方式。比如漢語成語“一箭雙雕”對應的英語成語是“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兩鳥),成語“掌上明珠 ”對應的是英語里的“the apple of ones eyes”,“對牛彈琴”對應著“to cast pearls in front of the swine”(在母豬面前撒珍珠) 。雖然含義大體相近,但語言表卻大相徑庭。
3 《紅樓夢》兩種譯本的比較分析
出于對作者的意圖,翻譯的目的,讀者要求的考慮,歸化和異化這兩種策略有其各自的價值。《紅樓夢》這部著作蘊含了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楊憲益和其夫人合譯的版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 )以及戴維·霍克斯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這兩種譯本最能體現譯者的翻譯觀以及對“歸化”“異化”兩種策略的應用。
3.1 書名的翻譯
關于書名《紅樓夢》-Dream in a Red Chamber 只是字面的翻譯,而中文“紅樓夢”三字就能引起讀者無盡的想象,這是英文名無法表達出來的。而霍克斯則采用了《紅樓夢》的別名---《石頭記》譯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來避免中英文化上的沖突。霍克斯在譯本的序中提到,法譯本、德譯本、意大利文譯本以及俄譯本的書名,都譯成了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在他看來,這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誤解,因為在他們的頭腦中,“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的意思就是“一個人睡在一間紅顏色的房間里”,也能引起神秘的聯想,可惜卻不是中文名的意思。在必須把“紅樓夢”這三個字譯成英文的時候,霍克斯譯成了“黃金時代的夢”(the dream of golden days)。
3.2 諺語的翻譯
俗語中文中四字成語,歇后語,俗語的使用很廣泛,特別是《紅樓夢》成書的那個時代,成語,四字格,俗語等在原著中更是俯拾皆是,楊憲益先生和霍克斯對此的處理也體現了兩位譯者不同的翻譯策略。
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曹:95)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Yang: 90)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Hawkes: 152)
宗教信仰也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經典著作,充滿了佛教和道教的意識。楊憲益先生在翻譯中套用了英語中的一個諺語,但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從而保留了源語的宗教特點。而霍克斯則采用了“歸化”的策略,直接使用了這句英語諺語未加任何改動,把源語中的佛教色彩改成了基督教色彩。霍克斯的這種表達更容易使目的語的讀者接受,但卻從譯文中讀不到原著中的文化特色。這樣一來,霍克斯把一個信佛的人變成了一個信耶穌的人。
3.3 文化背景的翻譯
不同的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不同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和思想意識等。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語言的表達上也有差異。
例如: 情人眼里出西施(曹:145)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Yang:681)
“Beauty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Hawkes:588)
而在例中,兩位譯者都用英語諺語替代了漢語諺語,都采用了“歸化”的策略。這是因為漢英兩種文化的差異,想在譯文中保留源語文化的因素有的時候會很困難,除非是為了專門介紹中國文化而采用直譯加注的方法。
4 結語
從前文的譯例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翻譯策略產生了不同的翻譯效果。楊憲益先生的譯本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語文化為導向的原則,即采用了“異化”的策略,使西方讀者盡可能多的了解中國文化;而霍克斯的翻譯遵循了以目的語文化為導向的 “歸化”策略,使一般的英美讀者更容易理解。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同一種翻譯標準的指導下,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的選擇可以是多樣化的,譯者應依據具體的翻譯情況來決定采用“歸化”,還是采用“異化”。但采用這兩種翻譯策略時一定要把握好“度”,萬不可“顧此失彼”,亦或“過猶不及”。 對譯者來說,重要的是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識,即意識到兩種文化的異同,“歸化”還是“異化”策略的選擇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在同一部作品的翻譯中應主要遵循一種策略。
參考文獻:
[1] 張琪.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評《語性理論與文學翻譯》[J].考試與評價: 大學英語教研版.2012(02):86-88.
[2] 程曉.文化翻譯理論在兒童文學翻譯中的應用[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8(03):141-143.
[3] 解華.文學翻譯理論的系統探索——簡評鄭海凌先生的《文學翻譯學》[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08):54-55.
[4] 趙越.眾里尋他千百度——基于詩學原理的中國傳統詩歌翻譯理論芻議[J].今日中國論壇.2013(Z1):182-183.
[5] 付姣.俄羅斯文學翻譯理論中文藝學派與語言學派對比分析[J].綏化學院學報.2012(04):143-144.
[6] 鄧璐璐.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及其批評[J].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8(04):124-128.
[7] 蔡新樂,徐廣聯.翻譯是一種對應(Correspondence)——關于翻譯學的一個設想[J].黃淮學刊: 社會科學版.1993(01):68-72.
[8] 李泮池.從風格翻譯理論角度談《傲慢與偏見》的譯本[J].語文建設.2012(06):22-23.
[9] 方銘.翻譯中的視角轉換及文化因素——孫藝風《視角 闡釋 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評介[J].外國語言文學研究.2007(01):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