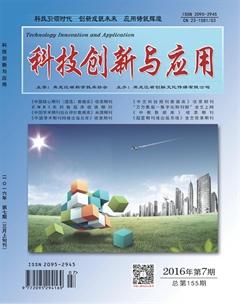巴戟天性能與功效的本草考證
王倩 李耿 倪晨 吳慶光
看入五臟,結合性味,與“安五臟”、“補中”、“強筋骨”、“治小腹陰中引痛”等功效對應。功效方面,明以前巴戟天的功用忠于《本經》、《名醫別錄》的原文記載,明清開始,歷代醫藥家對巴戟天的功效增補了“利水消腫、除濕”之功效,在應用方面增補了“水腫、嗽喘,溲血,腰痛痹痿,眩暈,泄瀉,食少,目疾,耳聾”。
關鍵詞:巴戟天;本草;性能;功效
巴戟天又名巴戟(《本草圖經》),雞眼藤、黑藤鉆、糠藤、三角藤(《中藥大辭典》),巴吉天、戟天、巴戟肉(《藥材學》),雞腸風、貓腸筋、兔兒腸(《中藥志》)[1]。它是我國著名嶺南藥材之一,也是臨床常用中藥之一。目前,關于巴戟天的本草考證多集中于名稱、品種來源、產地、形態特征、采集炮制等方面,在功效主治方面的考證不夠深入,因此,文章力從巴戟天的性能與功效應用方面深入挖掘,探討巴戟天的性能與功用的歷史源流。
1 性能考證
1.1 性味考證
巴戟天始載于東漢時期,《神農本草經》[2]記載: “味辛,微溫”,其后《名醫別錄》[3]:“味甘,無毒”。至唐宋時期及明代,《新修本草》、《開寶本草》、《本草綱目》[4]、《本草蒙筌》[5]、《雷公炮制藥性解》均描述為“辛、甘,微溫,無毒”;張介賓《景岳全書》稱該藥為“味甘微溫,陰中陽也”;《本草經疏》:“巴戟天,……,是當木之令而兼金之用也,故其味辛。《別錄》益以甘,而《本經》又曰微溫無毒,宜其然也”。清代《本草備要》、《本草求真》則記載該藥“甘、辛,微溫”。
1.2 歸經考證
《神農本草經》中并未提及歸經,宋代《圖經衍義本》:“專入腎家”。元代王好古云:“巴戟天,腎經血分藥也”。相關的記載主要集中在明清時期,各家論述不盡相同。《雷公炮制藥性解》:“入脾、腎二經”;《本草經疏》:“巴戟天稟土德真陽之精氣,兼得天之陽和,陽主發散,散則橫行,是當木之令而兼金之用也”;陳士鐸在《本草新編》提及:“入心、腎二經”;《本草經解》:“入足厥陰肝經、足陽明胃經”;《本草備要》、《本草求真》均認為:“入腎經血分”;《本經逢原》:“腎經血分及沖脈藥也”。《本草求原》:“巴戟天,……為腎胃、屬金。沖脈血分之良藥”。《本草崇原》:“稟太陰金土之氣化。其性微溫,經冬不凋,又稟太陽標陽之氣化。……肺主氣而屬金,太陰天氣,外合于肺也。”《得配本草》:“入足少陰經血分”。
根據本草記載,在性味方面,《神農本草經》最初并未提到“甘”味,后世醫家加以補充完善。也與巴戟天具有溫補之功效吻合。其中“味辛,微溫”沿用至今,發揮著溫通之功;歸經方面,根據歷代本草描述,巴戟天以入腎經為主,尤其是在宋元時期,多強調專入腎經。到明清時期,又增加歸脾經、胃經、心經、肝經、肺經和沖脈的認識,完善了入五臟的歸經認識,與 “安五臟”、“補中”、“強筋骨”、“治小腹陰中引痛”等功效對應,并進一步擴展了明清時期功效的運用范圍。
2 功用考證
2.1 東漢時期
《神農本草經》將巴戟天列為上品:“主治大風邪氣,陰痿不起,強筋骨,安五臟,補中,增志,益氣”;《名醫別錄》增補了“主治頭面游風,小腹及陰中相引痛,下氣,補五勞,益精,利男子”[2、3]。
2.2 唐代
《新修本草》[6]將《本經》與《名醫別錄》的論述加以綜合:“主大風邪氣,陰萎不起,強筋骨,安五臟,補中,增志,益氣。療頭面游風,小腹及陰中相引痛,下氣,補五勞,益精,利男子”;《備急千金要方》取前人論述之功效,用巴戟天等藥物組方成“腎瀝散”,稱之為“虛勞百病方”,亦用巴戟天配伍肉蓯蓉等組成“蓯蓉補虛益氣方”, 主治“五臟虛勞損傷,陰痹,陰下濕癢,或生瘡,莖中痛,小便余瀝,四肢虛極,陽氣絕,陽脈傷”,強調了巴戟天的補益之功。甄權在《藥性論》中對功用加以補充:“能治男子夜夢鬼交泄精,強陰,除頭面中風,主下氣,大風血癩”。[7]
2.3 宋代
《日華子本草》記載:“安五藏,定心氣,除一切風,治邪氣,療水腫”;《太平圣惠方》中的“巴戟散”,主治“虛勞,腰腳疼痛,行立不得”[8]。《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運用巴戟丸“補腎臟,暖丹田,興陽道,減小便,填精益髓,駐顏潤肌”;《本草衍義》:“有人嗜酒,日須五七杯,后患腳氣甚危,或教以巴戟半兩,糯米同炒,米微轉色,不用米,大黃一兩, 炒,同為末,熟蜜為丸,溫水服五七十丸,仍禁酒,遂愈”。
2.4 金代
劉完素在《宣明論方》中記載治療“腎氣虛弱、語言謇澀、足膝酸軟”的“地黃飲子”亦有巴戟天。
2.5 明代
《本草綱目》[4]:“治腳氣,去風疾,補血海”;《景岳全書》:“雖曰足少陰腎經之藥,然亦能養心神,安五臟,補五勞,益志氣,助精強陰。治陰痿不起,腰膝疼痛,及夜夢鬼交,遺精尿濁,小腹陰中相引疼痛等證”。并用含巴戟天的贊育丹治療“陽痿精衰,陰寒不育”。《雷公炮制藥性解》:“主助腎添精,除一切風及邪氣”;《本草蒙筌》[5]:“禁夢遺精滑,補虛損勞傷。治頭面游風,乃大風浸淫血癲;主陽痿不起,并小腹牽引絞痛。安五臟健骨強筋,安心氣,利水消腫。益精增志,惟利男人。”《本草經疏》:“其主大風邪氣,及頭面游風者,風為陽邪,勢多走上,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巴戟天性能補助元陽而兼散邪,況真元得補,邪安所留?此所以愈大風邪氣也。主陰痿不起,強筋骨,安五臟,補中增志益氣者,是脾腎二經得所養而諸虛自愈矣。其能療少腹及陰中引痛,下氣并補五勞,益精利男子者,五臟之勞腎為之主,下氣則火降,火降則水升,陰陽互宅,精神內守,故主腎氣滋長,元陽益盛,諸虛為病者不求其退而退矣。”《本草新編》:“巴戟天正湯劑之妙藥,溫而不熱,健脾開胃,既益元陽,復填陰水,真接續之利器,有近效而又有速功”。
2.6 清代
《本草求真》[9]:“溫補腎陽,兼祛風濕。巴戟天專入腎……據書稱為補腎要劑,能治五癆七傷,強陰益精,以其體潤故耳。……然氣味辛溫,又能祛風除濕,故凡腰膝疼痛,風氣腳氣水腫等癥,服之更為有益”。《本草備要》:“補腎,祛風。甘辛微溫。入腎經血分、強陰益精,治五勞七傷;辛溫散風濕,治風氣、香港腳、水腫”;嶺南本草專著《本草求原》在評價總結前人的論述外,亦認為:“巴戟天,即不凋草。經冬不凋,故達陽更能生陰,……凡元陽衰,陰精亦虧,不受剛燥者宜之”,此外,補充了治療“嗽喘,溲血,腰痛痹痿,眩暈,泄瀉,食少,目疾,耳聾,尿不禁,皆上達下歸,元氣周流之效。此乃元氣之主劑,立其主,可隨寒熱而佐之,以達下焦之主氣,故磁石丸益腎陰、蓯蓉丸益腎陽俱用。相火盛,大便燥,忌之”。《傅青主女科》在溫胞飲、調肝湯中亦加入了巴戟天溫補調經。《本草崇原》論述:“主治大風邪氣者,得太陰之金氣,金能制風也。治陰痿不起,強筋骨者,得太陽之標陽,陽能益陰也。安五臟,補中者,得太陰之土氣,土氣盛,則安五臟而補中。增志者,腎藏志而屬水,太陽天氣,下連于水也。益氣者,肺主氣而屬金,太陰天氣,外合于肺也。”
2.7 民國時期
《本草正義》:“溫養元陽,則邪氣自除,起陽痿,強筋骨,益精,治小腹陰中引痛,皆溫勝寒之效;安五臟,補五勞,補中,益氣,皆元陽布護之功也”。
縱觀諸多本草論述,結合現今對巴戟天功用的描述“補腎陽,強筋骨,祛風濕。用于陽痿遺精,宮冷不孕,月經不調,少腹冷痛,風濕痹痛,筋骨痿軟”[10],從《本經》開始,巴戟天治療“陰痿不起、強筋骨、增志、暖丹田,興陽道,減小便,填精益髓”等主要功用沿用至今,與現在的“補腎陽,強筋骨,治療健忘”等描述一致。在明以前,關于巴戟天的功用記載基本忠于《本經》、《名醫別錄》的原文描述,明清開始,歷代醫藥家對巴戟天的功效增補了“利水消腫、除濕”之功,在應用方面增補了“水腫、嗽喘,溲血,腰痛痹痿,眩暈,泄瀉,食少,目疾,耳聾”。古之“主大風邪氣”演變為今之“祛風濕”,而“安五臟”的古代論述現今多強調“補肝腎”,目前,仍然有一些本草記載的功效在當今沒有被廣泛關注運用。如:
(1)“主治大風邪氣”中,除療風濕,是否還適用于其他風邪證?當今鮮有論治頭面游風的臨床報道。
(2)古之“安五臟、補中”,現今除了補益肝腎,亦鮮見補益他臟的臨床運用。
(3)因氣候變遷,產地由北向南轉移,魏晉至清前期,主產于四川(巴郡、建平、宜都、歸州)、蘇皖,清末轉至江南(江西、浙江、廣東),近代主要集中在華南(廣東、廣西、福建)。從古至今的產地和品種發生了變化,也有可能出現功效的差異。不同品種的藥材功效有何不同?望本次巴戟天的考證可拋磚引玉,為后續進一步研究巴戟天的功用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梅全喜.廣東地產藥材研究[M].廣東:廣東科技出版社,2011.
[2](清)顧觀光.神農本草經[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3]陶弘景.名醫別錄[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4]李時珍.本草綱目[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
[5]陳嘉謨.本草蒙荃[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
[6]蘇敬.新修本草[M].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
[7]陳彩英,詹若挺,陳蔚文.南藥巴戟天源流考證[J].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26(2):181-187.
[8]程春松,程明,郭友平,等.基于古文獻中圖版的藥用植物巴戟天考證[J].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2014,20(24):237-242.
[9]黃宮繡.本草求真[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
[10]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華本草》編委會.中華本草[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