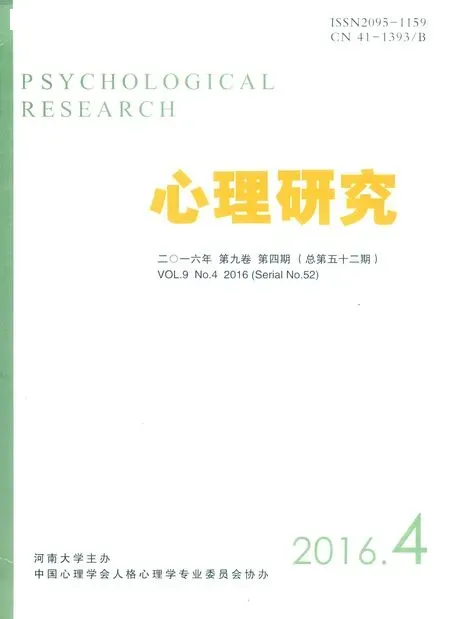不同管理模式下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
馬露露 馬紅宇 梁 娟 楊林川 高 記
(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武漢 430079)
不同管理模式下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
馬露露馬紅宇梁娟楊林川高記
(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武漢 430079)
研究旨在探討在權威決定與制度決定兩種不同管理模式下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對結果接受性的影響。以社會交換理論為理論基礎,采用大學生獎學金評定實驗情境,以兩種管理模式為背景因素,通過2(權威信任:高/低)×2(程序公正:高/低)的被試間設計探討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結果發現,權威決定情境下,權威信任調節程序公正效應,在權威信任較高的條件下,程序公正能夠顯著提升結果接受性,在權威信任較低的條件下,無論程序是否公正,被試的結果接受性普遍較低;制度決定情境下,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的調節效應不顯著,且權威信任與程序公正均能正向預測結果接受性。
權威決定;制度決定;程序公正;權威信任;結果接受性
1 問題提出
社會公正是維持社會穩定發展的前提與基礎。社會改革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社會不平等、貧富分化、城鄉差距逐漸拉大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各種社會風險和社會矛盾凸顯,群體性事件頻發[1,2]。如何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提升個體對相關政策引發的結果的接受性是關鍵。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是影響組織成員態度與行為的關鍵變量,Cremer和Tyler的研究發現,權威信任調節程序公正與合作行為之間的關系[3]。然而,中國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各類企業呈現出多元化管理模式。我國立法逐漸完善,在政府及企業管理等層次基本上達到“有法可依”“有制度可依”。然而,在社會改革不斷推陳出新、某些領域的法制建設依然不夠完善的情況下,決策結果往往取決于權威。在現代企業運作中,當采用團隊合作模式進行管理時,團隊領導往往具有很大的分配權與決策權。這便體現了“法制”與“人治”兩種不同的管理模式,具體到執行方式上即為制度決定和權威決定。本文探討兩種不同管理模式下,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
公正心理學的研究起源于1965年亞當斯的公平理論,關注資源分配的結果是否公正。Thibaut和Walker通過對法律程序的研究指出,人們不僅關心分配的結果公正與否,還關心用于決定資源分配的過程是否公正,即程序公正。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程序公正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與態度,如工作滿意度、組織公民行為等,程序公正對相應結果變量的影響效果這一關系即程序公正效應(procedural justice effect)[4-7]。信任和程序公正作為影響組織成員態度與行為的關鍵變量,兩者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組織公正領域的研究熱點[8,9]。Van den Bos,Wilke和Lind以公平啟發理論(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為依據,發現權威信任信息的有無調節程序公正效應[10]。當權威信任的相關信息缺失時,個體更加在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能夠影響個體的公正判斷和結果滿意度;當呈現權威信任的相關信息時,程序公正則不會對個體產生影響。在現實情境中,由于個體與權威之間的長期互動,個體往往在獲得程序對待信息之前便已形成權威是否可信的判斷。因此本研究關注權威信任的高低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
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為程序公正效應提供了一種解釋:員工將公正視為值得交換的利益。程序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員工的利益,因此促進了員工對權威的信任以及進一步的合作行為。社會交換理論進一步指出,社會交換的質量在公正與合作行為之間起著關鍵作用,而信任則是保證交換質量的基礎[11]。一系列的元分析表明,信任與公正之間存在適度正相關,并且兩者是相互影響的[12,13]。權威信任是指在多大程度上人們相信權威(領導、上級)關心其福祉,并且會基于成員的利益行事[3,14]。在組織情境中,員工已經形成權威是否可信的判斷,只有在權威信任較高的情況下,才能保障交換的質量,因此權威信任調節程序公正效應。De Cremer的研究發現,領導者偏見調節程序公正與公正判斷之間的關系,當領導者被感知為無偏的時候,程序公正影響個體的公正判斷,但當領導者被感知為有偏的時候,此時個體普遍認為領導是不公正的[15]。De Cremer和Tyler通過實驗室實驗、組織或社會背景下的調查,發現權威信任調節程序公正與合作行為之間的關系,只有在權威信任較高的條件下,權威執行公正才能預測員工和民眾的合作行為[3]。這一研究開始關注情境因素的重要性,但只是將研究調查放在籠統的組織背景或社會背景下進行,而對于某一背景所反映的具體情境因素并未展開探討,本研究擬結合中國背景下兩種不同的管理模式,探討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機制。
從權利保障的視角看,封建社會人民的權利保障主要依賴于傳統的君王,法治社會下,人民權利的保障則依賴于具體的法律法規[16]。具體到中國現代社會管理模式下,由權威決定決策過程及分配結果的管理模式即權威決定。“人治”思想源于中國儒家文化,強調依靠統治者個人的權威治理國家。孔子言“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反映了權威信任的重要性。現代企業運行強調團隊合作模式,賦予團隊領導較多的管理權限;而華人企業則具有泛家族人治文化,領導往往集權力于一身[17]。權威信任建立了一種選擇性知覺,當組織成員具有較高的權威信任時,成員相信權威會保護其利益,不會做出違反組織成員利益及組織規范的行為[18]。當權威信任水平低時,程序公正會被個體知覺為一種印象管理策略[19]。因此,在權威決定的管理模式下,權威信任是影響民眾公正感知的關鍵變量。正如社會交換理論所提出的,信任是保障交換的基礎,只有在權威信任較高的條件下,程序公正才會提升民眾的結果接受性;在權威信任較低的情況下,程序公正不會對民眾的結果接受性產生影響。
假設1:在權威決定情境下,權威信任調節程序公正與結果接受性的關系。
按照制度及管理規章決定決策過程及分配結果的管理模式即制度決定。制度決定背景下,無論是社會情境還是組織情境,決策結果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管理規范依據。在此種背景下,制度本身就是對交換質量的有力保障,程序公正將是影響個體結果接受性的主要因素。此種背景下,權威作為相關部門的代表宣布結果,較高的權威信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個體的態度,提升其結果接受性。
假設2:在制度決定情境下,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正向預測結果接受性。
本文關注兩種不同管理模式下的程序公正問題,由于研究情境需要涉及某種具體的制度執行情境,本研究擬以大學生為被試,選取涉及學生切身利益的獎學金評選這一典型情境。而輔導員在學生群體中能夠較好地代表權威,繼而操縱權威決定和制度決定兩種不同的管理模式,從而探討兩種不同的管理模式下,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機制。
2 研究方法
為了更好地操作權威決定與制度決定情境下的程序公正,對255名大學生進行了不同情境下公正原則相對重要性的前測。權威決定情境使用如下指導語:“從學校獲悉,明年開始我校的獎學金評選權力將下放到各院系的輔導員手中,完全由輔導員決定最終的評選結果”,共121人。制度決定情境使用如下指導語:“從學校獲悉,明年開始我校的獎學金評選,將嚴格按照統一的《獎學金評定細則》進行,輔導員手里沒有任何自主權,評選結果完全由評定細則決定”,共134人。然后請被試對自編的19條目、五因素(領導無偏、公開透明、調查民意、客觀真實、可修正性)程序公正問卷①問卷源自高記(2010)的博士論文,主要探討中國背景下的程序公正問題。問卷的信效度良好,α=0.85。各項目的重要性進行評價。結果發現權威決定情境下,大學生更注重民意調查;制度決定情境下,大學生更注重公開透明。因此,權威決定情境下的程序公正通過是否進行民意調查進行操縱,制度決定情境下的程序公正通過是否公開透明進行操縱。
2.1被試
權威決定情境下正式樣本為131人,均為某高校公共心理學課堂的學生。平均年齡為20.47歲(SD=0.96),其中男生41人,女生90人,有71人申請過獎學金。
制度決定情境下正式樣本為89人,均為武漢某高校的學生。平均年齡為20.90歲(SD=2.12),其中1人年齡數據缺失。男生28人,女生61人,有50人申請過獎學金。
2.2實驗設計
采用2(權威信任:高/低)×2(程序公正:高/低)的被試間設計。運用情境故事(scenarios)的方法,通過對獎學金評選情境的描述對自變量進行操縱。
2.3實驗材料和程序
實驗過程為集體施測。通過指導語告訴被試,他們會讀到一則關于獎學金評定的描述,假設他們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并且提交了獎學金申請材料。要求認真閱讀故事,盡量將自己投入到描述情境中,然后根據自己經歷該情境后的感受作答。
權威決定情境描述如下:李華所在的學校每年均會進行獎學金評選活動,學校把獎學金評選的權力下放到各院系的輔導員手中,完全由輔導員決定最終的評選結果。
制度決定情境描述如下:李華所在的學校每年均會進行獎學金評選活動,學校嚴格按照統一的《獎學金評選制度》進行,評選結果完全由評選制度決定,不受輔導員的影響。
權威信任的操作:李華所在院系的輔導員是值得信任的/不可信的,在日常的學生工作中,盡量/沒有以一種使多數人都滿意的方式解決問題,學生普遍相信/不相信該輔導員會考慮每位學生的利益。
權威決定情境下程序公正操作如下:該輔導員在評選過程中的一貫的風格是注重/不注重征求廣大同學的意見。
制度決定情境下程序公正操作如下:學校每年的評選活動都是在有/沒有學生監督的情況下進行,公布/不公布所有的評選細節。
反應量表包括被試感知到的獎學金評選方式(1代表完全由輔導員決定,7代表完全由獎學金評選制度決定)、民意調查程度/公開透明程度和權威信任程度,目的是為了檢驗對情境及自變量的操縱是否有效,分別由一個題目來測量;四個項目測量程序公正判斷,“獎學金評選這樣做,總的來說是合理/公平/合適/公正的”。兩個項目測量結果接受性,“我愿意接受/尊重這種做法所產生的結果”。所有量表均采用7點計分。
3 結果分析
3.1權威決定情境下相關結果分析
3.1.1操作檢驗
對權威決定情境進行操作檢驗,被試對獎學金評選方式的判斷均值為2.95(SD=1.56)。可見權威決定情境下被試認為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輔導員決定的。
對權威信任進行2×2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權威信任的主效應顯著,F(1,127)=52.17,p<0.001,η2= 0.28。高權威信任組被試的權威信任感顯著高于低權威信任組(M高=4.47,M低=2.76)。程序公正的主效應顯著,F(1,127)=4.99,p<0.05,η2=0.03。高程序公正組被試的權威信任顯著高于低程序公正組(M高= 3.88,M低=3.35)。交互效應不顯著。De Cremer和Tyler實驗中程序公正操作同樣對權威信任產生了影響,由效應量可知,權威信任的操作是有效的。
對程序公正進行2×2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程序公正的主效應顯著,F(1,127)=75.80,p<0.001,η2= 0.37。高程序公正組被試感知到的評選過程中的民意調查顯著高于低程序公正組 (M高=4.36,M低= 2.36)。為了進一步檢驗通過民意調查操縱程序公正的有效性,以程序公正判斷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t(129)=5.27,p<0.001,Cohen’s d=0.93。高調查民意組的得分顯著高于低調查民意組的得分(M高=3.78,M低=2.43),表明對調查民意這一原則進行操縱達到了對程序公正進行操縱的目的。
3.1.2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調節作用
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對結果接受性進行2× 2方差分析,結果表明,程序公正的主效應顯著,F(1,127)=25.22,p<0.001,η2=0.14。高程序公正組的結果接受性顯著高于低程序公正組被試的結果接受性(M高=4.17,M低=2.91);權威信任的主效應顯著,F(1,127)=28.99,p<0.001,η2=0.16。高權威信任組被試的結果接受性顯著高于低權威信任組(M高=4.21,M低=2.86);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的交互作用顯著,F(1,127)=4.00,p<0.05,η2=0.02。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發現高權威信任條件下,程序公正主效應顯著,F(1,127)=19.60,p<0.001,η2=0.13;低權威信任條件下程序公正主效應不顯著,F(1,127)=3.78,p>0.05。這驗證了假設1(見圖1)。
3.2制度決定情境下相關結果分析
3.2.1操作檢驗
對制度決定情境進行操作檢驗,被試對獎學金評選方式的判斷均值為5.24(SD=1.48),可見制度決定情境下被試認為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評選制度決定的。
對權威信任進行2×2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權威信任的主效應顯著,F(1,85)=20.89,p<0.001,η2= 0.19。高權威信任組被試的權威信任顯著高于低權威信任組(M高=4.81,M低=3.35)。
對程序公正進行2×2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程序公正的主效應顯著,F(1,85)=12.56,p=0.001,η2= 0.13。高程序公正組被試感知到的評選過程中的公開透明程度顯著高于低程序公正組 (M高=4.22,M低=3.80)。為了進一步檢驗通過公開透明操縱程序公正的有效性,以程序公正判斷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t(87)=7.27,p<0.001,Cohen’s d=1.56,公開透明組的得分顯著高于未公開透明組的得分(M高=5.11,M低=2.97),表明對公開透明這一原則進行操縱達到了對程序公正進行操縱的目標。

表1 權威決定背景下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對公正判斷和結果接受性的影響(M±SD)

圖1 權威信任與程序公正對結果接受性的交互作用
3.2.2描述性統計結果
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對結果接受性進行2×2方差分析,結果表明,程序公正的主效應顯著,F(1,85)=28.50,p<0.001,η2=0.22。高程序公正組的結果接受性顯著高于低程序公正組被試的結果接受性(M高=5.22,M低=3.51);權威信任的主效應顯著,F(1,85)=15.70,p<0.001,η2=0.12。即高權威信任組被試的結果接受性顯著高于低權威信任組(M高=5.00,M低=3.73);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1,85)=1.11,p>0.05。這驗證了假設2。

表2 制度決定背景下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對公正判斷和結果接受性的影響(M±SD)
4 討論
當前研究通過獎學金評選情境實驗探討不同管理模式下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研究發現,權威決定情境下,權威信任調節程序公正效應,只有在被試具有較高權威信任的條件下,程序公正才能夠提升被試的結果接受性,在權威信任較低的條件下,被試的結果接受性普遍較低;制度決定情境下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均可以提高被試的結果接受性。
公正與信任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研究者的關注熱點,當前研究者多從信任的概念結構及理論整合角度出發,對公正、信任與合作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進行解釋[1,11,20-21]。本文則從兩種實踐管理背景出發,探討不同管理模式下,權威信任與程序公正對個體態度及行為的影響,發現不同管理背景下,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存在不同的作用機制。因此,未來研究在探討公正與信任之間的關系時,應結合具體的情境因素,以更加準確地探明兩者之間的關系。同時,還應關注中國背景下的公正研究,如權力距離、服從特質等對民眾態度及行為的影響,進而更好地指導實踐。
本文研究結果與De Cremer和Tyler的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該研究實驗1和實驗2所采用的情境均是由指定的權威進行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權威決定的管理模式。研究3和研究4則通過問卷調查,探討社會情境和組織情景下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機制,同樣驗證了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調節作用[3]。雖然De Cremer和Tyler關注到情境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并未探討具體情境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則結合中國背景下政府及企業管理實踐,通過區分兩種不同的管理模式,即人治與法治,探討了權威信任在兩種情境下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機制。選取獎學金評選情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由于各學校乃至各學院獎學金評選流程存在很大的差異,學生對獎學金評選的公平感知差異較大,使得利用這一情境操縱兩種不同的管理方式具有可行性與真實性。
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政府管理方面,在處理制度以外的社會爭端時,在保證程序公正的同時應充分注重營造政府公信力以及營建代表人物的權威信任度;企業管理方面,在給予中層干部管理權限的同時要保證其能夠公平地對待員工,選拔具有較高信任度的領導干部才能更好地促進組織發展。在制度決定的情景下,提高權威信任依然能夠提升結果接受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法治背景下,民眾對權威的期待。當今社會反腐與法治建設同步進行,對于提升民眾公正感進而促進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實驗設計的限制,當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當前研究為情境實驗,由于研究中設置的管理模式是兩種極端的情境,其生態效度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實際情境中決策往往受到制度和權威的雙重影響。如同我國在建設法治社會的同時在解決問題時依然強調“合情合理”,很注重人的變通性和靈活性。雖然我國政府及企業管理在多數情況下已經做到“有法可依”“有制度可依”,但是考慮到目前法治建設尚處于初期,且受到傳統人治思想的影響,權威信任在制度執行過程中依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未來研究應進一步結合現實情境,探討權威信任對程序公正效應的影響。第二,以大學生為被試,并以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獎學金評選為情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會背景下民眾對涉及其利益的事件的反應。未來研究還應進一步以社會調查的形式探討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對民眾態度及行為的影響。
5 結論
當前研究通過獎學金評選情境實驗發現,在權威決定情境下,權威信任調節程序公正與結果接受性之間的關系,只有在權威可信的條件下,權威執行程序公正才能提高大學生對獎學金評選結果的接受性;在制度決定情境下,程序公正與權威信任均可正向預測被試的結果接受性。
1張書維,許志國,徐巖.社會公正與政治信任:民眾對政府的合作行為機制.心理科學進展,2014,22(4):588-595.
2張書維,王二平,周潔.跨情境下集群行為的動因機制.心理學報,2012,44(4):524-545.
3De Cremer D,&Tyler T R.The effects of trust in author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on cooperation.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7,29(3):639-649.
4Thibaut JW,&Walker L.Procedural justice:A psychological analysis.L.Erlbaum Associates,distributed by the Halsted Press Division of Wiley,1975.
5Heslin P A,&Walle D V.Performance appraisal procedural justice:The role of a manager’s implicit person theory.Journal of Management,2011,37(6):1694-1718.
6van Dijke M,De Cremer D,Mayer DM,et al. When does procedural fairness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behavior?Integrating empoweringleadership types in relational justice model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2,117(2):235-248.
7梁娟,馬紅宇,高記.自我不確定感對程序公正效應的調節作用:回顧與展望.心理科學進展,2013,21(3):530-538.
8De Cremer D,&Tyler T R.Managing group behavior:The interplay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sense of self,and cooperation.In M.Zanna(Ed.),Advances in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NewYork:Academic Press,2005,(37):151-218.
9張婍,王二平.社會困境下政治信任對公眾態度和合作行為的影響.心理科學進展,2010,18(10):1620-1627.
10Van den Bos K,Wilke H A M,&Lind E A.When do we need procedural fairness?The role of trust inauthor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5(6):1449-1458.
11Colquitt J A,Scott B A,Rodell J B,et al.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a decade later:Ameta-analytic test of social exchange and affect-base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3,98(2):199-236.
12Colquitt J A,Conlon D E,Wesson M J,et al.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25 year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1,86(3):425-445.
13Sepp?l?T,Lipponen J,Pirttil-Backman A M,et al. A trust-focused model of leaders’fairness enactment. Journal of Personnel Psychology,2012,11(1):20-30.
14van Dijke M,&Verboon P.Trust in authorities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to procedural fairness effects on tax compliance.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10,31(1):80-91.
15De Cremer D.The influence of accuracy as a function of leader’s bias:The role of trustworthiness in the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4,30(3):293-304.
16魏建國.再論中英兩國的人治與法治傳統——以權利保障方式的不同為分析視角.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2,(2):22-31.
17楊國樞.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見楊國樞,余安邦(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87-142.
18Brown G,Crossley C,&Robinson S L.Psychological ownership,territorial behavior,and being perceived as a teamcontributor:T he critical role of trust in the workenvironment.Personnel Psychology,2014,67(2):463-485.
19Greenberg J.Looking fair versus being fair:Managing impression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0,12:111-157.
20Colquitt J A,&Rodell J B.Justice,trust,and trustworthiness:Alongitudinal analysis integrating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6):1183-1206.
21Colquitt J A,LePine J A,Piccolo R F,et al.Explaining the justice-performance relationship:Trust as exchange deepener or trust as uncertainty reducer?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2,97(1):1-15.
The Influence of Trust in Authority on Procedural Justice Effect under Two Different Management Contexts
Ma Lulu,Ma Hongyu,Liang Juan,Yang Linchuan,Gao Ji
(School of Psycholog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rust in authority on people’s outcome acceptance under two different management modes,authority determined and institution determined.Using the scholarship selection scenario experiments and the different management modes as background factors,the experiment design was a 2(trust in authority:high/low)×2(procedural justice:high/low)between-subject design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rust in authority on procedural justice effect.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the following:when the outcome was determined by authority,authority trust positive moderate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outcome acceptance.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authority trust,authority enacting procedure justice can improve people’s procedural justice judgments and outcome acceptance.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authority trust,the outcome acceptance was low no matter about the procedural.When the outcome was determined by institution,procedural justice and trust in authority both ha d positive impact on outcome acceptance.
a uthority determined;institution determined;procedural justice;trust in authority;outcome acceptance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研究計劃重點支持項目(91324201)、華中師范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CCNU14Z02015)
馬紅宇,女,教授,博士。Email:mahy@mail.c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