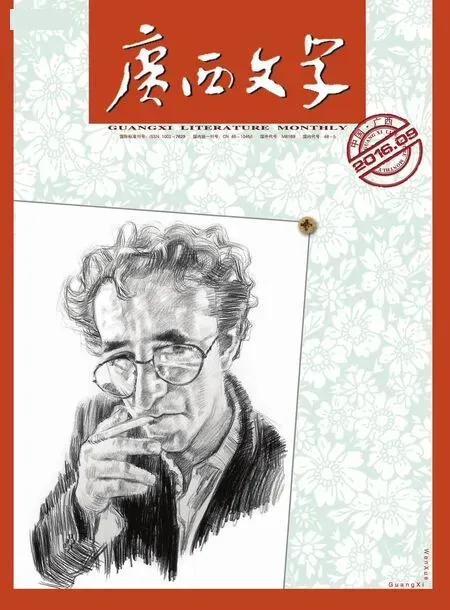溪源和地氣
王云高/著
對題行文,“故鄉”的“故”字以古鑲義,自然屬于歷史上人文景觀的舊話。而本老頭子年屆八十,生于南寧,三歲時因日寇從欽州北犯,作為民團周刊社編輯的父親攜家隨機關北遷桂林。1944年日寇南下,桂林大疏散,改行桂嶺師范教師的父親攜家南下蒙山。直至1950年解放后回到南寧,從此過的是城市居民的現代俗事。因此,居留六年的蒙山便在我心中成了第二故鄉,連當地友人都把我看成“半個蒙山人”。據此,本文便打算敘述那段童年到少年的舊夢。
鯉魚和板栗的回憶
1985年,年將半百的我第三次回到蒙山,為的也是蒙山的往事;1981年我第二次去后還鄉,獲悉蒙山的老同學彭貴康在東鄰昭平當縣委副書記,落實責任制脫貧致富頗有績效,因而寫了個短篇小說《濕引炮燒婿》頌之,沒想到陷入一場文字獄,受到“否定公社化”的指責,后來得到自治區黨委領導乃至蒙山籍的老紅軍陳漫遠出面平了反,《廣西日報》還在1983年5月16日重新發表它以示肯定,我這才三返故鄉,再作交流。這個氛圍當然是溫馨的,父親的學生趙培盛(其兄培正又是我讀高小的老師)親自把我帶回家鄉長坪公社三妹村。
那是一個美麗的瑤寨,我至今還記得培盛哥買了一塊山豬肉,由于下坡的步伐力度太大,穿肉的竹篾居然割斷了脆嫩的豬肉掉到了地上。
這個細節引起了我一連串的回憶:記得1944年日寇侵入縣城時,我家就逃難到此,我還記得那山溪水清冽得可愛;八歲的我在這里學泅水,沉在水底睜開眼睛,居然看到一群小鯉魚在眼前游樂,我伸手抓住了一條紅魚,弄得它痛苦地掙扎,我心一軟就放了它一命。我跟著出水上岸,躺在沙灘上取暖,沒想到一來二去,那一身疥瘡居然被熱沙燙得結痂痊愈了。我還記得,那天在山坡上走,猛然挨刺疼了赤腳,彎腰一看:板栗!野生的,足有乒乓球恁大,我先后撿了五個,拿回家來,奶奶那番高興,因為足足省了兩碗粥!
真是環保啊,四十一年的折騰后復歸,雖然大不如前,但當年的溫馨還相當濃烈,特別是當年游泳的碼頭上還有幾個瑤妹在漂洗長發,我用當地土話撩她們兩句,瑤妹居然都低著頭不說話。
我高興了,當場寫了兩首七絕:
三妹家住紫云邊,半似凡人半似仙;
濯發泉頭分綠澤,染遍千山萬頃田。
坳口花香染白云,蒼苔仰笑古藤根,
天兵北上百余載,村女含羞尚避人。
詩稿寫成,給培盛“斧正”,他很欣賞,進村后跟瑤胞介紹我。
當年的前緣,如今的身份……瑤胞們很高興,請我將這兩首七絕寫下來存念,只是周邊幾家竟然找不到一張可寫字的紙,無奈之下我只能向屋角撿到一張刨花,用鋼筆寫下來了。
這是我這個詩人兼書法家的唯一“創新”。
“山豬送酒”后,夕陽下山了,我們趕緊離去,走過村頭,我還記得那個“十三王娘墳”,兒時聽說是個美人墓,還扯著趙哥繞去一觀,景致小有變化,整齊多了。趙哥告訴我,這是洪秀全一個妃子的墳(當年我們也曉得的),解放后作為革命歷史文物,做過整理,還發現骸骨的頭部蓋著個銅盆,現在藏在縣文物辦了。
我對此略有所知,應答幾句,跟回了縣城。
兩副先人墓聯的筆跡
走回縣城的路基本上是四十年前的舊路。依稀的景色又引起了舊事的“閃回”。
我這個知識分子的一大特色是沒有畢業證,1958年高中還沒畢業就由母校委了教職,甚至連初小也沒讀過,在逃難中度過童年,上不了學,識字和算術只能在職為教師的父親身邊自學成才。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家從瑤山回到縣城,原打算乘船下梧州轉回南寧家鄉,無奈二妹患了肺炎(當時稱急驚風)搶救無效夭折了,因而花盡了家中的款項,全家只好流落蒙山。時年十歲的我當然只能報考高小,而且居然以第十三名的名次考上了城廂中心學校。我至今還記得高小第一學期班主任老師李永成對我的鑒定,“天資穎悟,學習勤奮,唯性孤僻,不大好動”記下了我當時因貧困而抑郁的歷史。但盡管這樣,兩年之后,我仍然以第三十一名考上了蒙山中學三十九班。我還記得第二學期,班主任龍騰老師上國文課,講的是明代文人歸有光的《先妣事略》,文中說及其母年輕時生育能力旺盛,但家境貧困,她就不想多生,但按當時的觀念,生育是婦人對宗族的義務,她欲拒不能,便跟一個老嫗感嘆,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食此,后妊不數矣。”妣食之,喑不能言。

洪秀全紀念館
我對此記得很清楚,直至此前,我還敢不查原著。我記得龍老師讀到這里,用蒙山方言插了一句:“你看,整個人啞了,慘不慘!”
但我在下邊聽著卻別有想法:“二螺”,無非是田螺或石螺,我都吃過,為什么就不啞,而那位“妣”卻發了病變?!
我想她屬于心傷,是心理而不是病理現象。
等到下課,我從后門出了教室,就在當年洪秀全降突圍旨的蘭樹下攔住了龍老師,囁囁嚅嚅地說出了上述想法。
他修長的身子俯下來盯了我幾秒鐘,我慌得渾身顫抖。
但他居然說:“你說的,有道理。”

2014年10月,我的蒙山學生湯展中成婚,我和老伴應邀回去喝喜酒,19日,我們老倆口與“親家”夫婦合照,左起第一人是我老伴,第二人“親家娘”,背景是“天王蘭樹”
而且,在下一節課,他甚至向全班同學公布了這場討論,朗聲說道:“我雖然翻了《康熙字典》,但王云高說得對。”
全班同學頓時環顧過來,須知龍老師當時年近半百,全校老師都稱他“龍老”,在縣城內也大有名氣,居然向一個十二歲的初一生……
從那一刻起,我在縣城里就有了一種另類的色彩。
那天回到縣城,不免憶及此事,其后,20世紀90年代,我還在報上發了一篇隨筆談之。但不久,報社向我傳達了譴責,說龍某已死于土改,姓王的不該為他“樹碑立傳”。
我至今不服。2006年蒙山中學八十周年校慶大會上,我仍在當眾講話中公布了此事:“我歌頌的是師德教風,師生互動是蒙中的優良傳統。”
說到師生感情,我還不能不提及一件逸事,我在成績拔尖之際,但由于前述的家庭經濟困難,第二學期即1949年春,我無錢交學費,只得申請輟學,而時任校長的孔憲銓先生聽到這消息,竟然親做家訪,了解真實的困境之后,他甚至在微薄的薪金中擠出一部分,再發動其他老師甚至家境富裕的同學,湊足了我一學期的學雜費,用今日的詞匯來說,就是“前衛的愛心工程”。
這一層深厚的感情,便不能不使我牢記于心,因之,“文革”浩劫后第一次回鄉,讀到了他的絕筆詩,我哀思泉涌地寫了一首悼詩,再其后,其子女為他遷葬,我還專門撰聯一副,書而付刻。
同樣的挽悼聯書,我還為另一位校長范建德獻上。
在第二故鄉的山野間,我留下唯一的字跡就是這兩聯二十八個字。當他們兩家的后人向我恭表謝意時,我的答復都是同一句話:“全靠先人揮鋤,開了源頭,我才在這世上留下了六百萬字作品。”
“十三王娘”的考據
在這六百萬字文學作品中,除了孔校長等先師灌輸的文思之外,還有故鄉水土和特有的元素——生活素材。
從三妹村回到縣城,在文史界的同仁間談及了“十三王娘墓”,我的思潮馬上又鼎沸起來。
當年,作為一個年方八歲的“鬧兒”,想象中的十三娘便只不過是一個青春美姐而已,而四十年后,在賞析了大量的影劇花旦,品味了曲折的劇情——具體來說就是以太平天國史料的考證之后,那幅稚嫩的素描圖就變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物。
眾所周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太平天國敗亡三十年后,否極泰來,辛亥革命就進入了醞釀階段。太平天國成了天堂的仿版,連孫中山也以“翻生洪秀全”自命。
作為失業教師的我父親,定居縣城后無事可為,便隨同一班文友“進山行獵”——去采集太平天國的史料。蒙山縣原名永安州,可算是洪秀全金田起義后占領的第一座州城,封王建制的“開國之都”。
“三歲定六十”,在這里發生的故事,對于日后太平天國的形象,肯定有決定意義的。
在近百年的頌揚中,洪秀全有很多類似神話的傳說。
例如軍紀,清代的筆記小說寫到,太平天國軍紀嚴明,從金田起義到天京定都,一直男女別營,即使原來是夫妻、母子、父女,都不能授受相親。還有一則筆記說,太平軍打下長沙之后,一員王爵的父母久別重逢,同居了一夜,手下的官兵便援引洪秀全的紀律,說是違犯“第七天條”(奸淫)捆上交給其子,而其子明知是嫡親父母,也只能依法判斬,同時私下派人向天王求情,洪秀全出面特赦,封為“國伯”才消了這場災禍。
在戰爭的氛圍中講究紀律,這是沒說的。
但是,具體到那位“十三娘”,就七牽八扯,出了一串疑案;她真實的姓名、籍貫身份,雖然無據可考,但既然是“十三王娘”,就說明洪秀全建制時起碼有十三個妻妾(另有史料說是三十八人)了,而該女人的死因,據查是小產。只是金田起義發生于1851年1月,當年9月攻占永安州,次年4月在三妹村突圍,七個月間從懷孕到小產,洪秀全本人在建制時是一個什么樣的紀律狀態,就不言而喻。他降旨說“有妖同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銀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這個“絕對平均主義”到底是真還是假?
這一系列的疑問就涌上了我的心頭。
于是,那年開太平天國建制歷史研討會時,我們去視察東炮臺,我向“太學”權威鐘文典(廣西師范大學教授,蒙山人,當年我父親的文友)問道:“太平天國敗亡后,昭王黃文英被俘后招供,洪秀全在天國體制中共封王二千七百多人,其中有幾個蒙山人?”
我這個慣寫小說的“雜家”出了偏題怪題,使這位正宗“權威學者”驚詫了,他眨了眨眼睛跟周邊友人一笑:“你看你看,我怎么從來也沒弄過這個課題呢!”
直到兩年后,我們作為廣西儒學會常務理事在桂林年會上聚首時,他才告訴我,已經發現了一個蒙山籍的王爺,只是級別不高,連個漢字的封號都沒有,蓋屬于四等的列王,是跟隨李開芳、林鳳祥北伐犧牲而追認的。
“零的突破”實現了,但我的思路仍然未釋:太平軍從金田到永安,路過大黎,駐兵三日,吸引了陳玉成和李秀成入伍,最后鍛煉成了后期的將帥,兩個家族中封王的共一打以上,而打下永安后,盤踞七個月,為什么只出了一個王。
邏輯的推理是,這七個月中暴露了矛盾。洪秀全提出了個絕對平均主義的藍圖,但實現的卻是等級比清朝還要森嚴的組織路線。常言道:“相見易得好,久坐難為人”,講究務實的蒙山人看出了他們的素質,罵了一句“老米根”(相當于白話的“勾撮屎”),所以永安突圍時,跟著走的也許不多,難怪后來我父親調查老聽到此語。
就這個邏輯推理出一個新的主題,我圍繞著洪秀全敗亡的過程,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題為《地獄門口的上帝》——他自稱是上帝的次子,以救世福民為號角,但卻以裝神弄鬼為務,所以被推到地獄門口去了。哭笑不得。新的主題都是傳統的史料中提煉出來的,我在寫作過程中查閱了二百四十三位“王爺”的歷史,在三十二萬字的篇幅中引用了近三萬字的史料,被文友戲稱為“引號小說”,折騰了近五年,最后在張笑天的連續劇《太平天國》熱播期間,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編者的思路是“唱個對臺戲也好”。
小說的發行情況頗好,連鐘文典這位專家也給我寫信代序,作了“嚴肅治史,深刻為文”的肯定。
除此之外,我還和蒙山籍的老紅軍陳漫遠合作了一部以他的革命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冬雷》,三十一萬字,這一來,除了短篇散作不算,在我的六百萬字洪流中就有了十分之一以上的蒙山題材,故鄉的流水融著永安山野的地氣,形成了我著作的一個特色。

蒙山勝景長壽橋
以方言證籍貫
在蒙山八年,我父親拜了一位同姓“阿叔”,我母親也認了兩位同姓的“大哥”“二哥”,這一來,我就有了一個叔叔兩個舅舅,一群表弟表妹,而我本人在平輩的同學和文友之外,也還帶出了一群文壇的晚輩,其中文畫兼佳的殘疾藝術家湯展中可稱為典型。再加上一口的蒙山方言,熟練流暢到連公安人員也無法挑剔的程度。所以我走在蒙山街上,一些朋友都稱我為“半個蒙山人。”
說起蒙山的話,那可是一種特色方言,它與周邊的桂柳話、梧州白話和客家話都不同,只有“上起新圩,下迄古湄”的約十幾萬居民通用,它的詞條中還有很多特色詞,甚至連屈原老夫子的“婆”“媼”“妣”等“化石詞 ”也常有所見,而我這個文人卻偏有另類的理解。
2001年9月,蒙山縣政府決定舉辦太平天國永安建制一百五十周年研討會,邀我回去出席,我回去了,故里重歸,激動之下,又來了詩意,找來紙筆,寫了一闋《沁園春》——
又轉蒙山,鄉音嚦嚦,儷影跚跚。看文筆(梁羽生公園那座寶塔)沖天,溪流金帶,湄江長壽,舊縣永安,燈火向明,營盤對月,天兵系馬認高蘭……步校園,有幾多童夢,閃爍其間。
個朝唐突東還,悟相見時難別更難。憶改革開場,炮曾濕引;小康道遠,跋涉維艱。憶苦思甜,撫今話昔,壯志未酬兩鬢斑。祈珍重,祝彩云新紀,共闖雄關。
是蒙山人才能看出,開頭一個“轉”字,就是回歸的意思,接下來六個四字句,環顧了八個景點,下片的“個朝”是今天的意思,而“唐突”,活用了方言“DOM DET”即驀然回首之意,又帶出了改革開放的一系列事件。
斗方剛寫成,文友劉海壽讀之大為驚訝:“你那口蒙山話我聽過了,但落筆寫詩也用方言,看來比我隊還厲害,舊時都稱你半個老鄉,現在看來,那半字就刪掉罷!”
我當堂幽默地答了一句:“你可是縣人大副主任,你的表態有法律作用的,我照辦就是。”
從此,我也就正式加入蒙山同鄉會了。也許是為了“落實政策”,連蒙山縣志和蒙山中學校史都列入我的記錄了,特在這里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