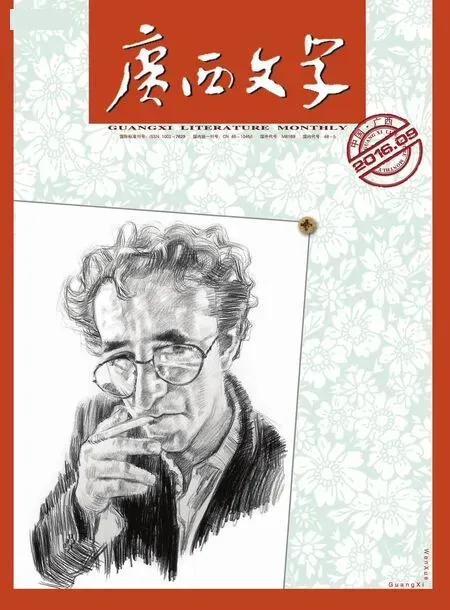小舟從此在
天山雪/著
在南中國廣袤的桂中盆地東南部,東經108°54′40′~109°44′45′、北緯23°54′30′~24°29′00′之間,是柳州市的柳江區,舟村,是這個區里的一個小小村落。
在這片肥美的土地上,亞熱帶溫暖的季風已經吹拂了上億年,吹生了一茬又一茬的樹木,也吹熟了一季又一季的稻米,還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這里,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隨處可見,山水秀美異常。
同樣的山川秀美,同樣的土地肥沃,同樣的降雨充沛,相比柳江區的其他村莊,舟村的動人之處,或者說它勝人一籌的地方,就在于它地處“三江”交匯處。據說,舟村,這個村名就是因此而來的,村民們相信,自己日日廝守的這個小村,就這樣宛如一葉漂浮在江上的小舟踏水而來。
遠處有山,近處有水,還有一條多情的小河流經小村,有柔柔的水草,在水波里蕩漾。有河流必有小橋,就有了小橋流水人家的婉約氣質,因此,舟村,還有了柳江版“小麗江”的雅號。
開心農場和城里的男人
我隨著何雄,一起從柳州市向舟村進發。
這條通往舟村的路徑,我是第一次走,而何雄,他走了一年有余。
一年前,他所在的公司派他駐守舟村,他于是日日往返,奔走在城市與村莊之間。時間,改變了很多東西,最最顯著的一點,他說,自己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情。
對于這條通往自己工作地的路,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這樣描寫:拉堡,往南寧方向,會先后看到兩塊橫在上方的成團路牌——到成團路口(渡村路口),右拐(只有一條路),路過一片一片的草莓窯,再路過兩家葡萄園,開始減速。往左看,有舟村慢生活指示牌——左轉進村,穿過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野,只有一條路,見右邊水車,左邊舟村慢生活指示牌——到村口,選偏左四十五度角路口前進兩百米,到達村中心小廣場,到達——右邊五十米到舟村壯吧即可。
這條看起來拉拉雜雜的線路走得是心曠神怡,大地一馬平川,風景在眼前無限打開,青山、稻田,歷歷在目。何雄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是在冬天。因為,夏天,是無法用草莓窯來作指示定位的,葡萄園也換了模樣,他在冬天描寫的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野,在此時,變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間或還有小片的藕田。
有風吹過,稻香和著陣陣荷香,撲鼻而來。
這不精確的表達與誤差恰恰是舟村,或者是整個鄉村的全部魅力所在,所有的一切都隨著季節的輪轉,更換不同的表情。
在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在推土機滾滾前進的轟鳴聲中,我們的舟村,以及與舟村毗鄰的村莊,還能夠用傳統的方式來描寫它的眉目,還保持著勃勃生氣,還有季節的誤差可以讓人欣喜,還用不著聳人聽聞的形容詞做標題,還用不上凋零、滿目瘡痍這類詞語描寫它的現狀,這一方的農耕天地依舊寧靜、完整,著實令人快慰之至。
何雄描述過的水車,舟村標志性的指示牌,在視線里一一出現之后,舟村,到了。
何雄,將車穩穩地停在舟村的第一接待點——壯吧門口的樹蔭下,這是舟村的對外第一接待中心,是整個舟村的形象工程之一。
此時,金燦燦的太陽才剛剛掛出來,在“舟村·慢生活”的牌匾下,那條流經村莊的河流一如往日那般清澈,濃密的樹下,三位老婆婆,已經在一邊聊天,一邊摘毛豆了。
壯吧——何雄的老板的祖屋所在地。這位從舟村走出去的熊姓漢子,終是不能忘記自己兒時日日嬉戲其間的美麗小村,想要為自己的村莊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他出資五千萬元,將自己公司的命運與村莊聯系起來,引進現代農業技術與管理理念,以現代農業為造血機制,公司出錢、出技術,村莊出地,父老鄉親出人力,營造多贏的格局,盡可能地把自己故鄉的亭臺樓閣、小橋流水、田野村落、人情世故保留下來,想要把外出打工的孩子召回家來,讓他們無須背井離鄉,在自己的家門口就把錢掙到手。

照顧農場的大嬸
何雄,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成了這個小小村莊的編外村民的,他是公司派駐此地的建設項目經理。
這是我第二次造訪舟村,上一次,我已經隨著何雄的腳步,參觀過他們公司著力開發的開心農場。七年前騰訊公司在網絡上開發的開心農場曾經風靡得老老少少都為之瘋狂,多少都市人曾經起早貪黑深夜設定鬧鐘起床偷菜。這片一期工程占地約三十畝的現實版開心農場,比網絡上的虛擬世界,要有趣得多。
這種以種植時令無公害果蔬為主,施農家肥,無污染的休閑+農業的運作模式,讓每一個懷揣田園夢的都市人著著實實圓了一把地主夢,這些大小在四十至九十平方米之間的小菜地,以購買或者租賃的形式向公眾開放。此時,用柵欄分隔成大小不等約一百八十廂的小片田地,在大叔大嬸的精心照料下,瓜果攜手蔬菜,絲瓜伴隨南瓜,各色果蔬,正在可著勁生長。
“看上哪塊就簽哪塊!”那些認購或者承租的農場主們,簽下認養證書后,總是無一例外地給自家的菜地起個可心的名字宣告主權,于是,光是看那些菜地上拉的牌子就已經是一件喜氣洋洋的事了。八星報喜呀、得一閑呀、恩恩和添添呀、富貴菜園子呀,林林總總的菜園子各自都有一個神氣活現的木牌子,趾高氣揚地掛著。
舟村的陽光充沛,雨量適中,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魚米之鄉,菜園里的風景,總是常換常新。一個種植周期約在五十天,常常是這家的貴妃苦瓜剛剛掛果,那家的水果西葫蘆已經成熟,與此同時,另一塊菜園里,紫色的洋秋葵,正在陽光下,驕傲地開著花。

開心農場
何雄掐著手指頭給我算了一筆賬:我們現在是每月七元一平方米,如果你認養五十平方米,每月花費三百五十元,年花費也就四千二百元,這也夠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一年的蔬菜供應量了,自己吃不完,拿去送親朋,送好友,自有一番禮輕情誼重的情意在。在舟村做個開心農夫,代價并不是太高。
“更何況,我們想要的,是倡導一種生活方式。”
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希望忙碌的都市人能在日復一日的忙碌中,能在舟村,暫時回歸我們的祖父祖母輩或者父輩們熟悉的農耕生活,能在土地與作物的陪伴下,將心事卸給自然,放慢腳步,回到記憶中那個純真美好的年代,重新發現身邊的美好,再次體驗已經消失在過往歲月里的單純,過過媽媽曾經給予的好日子,吃吃媽媽曾經做過的老味道。
只勞力而不勞心的時間是快樂的,每到周末,農場主們通常會呼朋喚友驅車前來,為自家的土地鋤土、種菜、施肥、采摘,順帶地,孩子在小河里玩水,大人在一邊垂釣,女人傍著美人蕉玩自拍,文藝青年還會把自己的樂器一并帶來,讓自家的菜聽著自己演奏的音樂健康成長……
當然,如果農場主們實在沒空,公司里的大叔大嬸們就代為履行職責,把菜地照料得好好的,在果蔬成熟的時候送過去。
于是,在舟村,每到周末,幾乎要用“一座難求”來形容,農場主們與普通游客,宛如勤勞的小蜜蜂,在舟村的各個地頭閃現,戲水、燒烤,土窯雞鴨……前陣子,就連中央電視臺的第七套節目,都以舟村門前的小河為拍攝點之一,壯家五色糯米飯,會唱歌的石琴,身著壯家傳統服飾的美麗姑娘,與舟村的好山好水好風情一起,排演了一場濃郁的壯文化風情大戲。
而何雄自己的微信相冊,永遠是在曬舟村。春節前曬熱門年貨:土雞土鴨土臘肉土粽子土年糕;曬舟村的捕魚節:在那些圖片中傳遞全村老幼齊上陣,放低水位備好工具,各顯其能撈一把的盛景,據說,2016年春節的捕魚王,捕到的野生鯉魚足足有十二斤重;春節里他曬拜灶王、品土窯吊燒雞,舞獅舞龍放炮殺豬殺牛做扣肉。無論天氣狀況如何,他總有得曬,小雨就曬細雨蒙蒙;雨前就曬山雨欲來;雨中就曬雨點的節奏;雨后如果有彩虹,更是大曬特曬地曬個不止;壯吧的花,農場出品的那些色彩誘人、造型奇怪又可愛萌萌噠的水果蔬菜,農場的廚房里出品的菜肴,也總是在他的相冊里一再地曬……
對于公司的安排,何雄充滿了感激:“我來舟村之前,做了一段時間的酒水銷售,那日子呀!”他搖搖頭,像是要把那些日子搖落在過去的模樣,“外表看起來好皮好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事,三高,心臟也有點問題。”他一邊說,一邊望一眼舟村,目光又亮起來,“現在,我天天吃這里的菜,喝這里的水,嗬嗬,再去醫院檢查,各項指標全在正常范圍里了,呀,生活得慢一點是對的。”
男人的村莊
整個舟村都姓熊,熊仕木,1964年生人,是我在舟村認識的第一個男人。

認領的樹
這位橄欖色皮膚的舟村本地人,將帶著我和何雄一起環舟村行走,讓我一一領略三條河流各自不同的美。
后來,何雄說,今天走過的部分地方,連他都沒走過。
與我們同行的,還有一條才八個月大的土狗阿黃。這個興沖沖的小動物時前時后地伴隨著我們,有時它一下子鉆進路邊的稻田里,整個身體消失在綠油油的秧苗里,只有稻苗輕微的顫動告訴我們它的大致方位。當我們站在舟村的小河邊為一道道清流驚喜贊嘆的時候,阿黃早就高高興興在一邊又是喝水,又是探爪地玩得不亦樂乎了,和它一比,都市里的狗狗,盡管也有可愛之處,總是覺得有點失之天然與質樸。
“完整的舟村由上舟、中舟與下舟三部分組成。我們落腳的那個舟村,其實是整個舟村的中舟,只是,老人們覺得中舟這個名字不夠好聽,就把中舟叫成新舟了。”熊仕木一邊走,一邊扯起了家常。他有三個孩子,最大的女孩已經在南寧工作,最小的男孩在職業學校里就讀,中間的孩子是大學在校生,妻子在柳州的一家酒店做服務員。他本人在何雄公司里負責一些雜事,壯吧的打掃、清潔與維護,樹木的綠化、修枝剪葉等,都是他的職責范圍。問起為何是妻子外出打工而他作為一個大男人卻選擇了留守村莊,他笑了一笑,沒有回答。
他帶著我和何雄沿著田間小徑一路走去,指點給我們看一些他認為重要的細節,微笑著看我們驚嘆,耐心地等待我們拍完照再次上路,對我們回憶當初舟村是怎樣在無意間發現螺螄可以這么吃的小故事,又是怎樣靈機一動想出把米粉與螺螄湯組合在一起的創意。舟村在20世紀80年代怎樣順應時代需求,成了遠近聞名的面條村的往事,在他的口中一一道來。遇見有可能淤積河道的水草他會順手清理,看到可以食用的果子他抬手就摘下一個讓我嘗嘗。但是,整個村莊,是寂寞的,我們走了整整一圈,用時近一個小時,一路上,除了遇見曬米粉的三位大嬸和在靈福寺忙碌的僧俗,以及一位在水里捕撈的農人,再沒有什么人可以遇見,只有在風中沙沙作響的農作物和兩頭牛,在途中與我們相遇。
八十多歲的熊老伯的住宅,緊鄰著壯吧,同處于村莊風水最佳地段。門前,就是繞舟村的小河,我一大早在舟村落腳的時候,何雄已經告訴我,我要想聽舟村故事的話,找這位熊老伯準沒錯,當時,他正安靜地坐在自家門口,平靜地望著門前的小河。
下午,我再去看他時,他保持著上午的姿勢與表情,坐在小板凳上,倚著門,旁邊,是一張躺椅,還是那樣平靜與安詳。和熊老伯說話無須提高音調,他的庭院的整潔程度讓我懷疑他是不是真的是一個人獨居,但是,周圍人向我證實,確確實實地,是他一個人住。

曬米粉

熊老伯的撈網
在熊金庫來之前,他簡潔地回答了我所有的問題,他確實是一個人住,他有冰箱,他偶爾會讓人幫他在菜市場里買入少許豬肉和青菜,他會在門口的這條小河打魚,一個人,雖然吃不了許多,但是,每頓飯,都會好好地吃的。
說完,他抬抬手,示意我看就掛在他頭頂上的三只撈網,那是他作為一個好漁夫的最佳證明,那三個撈網,一望即知有一雙細致而老到的手在照顧著,妥妥帖帖地,穩穩地掛在墻上。
熊金庫帶著午后耀眼的陽光,踏過小橋向我們走來的時候,我有點驚訝,同是舟村本地人,熊金庫的氣質幾乎是個城市人。他與熊仕木同齡,如果他換上一套相應的高爾夫球衣,他那比熊仕木略淡的橄欖色皮膚會讓人相信,他的好身材,是在高爾夫球場里日日廝磨的結果。他們家的狗狗阿花,帶著一種主人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的忠誠,尾隨其后。
當時,我與熊老伯的對話正告一段落,熊老伯對他的到來,沒有任何的喜悅、驚訝或者其他表情,他還是沉默地坐在門前的石墩上。那塊石墩,因長年累月地接納各色人等的屁股,與人體接觸的部分,已經濕潤如玉。
熊金庫比熊老伯健談得多,話題一下子就打開了,我們談村莊里外出打工的女人。和熊仕木一樣,熊金庫也是留守村莊的男人,妻子在離村莊不遠的拉堡打工,一個月回來一次,他的獨生子,懷揣著我要飛得更高的夢想,在深圳打工。我不敢再問為什么這個村莊都是女人外出而男人留守,只是順著他呵呵地笑著說出的話語:“還是做女人好呀,反正只要有男人,女人怎么著都有飯吃,覺得這一家的飯不好吃,換一家吃就是了。”接著問,“你們兩口子常常打電話嗎?”
“打呀,有事當然要打電話了。”
“怎樣算有事?是一定有什么必須通知對方的事才打電話呢,還是想對方了就打電話?”
“想打就打。”
“是你打過去多還是她打過來多?”
“都差不多。”
我還問起村莊的婚嫁,答案并不比我從新聞里讀到的樂觀,現在的妹子,只要有可能,還是更愿意到城市里生活。簡單地定義說妹子們勢利是不公平的,畢竟,更好一些的物質生活,更好一些的教育資源,更多一些的發展機會與空間,更好一些的醫療資源,都在城市里。
“我們村里,現在還有近三十個光棍。”
我們一起沉默,一起默默地看著幾十米開外,幾個快樂的光腚少年,就著白亮亮的陽光,從岸上跳到河里,又從河里爬到岸上……

舟村小景
話題再次響起時,還是從屋主熊老伯身上展開,熊老伯的孩子們,都在城市里,他有兄弟共五個,兄弟、自己的孩子以及和孩子一起來的孩子的孩子,如果一起回家的話,那場面,熱鬧得很哪,要擺上三桌才坐得下;他身體多硬朗,你看,他家掃得多干凈。話題是怎樣從這些愉快的家庭場景流向熊老伯因吸毒而早逝的兩個兄弟身上的,我已經記不清了,我只記得,談起這些可怕的往事,金庫的音調沒有變,一旁的熊老伯,平靜得像在聽其他人的故事,熊仕木也不吭聲,我再一次不敢追問細節,我能想象得到那樣的事件給一個家庭和一個村莊帶來的災難。這樣的平靜,在熊金庫談到他自己同樣因吸毒而早逝的三個兄弟時,也沒有改變。
“吸毒的全是村里面的能人,真是可惜了。”他一邊說一邊更頻繁地撫摸著自己家的狗狗阿花。
火燒云燃燒在天空的時候,幾個玩水的孩子不知何時已經回家了,村莊還是那么安靜,熊老伯表示,他要張羅晚飯了,我順勢在他的家里仔細地看了一圈。這是一座敞亮的大宅,并不雕梁畫棟,卻莊重典雅,處處透出強健的風骨,想來,當初造房子的時候,是按照祠堂的標準建造的,天井打掃得干干凈凈,水泥地面完好無損,廚房井井有條,廚具的整潔程度證明了清洗這些廚具的那雙手穩定又可靠,眼睛視力正常,靠墻而放的折疊桌椅,展示了在這座房子,聚餐是經常在舉行的事。
與這房子相比,比鄰而居的熊仕木的房子雖是新建的鋼筋水泥混凝土的三層小樓,氣質卻是遜了好大一籌。不得不說,熊老伯的家,干凈整潔得不像一個老鰥夫的住所。熊金庫指著站墻上一個男人的照片告訴我,這是熊老伯的其中一個兄弟,那個眉清目秀的男人,一定是他之前所說的能人一枚。
熊老伯去張羅晚飯了,熊金庫撫著自己的狗狗阿花,淡淡地說:“我不著急,反正家里就我和我的狗。”一邊的熊仕木立即接上話頭,“我是和我的貓。”
兩個男人,說這句話的時候,音調沒有高低起伏,相互的目光沒有對視,我低下了頭。
何雄告訴我,熊金庫也是村莊的能人,他有眼光、有魄力,能叫得動人去干活,開心農場旁邊那塊規劃成燒烤場的用地,一系列的組織協調溝通,就是他卓越的工作能力的證明。

前來調研的地方官
二十七歲的釋明慈
出了熊老伯家,我和何雄一起穿過村前的稻田,再訪上午到過的靈福寺。
越是接近,裊裊的佛樂越趨清晰,西下的霞光中,笑嘻嘻的農夫伴著佛樂在砌墻,五米開外,包括小師傅釋明慈在內的眾人,在挑磚。
那塊落款2013年12月18日的寺志記錄著靈福寺的來龍與去脈。
靈福寺的前身創建于道光五年,即1825年,原名“坡棷廟”(壯語)。老廟在1996年被大水沖塌。2003年,熊姓族人在寺廟原址發起重建,2008年,坡棷廟更名靈福寺。
不可否認,有一座真正的有愛心的寺廟在,對一個人的心理安慰是巨大的。痛苦的理由那么多,痛苦的接口如此廣大,能有一個端口,什么也不說地接納那些在涼薄世道里受傷的心,總是好的。在過去的慢時光里,那些在大地上星羅棋布的大大小小的寺廟,以及村頭供奉的土地公土地婆,像一口口溫泉,溫柔地滋養著四處飄蕩的疲憊的心靈。在很多年前,我還很年輕的時候,我曾經見過一個婦人,站在一棵掛滿紅飄帶的榕樹下,依著樹干,喃喃地訴說心事。今天的靈福寺門前,也有一棵同樣掛滿紅絲帶的大榕樹,一個約莫五歲的小女孩,就在這棵掛滿紅絲帶的樹下,心無芥蒂地和我說東道西。

環村小渠
今天的靈福寺只是規模初具,一塊又一塊的功德碑記錄了人們對這座寺廟殷殷的深情。村民們都不富裕,捐款都不是大手筆,靈福寺的供品,卻是我見過的最新鮮的,紅彤彤的富士蘋果,新鮮的哈密瓜,剛剛上市的荔枝、西瓜、水蜜桃、花生,都和寺廟前剛剛盛開的睡蓮一樣清新潔凈。佛臺上供奉的王母娘娘與玉皇大帝、關公、包公、財神、土地公與土地婆,還有送子觀音,滿滿的,都是雙雙對對的居家歡樂與接地氣的祈求。當我在電腦上敲下這些文字時,心里響起的,居然是“小松樹,快長大”的旋律。
廟里有和尚,看到這位眉清目秀的年輕小和尚釋明慈時,一個心里留存已久的問題禁不住脫口而出:“師傅,你使用蚊香嗎?”
他完全地不假思索:“我不用的。”
“那蚊子咬你呢?”
“我用風扇把它吹走。”頓了一頓,他接著補充道:“有一些道行高的師兄,蚊子不咬的。世間的萬物,都會相互感應,你沒有傷害蚊子的心,蚊子就不會來咬你。”
我笑了一笑,好吧,我被蚊子咬,是因為我道行不夠。嘴邊的另一個問題,終于還是咽了下去。
他微微地笑著,年輕的臉龐白凈平和,牙齒閃閃發光,他的帥,不亞于現在大熱的韓劇明星宋仲基。他對我的好奇的目光,為何選擇了出家的提問,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這是緣分”。
此刻,釋明慈還要去挑磚,有人在廚房張羅晚餐,我不想去幫忙,就順從地聽從建議,脫下鞋子,光著腳坐在河邊,自己發呆。開飯之前,有人給我送來了本年度的第一碗綠豆粥,還有一杯靈芝水,招呼我品嘗他們的糕餅。這些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在這個傍晚,給了我滿滿的美意與愛心。
城市華燈初上之時,也是舟村晚霞漸斂、倦鳥思歸的時刻,砌墻的人和挑磚的人,都收工了,我已經從那塊寺志里知道,靈福寺的廟會分素餐與葷食兩種,這頓素齋,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齋,舟村,在這一天里,包辦了好幾個第一次。雖然是團團而坐,顯然地,釋明慈小師傅是眾人的馬首,大家都有意識地把比較多的空位留給他,他有點不好意思,可是架不住眾人的意愿。
在蚊香終于抵達餐桌之前,我已經盡量低調地手舞足蹈了好一會兒了,眾生平等,人要開餐,蚊子也要生活與繁衍。不能不承認,釋明慈小師傅的一句話,讓這個事情呈現出別樣的美感與慈悲:“你也不輕易到我們這里一次,這里的眾生見你一次容易嗎?你施舍一點給他們,也是功德一件。”
好吧,好吧,施與是美德,這是無可爭辯的。
可是,我還是有點后悔自己沒有攜帶花露水。
用齋時坐在我邊上的男人是那位和我攀談了老半天的小女孩的爸爸,他的妻子,也就是小女孩的媽媽,笑著說自己讀了一天的佛經。這個因著種種因緣才組合而成的家庭,堅定地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只要出于誠心正意,初心自然會將他們帶到平安喜樂的世界里,一切,自有老天打賞。
離去之時,坐在我對面的姐姐,追了上來,分賜我和何雄一袋果餅,臨別前的那句“阿彌陀佛”,真誠無比。
釋明慈師傅送了我們一小程,在路上,他一直在和何雄商量著怎樣開一條路,把到舟村休閑的人流,引到寺廟來。他說,一個景區,加入了寺廟文化,是不一樣的。
此時,明月初升,白白的月亮,和詩歌里曾經照過李白杜甫的那一輪,同樣地皎潔。
我們的村莊
就在我在舟村采訪的這一天里,舟村還接待了前來調研的柳江區主管農業的區長,這樣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舟村,和鄰近的村屯相比,并不是頂兒尖的那一個,盡管自然條件很好,人也夠聰明,但缺乏足夠的青壯年建設家鄉,還是舟村的硬傷。舟村熊金庫評價自己的村人“還是有點懶的”,這些“有點懶”的青壯年多數去城市里謀出路了,舟村目前只有約三百人居住,大部分是老人。
村莊雖不衰敗,與城市相比,舊貌換了新顏越來越美麗的村莊,就像那個梳著大辮子的小芳,雖不缺乏動人的美麗,還是留不住青壯年們向往城市的心。怎樣讓那些在他鄉的明月里漂泊的游子,停下外出的腳步,留下來踏踏實實地為自己的村莊做些什么,依然是地方官們寤寐思之的問題。
在柳江區的版圖里,鄰近的村屯已經有了很好的表率,那些走在前列的村屯,人均年收入超萬元,在那些村屯里,已經有遠見卓識者,放棄在外打工的傳統路徑回流故鄉,把自己的未來與村莊的未來捆綁在一起。依托工業重鎮——柳州五十公里半徑的有利條件,借助柳州市現有的海陸空三維立體交通體系與現代農業的強強聯合,將柳江區打造成環都市鄉村旅游休閑基地,已經初具規模。
今天,一個綿延了幾千年溫柔敦厚的農業文明古國,在向更加強而有力的工業文明邁進的大轉變中,追求怡然自樂的理想國的夢想,并沒有隨著互聯網的強力介入而有減少,相反,對社會,對人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有城市的職責與功能,鄉村有鄉村的生存之道,城里的瑪麗精致華美,是美的一面,鄉下的小芳質樸天然,是美的另一面,兩者并不相悖。
無論時代如何更迭,故土永遠是一個游子永恒的安慰與最后的歸途,那個最最著名的回家人陶淵明,就是在自己的故土,描繪出自己理想國的模樣,“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

金庫與阿花
這個理想國的模樣,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直至今天,依然是我們的夢想家園。
對于一個現實的鄉村守望者,例如,熊老伯,例如,熊仕木,例如,熊金庫,例如,來舟村調研的地方官們,總還是希望能創造出一些柔軟而難忘的東西,好讓遠方的良人,對著自己的故土,深情地向往。與余秋雨先生在《行者無疆》里談到的冰島總統的情懷如出一轍:“我們冰島雖然地處世界邊緣,但每一個國民都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生活。作為總統,我需要考慮的是創造出什么力量,能使遠行的國民思念這小小的故土。”
歷史不能停滯,時光不會倒流,今日的鄉村,依然如同我們初戀的那個小芳,在我們內心深處最最柔軟的角落里生長。
守護鄉村,就是守護我們的故土,守護我們最最美好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