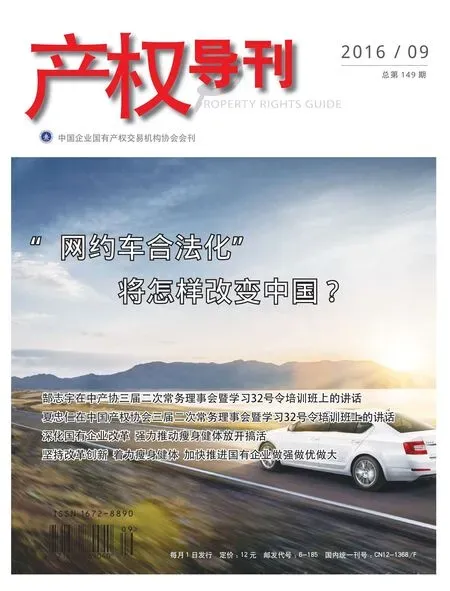我還是要談一談需求側改革
◎ 王賢輝
我還是要談一談需求側改革
◎ 王賢輝

自從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以來,報刊上就少見討論需求問題了,但是,我還是要談一談需求側改革的問題,因為需求側改革的問題不解決,供給側改革也難達到目的或取得預期實效。
現在,人們一提到拉動需求,就想到2008年的四萬億投資,一提到四萬億投資,就聯上當下的去產能去庫存,就談虎色變。問題在哪里?問題不在投資四萬億拉動需求,而在于一些決策者對需求的片面認識和誤判。
需求有外需和內需兩種,外需就是出囗,因為全球受經濟危機影響,經濟不景氣,出口不旺,所以靠外需拉動中國經濟效力有限,這是眾所周知的。問題就出在內需上,內需就是國內消費,又分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兩種,但生產消費最終必須落地到生活消費,才成為社會的最終消費,只有居民的最終生活消費,才能有效拉動經濟,而只有成為居民最終生活消費的供給才成為有效供給,才是中央的供給側改革所指。凡是不能形成居民最終生活消費的供給都是無效供給,無效供給就是對需求特別是內需的片面認識和誤判的產物。所以用投資拉動經濟沒有錯,錯就錯在亂投資,亂投到只能拉動生產消費即GDP,但不能形成居民最終生活消費上去。比如,許多城市庫存的大量商品房賣不出去,許多鋼鐵水泥煤炭等生產消費的原材料不能變為居民生活的最終消費品,所以,抓供給側改革必須同時抓需求側即居民生活消費需求改革,只有用滿足居民生活消費需求來拉動中國經濟才有可持續性。這里要特別指出,本文所說的內需,是專指居民生活消費需求。
那么,怎樣才能滿足居民生活消費需求呢?毫無疑義,通過供給側改革,不斷向各階層居民提供需要的高質量消費品,但是,光有這一條還不行,還要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的購買力,因為即使你能提供最好的高質量消費品,居民如果沒錢買也還是白搭。如房地產一邊在去庫存,一邊又有許多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缺乏住房,原因不是房造多了,而是因為他們有消費需求但無消費能力,即缺乏購買力。要提高購買力,當然就要增加就業和提高收入,但光增加就業和提高收入還不夠,還必須社會財富分配公平,否則,社會財富再多,如果被少數人占有,社會還是缺乏購買力,因為在同時期內,如果多數人增加一百元收入,而少數人卻增加一千元甚至一萬元收入,則多數人還是消費不起,因為物價會被少數有錢人拉抬上去,當少數有錢人消費滿足后,多數中低收入者卻因消費不起,而使全社會內需萎縮經濟下行。例如,以一個企業來說,如果大多數員工年薪都是二三萬元,而少數高管年薪卻二三十萬甚至上百萬數百萬元,你說光提高員工年薪幾千元,能拉動社會消費嗎?然而,我國企業員工與高管貧富差距懸殊的現狀就是這樣,還有行業之間的收入貧富差距更嚴重;又如農民工進城買房問題,就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收入來說,要在其打工的所在城市買房是不可能的,即使你讓其落戶也買不起,農民工不像城市居民,退一步說,即使像城里人一樣貸款買房,也不一定會買,因為職業不穩定,如果貸款買了房,明天老板辭退你了或者要換個城市打工怎么辦?再說如果在大城市打工,在家鄉的小城鎮買房,行不行呢?那他買的房給誰住?自已還長期在外打工租房,又如果讓農民工回到家鄉的城鎮去就業也不行,因為中小城鎮吸納不了,大城市又需要大量的農民工。因為中國的優質社會資源大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城市,所以,中國的城鎮化和保障房工作進展緩慢收效甚微。
綜上所述,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在抓好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解決內需問題,重點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生活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因此,在繼續擴大就業的同時,必須全面系統精準的進行社會財富收入分配改革,縮小貧富差距,總體提高社會居民生活消費能力。
縮小貧富差距,推行社會財富收入分配改革難度極大,甚至比反腐敗的難度還大,因為,這不僅涉及到某些利益集團,甚至還涉及到某些掌權者的切身利益,但必須知難而上,否則,就不能破解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難題。辦法總比困難多,關鍵是決策者對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進行社會財富公平合理分配,提高社會居民總體消費能力的重大深遠意義的認識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