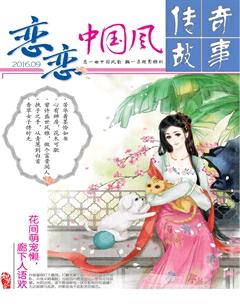執(zhí)子之手,從青蔥到白首
顧素玄
世間若注定要有一場緣分等你來相赴,那便是隔山隔海也阻擋不住。
身為家中嬌女的林佩環(huán)本是順天京城人,因父親林西厓素在蜀中一帶為官,她從北到南,漸漸把他鄉(xiāng)作故鄉(xiāng),成長為一個四川女子。
容顏清麗,才情無雙,有良好的身世,又擔了個才女的名頭,正值妙齡的林佩環(huán)從不擔心不能找一個良人來配,怕只怕眼界太高,心思太廣,不能妥帖地安放柴米油鹽,恬度煙火人間。可事實證明,不僅她不一樣,她的父親也眼光獨到。
林西厓?yōu)榕畠嚎粗辛艘蝗恕_@人生于官宦世家,有清代“蜀中詩人之冠”的美譽,才華和人品都廣受肯定—唯獨一點,他曾娶妻生子,雖均已病逝,但佩環(huán)嫁過去還是逃不脫“繼室”之名。
得知消息的林佩環(huán)沒有與父親吵鬧,亦不覺得委屈。她默默將張問陶這個名字翻來覆去念了好幾遍,又想起那些平日看過的他的詩文,不由對這未來的夫君充滿了憧憬。
而張問陶此時除了期待,更多的是忐忑。他自鄉(xiāng)試落第后便遭遇了巨大變故,妻兒雙雙逝去,留下他一介鰥夫,空嘆功名受挫,命運乖戾。如今卻有這樣一門好親事擺在他眼前,雖說是招贅,但林家為人并不囂張,反而彬彬有禮。對張問陶而言,此番招贅更像是一種知遇之恩,拯救他掙扎出人生泥潭。他為此寫下詩句,“慚愧祁公能愛我,夜窗來聽讀書聲”,想要好好報答。
身為一個父親,林西厓不期許他能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回報,只要女兒生活幸福,他就對自己的選擇安心了。但張問陶也很清楚,鳳冠霞帔滿堂喧鬧之后的漫長光陰,他要想待林佩環(huán)好,光靠這份感激是不夠的。
淺情深愛,都要在時光流淌里逐步抽絲剝繭,還原出最真實的形態(tài)來。
他和她都是聰慧之人,在塵世姻緣里找準了自己的位置。她沒有端著大家閨秀的架子,絲毫不嫌棄丈夫的貧困窘迫。她對他只有賢妻良母的寬容體諒,以及紅顏知己的溫柔解語。張問陶感受到她所有的付出,常常贊美她。
他知道他的妻有多好,不吝寫詩來夸她,從“學書且喜從吾好,覓句猶堪與婦謀”到“袖中已遂襄陽癖,林下尤逢謝女才”,一種贊賞,萬般語言,不厭其煩地寫。也不是虛假,她的確能與他詩歌酬唱,琴瑟和鳴。所以這贊賞里藏了才氣,染了愛意,格外真誠。
他20歲初婚,不到兩年便成孤家寡人,未來的路一度不知該如何走下去,而林佩環(huán)的出現(xiàn)讓他的生活像暖日照在大海上,日升日落都伴著潮洄的響,再也不會孤單。
婚后張問陶重振旗鼓,進京趕考,此次順利中第,后又留京一段時日。這大概是與佩環(huán)成親以來分別最久的日子,相思情重,無處排遣,只能以詩詞代替,輾轉(zhuǎn)寄情。
“春衣互覆宵寒重,繡被聯(lián)吟曉夢清。一事感卿真慧解,知余心淡不沽名。”
寄出這首《春日憶內(nèi)》,他才驚覺他真是牽念她。因為牽念,恨不得把一顆心剖給她看,好讓她知道他無心爭名奪利,只等事情一了,就回到她身邊。
所謂細水長流,無非就是些瑣碎至極的事,但每件事都倒映著心里那個人的影子。得了空閑,張問陶便馬不停蹄地從京城回轉(zhuǎn)蜀中,等到次年需要再次入京時,他決定帶著妻子同往,不愿受那離別苦。
私下聊天時,張問陶常常在妻子面前說他倆是注定的姻緣,他把它稱之為“硯緣”,還特意作詩留存。她笑他總提舊事,但心里也對這其中的緣分驚慨不已。原來,林西厓于成都任職時,曾有人持古硯求售,匣中有銘文記載是君賜之物,林西厓便珍藏起來。二十余年后,張問陶已是林家婿,瞧見這方硯,發(fā)現(xiàn)竟是其先祖赴宴時得到的綠端硯,后來被落魄的族人賣了出去。沒想到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在他還未識得佩環(huán)時,家中的端硯早已替他牽好了這根紅線,先他一步來到她的身邊。是天意,也是傳奇,更是平淡中的有味,如同伴隨他們每一天的衣食住行。
光陰潺湲,每一段都有其獨特的韻意,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方能覺深。她日復一日地為他張羅吃穿,他時不時學習張敞,為她輕掃蛾眉。她為他生兒育女,他將一切感懷在心。他與她的生活既有油鹽醬醋的真,又有琴棋書畫的雅,聊家長里短,亦對畫談心。
有一年隆冬,屋外大雪盈尺,張問陶看著爐煙裊裊中的佩環(huán),在宣紙上為她畫了一幅肖像。林佩環(huán)欣喜于他的心思,也仰慕他的才華,拿起筆在一旁題下一首詩:“愛君筆底有煙霞,自拔金釵付酒家。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
清瘦簡約如梅花一般的詩句,卻是再重不過的諾言,她這一生的修行為的就是這個“人間才子婦”的名頭,她心甘情愿。
識妻真心的張問陶感動不已,依韻和詩一首:“妻梅許我癖煙霞,仿佛孤山處士家。畫意詩情兩清絕,夜窗同夢筆生花。”
多么有幸,才能將梅妻鶴子的清絕化作身邊人的踏實,密密麻麻的針腳里有她,龍飛鳳舞的筆跡里也有她。相依相伴,互解互懂。
他們之間的交流從來都是這般平等,簡單的語言往往融了一片柔情。正因如此,他遇上她后的時光幾乎沒有太多坎坷,在浮生小樂里毫不費力地過成了旁人眼中的知音伉儷。
這人間歲月是獨屬于他們的,經(jīng)年累月積了灰反而更好看,有種塵埃落定的況味。賞著賞著,青蔥白頭,就走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