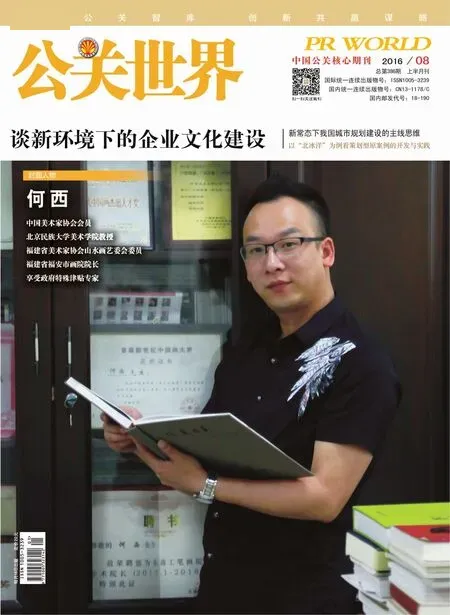學黨史、悟公關:中國共產黨應對長征危局始末
文/劉占全
學黨史、悟公關:中國共產黨應對長征危局始末
文/劉占全
自1921年建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依靠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中,經歷的危難、克服的挫折很多。從全局來看,最能表明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并鮮活表現中國共產黨卓越公關藝術的,是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成功應對長征危局的革命實踐。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史是最好的營養劑。
中國共產黨由稚嫩到成熟,由弱小到強大,由體制外的政黨發展成為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執政的世界第一大黨,不斷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科學處理與國民黨等其他政黨的關系,采取務實靈活的統一戰線政策,成功克服了多次危難和挫折,積累了諸多公關經驗。黨的歷史為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關理論提供了鮮活的史料資源,值得業界人士深入挖掘、認真總結、大力宣傳。
一、長征中黨和紅軍的艱險處境與重大損失
由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錯誤,直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份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方根據地紅軍主力被迫先后進行戰略大轉移,這就是黨史上有名的長征。一支武裝力量脫離原來的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處于流動狀態,也就進入了一個危險的局面。要理解這一點甚至說要理解黨領導下的全部中國革命,必須首先要搞明白什么叫根據地。
根據地,簡單講,“根”,就是根基,“據”,就是憑依、倚仗、依靠,“根據地”就是有群眾基礎的、可以依靠的地區。毛澤東曾給農民出身的戰士這樣講“根據地”:人不能老走著、老站著,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得靠屁股,“根據地”就是屁股。紅軍離開根據地,離開支持自己的群眾,兵源補充和槍支彈藥、糧草被服等物資供應就會面臨極大困難,所以說,戰略轉移中的紅軍是極端危險的。
離開根據地這個依靠,加之長征前期中共中央領導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中后期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和國民黨幾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革命遭受嚴重曲折。長征結束之后,紅軍和根據地損失了90%,黨在國統區的力量幾乎損失殆盡,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中國革命瀕臨絕境。
二、黨的成熟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制定
盡管長征使黨和紅軍損失很大,但挫折和失敗也教育、鍛煉了革命隊伍。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形成了集體領導體制。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聯系中斷(1934年10月—1936年6月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沒有電訊聯絡)獨立自主解決本黨重大問題的開始,是黨史上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這次思想解放開了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先河,這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
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雖然不多,但這是黨的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骨干。毛澤東在1960年5月7日一篇報告中評價道:“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長征前曾經達到過三十萬人,因為犯錯誤,后來剩下不到三萬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難的時候不要動搖。三萬人比三十萬人哪個更強大?因為得到了教訓,不到三萬人的隊伍,要比三十萬人更強大。”
領導正確,隊伍堅強,這就為長征的最后勝利和科學政治路線的制定奠定了組織人事基礎。
長征期間,日本侵略者向中國的進攻沒有停步,國民黨統治集團傾全力“剿共”,對日本侵略者節節退讓。1935年的華北事變,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以一二·九運動為標志,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新高潮已經到來。
1935年7、8月間,共產國際七大提出了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剛剛到達陜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提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并且指出,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必須堅決加以糾正。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著重指出了共產黨和紅軍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但要充當發起人,而且應當成為堅強的臺柱子,“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瓦窯堡會議制定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使黨在應對新的歷史挑戰時日益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三、長征勝利后喜憂參半的陜北形勢
新政治策略雖然已經制定出來,但策略的實施需要時間,實施效果的顯現有一個過程。盡管長征取得了勝利,但長征危局仍沒有結束。
紅軍三大主力來到陜甘寧根據地勝利會師,中共中央和紅軍有了落腳點,中國革命又有了一個大本營,好像中國共產黨已經轉危為安了。其實不然。長征危局并沒有隨著戰略轉移的成功而完全被破解。事實上,紅軍主力到達陜北后繼續面臨著嚴峻局面,從某些角度來說,甚至比長征中所面臨的嚴峻局面更加危險。
1935年10月,作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以后面臨兩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一是自身兵源、槍支彈藥和糧草被服補給仍很困難。因為陜北土地面積雖大,但這里人口密度低,土地貧瘠,物產匱乏,遑論武器彈藥補充。二是外在軍事壓力仍然很大。紅一方面軍主力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時是8.6萬人,到達陜北時只剩下8000人,加上陜北的紅十五軍團7000余人(紅十五軍團是由劉志丹等人領導的紅26軍、紅27軍和1935年9月先期到達陜北的紅25軍三個軍會師后合編而成)。紅一方面軍8000人加上紅十五軍團7000余人,共1.5萬余人。可是,他們面臨著駐扎在陜西的兩個強大對手: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十七路軍和以張學良為首的的東北軍。張、楊兩支部隊當時在陜西一共有11萬兵力。
1.5萬人的紅軍面對要剿滅他們的11萬國民黨軍。所以,紅一方面軍當時面臨的軍事壓力還是蠻大的。為了積蓄抗日力量,發展壯大自己,補充兵源、籌集物資糧草、擴大根據地,1936年2月至7月,紅軍先后進行了東征和西征戰役。這些嘗試盡管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遇到了很大阻力,敵我在大西北的軍事力量對比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可喜的是,中國共產黨制定的符合歷史潮流的統戰策略已經開始發揮作用。
紅軍在與東北軍、西北軍交戰的過程中,發現了張學良、楊虎城不想打內戰的政治傾向,因此,中國共產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的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一戰線工作。張、楊先后與中共達成合作協議,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在1936年上半年實際上已經停止敵對行動。
張學良、楊虎城都是愛國將領。楊虎城是較早公開強烈要求抗日救國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之一。張學良與日本人有很深的家仇、國恨情節,他的父親張作霖曾是“東北王”,由于不和日本人合作、拒絕簽訂賣國條約,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成重傷逝世。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由于戰略判斷失誤,加上“情報也不夠”,把整個東三省丟掉了,所以,他很想打到抗日前線去,打回東北去。
1936年4月9日晚間,周恩來和張學良在延安一座天主教堂中秘密會見,這就是黨史上著名的“膚施(延安曾稱膚施)會談”,會談的結果是雙方一致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不過,在如何對待蔣介石這一問題上有齟齬和分歧:張學良主張逼蔣抗日;中國共產黨主張抗日反蔣。
張學良對蔣介石“剿共”而不抗日的政策不滿意,但是他不主張反蔣。張學良認為:蔣介石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實力派,抗日離不開他,若努力爭取,他可能會有所轉變。中國共產黨主張抗日反蔣,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當時把蔣介石集團和日本一樣看做是自己的敵人。中共這樣一個方針從情理上來說完全可以理解,因為自1927年開始近十年的時間內,蔣介石一直意欲把中共和中共的武裝力量當做最大的敵人消滅掉,即便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后,蔣介石仍然秉持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放過中共,特別是這時尚未完成長征的紅四方面軍、紅二、紅六軍團等紅軍仍處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之中。
周恩來把張學良的意見帶回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就在第二個月,1936年的5月初,中共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轉變,公開放棄了反蔣口號。1936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也電告中共中央,不同意把反蔣與抗日的口號并提。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指出:“我們認為,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論是不對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要真正武裝抗日,還必須有蔣介石或他的絕大部分軍隊參加。”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國內階級關系變化的實際情況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化。中國共產黨準備和東北軍、西北軍在祖國大西北造成一個聯合抗日的局面,來逼迫蔣介石轉變政治態度和立場,問題是蔣介石轉變是有難度的。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陜北將要會師的時候,蔣介石由南京飛到西安督戰,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然后,10月至11月間,蔣介石到洛陽做“剿共”軍事部署,將其嫡系部隊約30個師調到以鄭州為中心的平漢、隴海鐵路沿線布陣待命,以便隨時開赴陜甘地區剿共。他揚言至多一個月即可消滅陜甘紅軍,“蕩平”共產黨的根據地。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共有約6萬人,而這個時候,已經在陜西和周邊的國民黨軍有約46萬人,紅軍和國民黨軍的力量對比懸殊更加明顯。

為了應對這一危險局面,在政治和軍事上打開新局面,中革軍委制定了一個“寧夏戰役”計劃,核心目標是,紅軍西渡黃河,占領寧夏,出綏遠,靠近蒙古,然后從蘇聯紅軍那里取得武器彈藥、糧草被服的援助。“寧夏戰役”計劃是從1936年10月24號晚上開始實施的,但由于船只缺乏,當時紅軍渡河速度緩慢。直到11月1日這一天情況發生了變化,黃河沿岸的所有渡口被趕到的胡宗南的10萬兵力全部占領,西渡黃河的通道被切斷。已經過河的是紅四方面軍一部共2.18萬人,其他紅軍無法繼續渡河,紅軍成為被懸隔于黃河兩岸的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沒來得及渡河的4萬黃河以東的紅軍,另外一部分就是已經渡過黃河的2.18萬紅軍。
11月11日,渡河部隊根據中央決定稱西路軍。西路軍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占領甘肅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向西北行軍,意欲到新疆獲取蘇聯援助物資。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與馬家軍英勇奮戰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但終因寡不敵眾,于1937年3月慘烈失敗,幾乎全軍覆沒。
黃河以東的幾萬紅軍在國民黨“中央軍”大舉壓境的情況下面臨的局面依然非常危險。
四、西安事變成為時局轉換的必然
在陜北紅軍處境極其困難的時候,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變——西安事變:不想打內戰的張學良、楊虎城“兵諫”蔣介石,逼其答應抗日。
蔣介石因為對張學良、楊虎城剿共不力不滿,1936年12月4日再次從洛陽飛至西安。他這一次對張、楊更加嚴厲地訓斥,迫令張、楊的軍隊全部開赴陜北“剿共”前線,而且威脅說,如果再“剿共”不力的話,他就要把東北軍調往福建,把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由“中央軍”在陜甘“剿共”。這實際已危及到張、楊部隊的生存,可以說,就“剿共”一事,蔣介石對張、楊下了最后通牒。
張、楊一邊面臨蔣介石要求打內戰“剿共”的壓力,而另一邊還同時面臨著民眾要求抗日的輿論壓力。此時,西安民眾的抗日救亡行動非常高漲,蔣介石到達西安以后,西安爆發了大規模的抗日救亡游行。特別是1936年12月9日,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西安城內1萬多名學生舉行請愿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楊二人在多次勸說、甚至“哭諫”蔣介石無效的情況下,他們選擇了順應民意,以強制措施逼蔣抗日。
西安事變的發生主要有四個方面的背景原因:一是張、楊二人為首的東北軍、西北軍抗日救國、停止內戰的夙愿已久;二是“華北事變”之后,中日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全民族抗戰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三是中共方面提出了務實靈活的統戰策略,對張、楊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影響;四是蔣介石把張、楊二人逼到了絕路,張、楊對蔣采取強制措施是順應民意的無奈之舉。
西安事變發生以后,張學良第一時間電告中共中央,中共派出周恩來等代表到西安協商解決辦法。中共中央在弄清情況后,對當時國內外輿論和各政治軍事力量對比情況進行了綜合分析,經再三研究,最終決定,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爭取南京政府正統,特別是爭取南京政府中的親美派、親英派、反對親日派,在蔣介石承諾張學良八項抗日主張的前提下,釋放蔣介石。在中共的協助和推動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之后,內戰基本停止,從內戰轉向抗戰、國共走向第二次合作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這在客觀事實上也為中國工農紅軍解除軍事壓力提供了最為重要的前提。
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才是中國革命走出危機的開始。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是中國共產黨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正如斯諾所說,它“在歷史的大峽谷上實現了一次歷史的大跳躍”,演出了一場“驚險的好戲”。
西安事變是在日本大舉侵華背景下,長期積蓄的民族情緒的大爆發,是一次救亡圖存民意的總表達。盡管從表面看,以張、楊二人作為民意代表、作為歷史事件的主角,以這樣一種方式爆發出來,似乎是一次偶然事件,而其實西安事變的發生是一種歷史必然。
如果非要說西安事變是一個偶然,那它也是必然中的偶然。“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歷史是各種力量較量的結果,但歸根結蒂,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民心所向即是歷史發展方向。民意此時不表達,彼時亦會表達,不以此種方式表達,亦會以彼種方式表達,歷史問題不以這種方式解決,亦會以另一種方式解決。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鐵一般擔當起民族救亡的歷史重擔,始終以人民利益為重,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始終依靠人民堅持全面抗戰路線,逐步成為團結抗戰的政治領導核心。而蔣介石集團害怕群眾,更害怕組織起來的群眾,走的是只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最終走向孤立。到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發展到121萬,人民軍隊120萬,民兵260萬,黨領導下的根據地人口1億人,為最終戰勝蔣介石集團、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劉占全,中共臨沂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