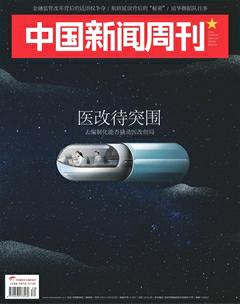因陋就簡,也讓恐懼成宴
楊時旸
眾多周知,“國恐”已經成為了一個固定的、帶有嘲諷性的短語。觀眾,甚至很多從業者自身都對它低看一等。中國特殊的限制機制,也讓這種類型片的騰挪空間異常微小。它逐漸淪為了一個無法翻身的笑話,陷入粗制濫造和被人訕笑的死循環。人們都以最低的期待值,幸災樂禍地想看著每一部所謂的恐怖片如何收場。
恐怖片在中國一片死灰,但《中邪》的出現卻讓它意外復燃。一位橫漂導演,花費幾萬元,用偽紀錄片的方式為這個類型挽回了尊嚴。相比于其他類型,恐怖片直接切近感官,所以,更多的這類電影都止步于肉身的反應,而不問向精神,它極其容易變得“自甘墮落”。最近,西方乃至日本的恐怖片都顯得凋敝,除了那部《女巫》,很難有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經歷了無數次重復的恐怖意象的重組之后,如果沒有更深層的心理鼓動和更劍走偏鋒的想法,很難再度支撐起人們的興趣。
《中邪》是在一種標準的紀錄片氛圍中開場的,那株隨風搖曳的大樹,暴土揚塵的街道,能說會道的東北算命噴子,躲在路邊的解卦大嫂……你會以為這又是一部以講述臟亂差為榮的中國式紀錄片,但當貧嘴滑舌的男主角和聒噪的姑娘出現的時候,一些影影焯焯的東西開始浮現。他們和當地負有盛名的“大師”王婆夫婦乘坐著那輛破舊的轎車開上土路,直到王叔隨口念叨著,“怎么這么偏啊”,突然之間,伴隨著暗下來的光影,有一種強烈的類型感撞擊了出來——它是一部標準制式的恐怖片,一些力量守株待兔,人們被欲望牽引,奔赴死亡。
《中邪》不戀血污,更接近驚悚和懸疑,切近于心理的恐慌而非挑動純生理反應。它的幾個陡坡式的心理懸崖設置得恰到好處,“中邪”的姐姐以一個沉默的正常人的面貌出現,之后在“治療”中第一次顯露出瘋癲,王婆夫婦從救治者變成膽怯者——換句話說,他們從主動方成為了被動方,這個轉化是被恐懼催化的,而同時,偷拍的攝像機發現了恐懼的根源——那些埋藏在心底的秘密,自己作為騙子和施害者一直擔心被報償;而在此之后,姐姐的“死亡”,以及更深一步的,死亡之后“冤魂”引發的混亂,都成為一步步潰散的節點。
客觀地講,對于大多數恐怖片資深影迷來說,從那個隱蔽的攝像頭揭露了王婆和王叔之間的嫌隙,彼此爭論曾經治死人的秘密的那一刻開始,這部電影就已經泄露了根底,但它還是用緊繃的氣氛拽住了觀眾。這個故事被巧妙地設置在一個近似封閉的空間中,無法逃脫的郊外,一座破敗的農家院,它的環境和人物設定都極度可信,對于這一類作品來說,這是代入感的堅實基礎。
從技巧上看,這部電影因陋就簡,但卻意外地達成了一種lo-fi的效果,偽紀錄片的鏡頭語言和粗糙的中國縣城以及濃重的幽秘色彩,經過互相疊加完成了一次劇烈的化學反應。鏡頭幾乎沒有錯漏,不存在偽紀錄片鏡頭之外的視角,肩扛手持拍攝的呼吸感與驚悚氛圍本身異常默契。末尾,那個碎裂的鏡頭,既符合劇情設定又為觀眾完美區分了視角。
從恐怖意象上說,《中邪》動用了所有最經典的符號:娃娃,飄蕩的尸體以及瘋癲的人,被恐懼調動起的黑暗人性,因仇恨被激發而成為殺戮者,它把這一切恐怖橋段和經典意象毫無痕跡地本土化為一種真實的中國經驗,而且,最終沒有歸因于怪力亂神,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復仇。從設置看來,這不是出于對審查的規避策略,而是從拍攝之初就定下的基調。
其實,很多恐怖片中都有一個明亮又樸素的內核——善惡有報。《中邪》也同樣如此,它是一個有關報償的故事,從另外的意義上,以極端的戲劇性手段,用私刑完成了一次懲惡揚善,而且最終,復仇者也遭到了法律的懲處。
中國恐怖片被合力摧毀了——從業者自暴自棄,審查者如臨大敵,觀看者嘲弄蔑視。但仍然有一些人能夠在狹窄的縫隙中努力維系自己以及這種電影類型的尊嚴。《中邪》只是認真地對待了這個題材,本分又充滿尊重地對待這個故事。它本土、自信又粗糲、鮮活。但愿這部作品是一個系列嘗試的開端,而不是一次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