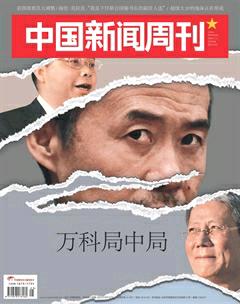王利明:“2020年完成民法典,我覺得有點趕急了”
韓永
6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這是該草案第一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過審。
作為民法典中最早編撰的部分,民法總則的制訂引人注目。從此次上會的草案內容看,它沿襲了民法通則的主體內容,同時又做了一些修改,其中關注度較大的修改包括: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限由十歲降至六歲;視胎兒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將訴訟時效從兩年延長為三年等。

這些修改,大多體現了正在發生變化的現實。但其中有些修改,還是引發了一些爭議。
就這些修改背后的邏輯,《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民法典編撰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民法學研究會會長王利明。
關于胎兒的民事權利,看法比較一致
中國新聞周刊:民法總則草案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限從10歲調到6歲,引起了一些爭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蘇澤林說,從10歲降為6歲,意味著從小學生降至幼兒園階段。而讓一個6歲的孩子承擔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不符合孩子的生理特征。這樣的調整是基于什么考慮?
王利明:原來(10歲)確實太高了。因為八九歲的孩子已經要買東西,坐車,從事一些交易,按照原來的規定,交易就無效了,因為他(她)沒有行為能力,這對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也不利。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現在兒童的心智水平和發育狀況,遠遠高于以前同階段的水平。另外,6周歲也是未成年人進入小學一年級的年齡,這一階段的未成年人能對自己的一些行為作出獨立的判斷。
所以當時討論以6歲上學為標準,將年齡下限進行調整,更好地尊重這一部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識,保護其合法權益。國外也確實有很多國家也是這么規定的。
中國新聞周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嚴以新認為,從10歲調整到6歲,步子快了一點。他建議調整到8歲。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年齡的下限,是否還有其他的選項?
王利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年齡的下限)究竟是6歲好,還是7歲8歲好,這倒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降下來還是對的。
中國新聞周刊:對中國孩子的成熟程度,有沒有一些數據的支撐?
王利明:有一些學者做過研究,可以證明10歲確實是太高了。
中國新聞周刊:民法總則草案第十六條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的保護,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民法總則》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基于什么考慮?
王利明:首先,這個規定跟墮胎是兩回事,不涉及(墮胎)這個問題。
民法總則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對胎兒的權益進行保護,以便胎兒出生之后能夠健康成長。
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從繼承的角度,要為胎兒保留必要的繼承份額,體現了特留份制度;第二,造成侵權之后,比如在出生前因不當行為導致胎兒的出生缺陷,胎兒出生后可以獨立請求賠償。
從案例來說,目前主要還是繼承方面,為胎兒留下特留份。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的看法比較一致。
對法人的分類爭議較大
中國新聞周刊:還有爭議較大的一個規定,是有關法人的分類。民法總則草案將法人分為營利性法人和非營利性法人。在對草案進行審議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萬鄂湘指出,傳統上將法人按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區分的做法,如在日本、中國臺灣等地,多已改為按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區分。民法總則草案的這種分法是基于什么考慮?
王利明:這個分法爭議很大,在學界也爭議很大。這種分類不能說沒有根據,主要是采用民法通則中企業和非企業法人的分類,是從那里來的。
但我個人認為這種分類太籠統,什么是營利性什么是非營利性,標準很不清晰。并且很多都無法分進去,像合作社,到現在誰也不知道它是營利的還是非營利的,國外一直存在爭論,都是兩種觀點。
中國新聞周刊:民辦學校好像也很難歸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佐書在審議時說,草案中“非營利性法人終止時不得向其成員或者設立人分配剩余財產”的規定,可能會讓很多拿出自己的房子、財物辦學的人打退堂鼓。在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改時,這一問題就曾引起很大爭議,并成為導致該法無法與其他教育法律修改一攬子通過的原因之一。
王利明:民辦學校也是這樣。本來應該是非營利的機構,但是又允許它獲得回報。我在這方面的主張,可以看看中國法學會的民法總則建議稿,是建議采用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的分類。許多大陸法系國家都采用這種分類,比較科學一些。
民法總則草案的這個分法,還是借鑒民法通則的一些經驗。但民法通則畢竟制定時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許多經驗不成熟,當時和現在的認識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互聯網因素有體現,但還不夠”
中國新聞周刊:草案第二十五條增加了子女對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父母的贍養、照顧和保護的義務。鄭功成委員在審議時說,中國目前已進入少子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的監護值得特別關注。過去村委會、居委會可以有效介入,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因此急切需要建立更加清晰、完整的監護制度。但他感覺草案這方面的規定還不夠完整清晰。
王利明:上述規定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反家暴法等法律中都有規定。此次在草案中,進一步強調了父母對于子女的撫養教育義務和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以強調家庭責任,弘揚傳統美德。
民法通則把監護的人群分為兩類,即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經過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補充,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老年人(60周歲以上),可以通過意定監護、法定監護和指定監護進行保護。但是,仍有部分人群沒有列入其中,例如一些高齡的空巢老人、智力障礙者等。因此,草案第二十一條作出“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人”的規定,將監護對象的范圍予以擴大,加強了對弱勢群體的保護。
中國新聞周刊:你之前說過,希望民法典的編撰能充分考慮互聯網的因素,這在民法總則草案中有體現嗎?
王利明:有體現,但很少。我一直呼吁,民法典的編撰要反映21世紀網絡時代的特點。立法機構也盡量考慮這些,為了進一步強調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促進創新發展,草案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類型進行了列舉,并明確將數據信息列入其中。
草案對于虛擬財產的規定,也可能是對這種呼吁的回應吧。這將會為一些法律制度的制定、一些新型案件的審理提供依據。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21世紀是互聯網的時代。如果說1804年法國民法典是19世紀風車水磨時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工業社會民法典的代表,那么,中國的民法典則應當成為21世紀互聯網時代民法典的代表。
我建議,民法典應該在五個方面反映互聯網時代的特征:一是強化對人格權的保護;二是預防網絡侵權行為的發生和擴散;三是有效規范個人信息的利用;四是規范網絡交易行為;五是豐富權利公示方法。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民法總則草案沒有更多地考慮互聯網因素?是有一些觀念障礙嗎?
王利明:(觀念障礙)倒沒有。有很多可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吧,有一些內容可能不好包括,就沒有寫進去。
中國新聞周刊:草案還有一個重要的修改,是將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由原來的兩年延長為3年。由你主持編撰的中國法學會民法總則建議稿,也主張將訴訟時效延長為3年。這是基于什么考慮?
王利明: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現行民法通則規定是兩年,學界和實務界一致認為兩年太短,一直在呼吁對此進行修改。現實中,由于訴訟時間過短造成的損失并不少見,例如銀行、金融機構等經常因為來不及請求、忘記或者舉不出證據,導致一些貸款不能及時收回,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延長訴訟時效,有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
中國新聞周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李適時說,民法典的編撰采用兩步走思路,第一步編撰民法總則,爭取提請2017年3月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第二步編撰民法典各分則,爭取于2020年3月將各分編一并提請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對這個日程和接下來民法典分則的編撰,你有什么建議?
王利明:現在想在2020年完成民法典,有點趕急了。我個人認為,進度還是應當服從于質量,分則內容十分復雜,技術性很強,總則相對還容易一點,最難制定的是分則。中國民法典制定舉世矚目,不必因為趕時間、趕進度,而不顧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