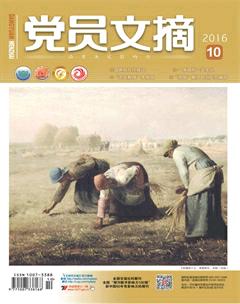一斤知識能賣多少錢
鄭依妮
知乎玩“值乎”“知乎Live”,果殼玩“分答”,百度玩“問咖”,一場“認知盈余”者通過社交平臺與人分享、并獲得收益的知識分享運動正在崛起
7月1日,知乎推出“值乎1.0”,用戶可將值乎消息分享到微博和朋友圈,被打碼的關鍵信息需要付費才能觀看;5月14日,知乎推出實時問答產品“知乎Live”,某些領域有特長的專家或“大V”可以創建特定主題、特定時間的Live并設置門票價格,用戶支付票價后,就能入群與答主溝通。5月15日,果殼網上線了后來紅遍社交網絡的付費語音問答產品“分答”,在“找人”一欄有這樣的分類:“這些年你關注的知乎大V。”
百度做了那么多年免費的“百度知道”,如今也想在知識變現上分一杯羹。讓人唏噓的是,值乎與分答的上線都先后刷爆了朋友圈,但幾乎沒人注意到百度在4月8日就推出了付費交流平臺“問咖”。
當“認知盈余”
碰上“分享經濟”
今年6月,馬化騰在新書《分享經濟》中,把“分享經濟”定義為公眾將閑置資源通過社會化平臺與他人分享,進而獲得收入的經濟現象。
閑置資源表現為閑置資金、閑置物品以及閑置時間,通俗說,就是閑錢、閑物、閑工夫。人們可以有償分享閑置的車輛、房子,也可以有償分享作為知識財富的認知盈余。據《認知盈余》作者克萊·舍基的說法,全世界受教育人口每年有累計超過一萬億小時的自由時間,如此巨量的認知盈余,以某種方式利用起來,可以產生超乎想象的巨大價值。
當“認知盈余”遇上“分享經濟”,一場知識付費運動就在互聯網上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人們突然發現,知識、經驗、技能也可以充實自己的荷包。《每周工作四小時》作者蒂莫西·費里斯說:“我為什么要把自己寶貴的時間浪費在學習那些冗長而枯燥的知識上面呢?如果我想要知道某些知識或信息,我可以去咨詢這個領域最優秀的專家,他們能給我最專業的指導和建議。我只需要向他們提出問題,花上幾分鐘或一小時的時間。”
中國的分享經濟正步入黃金期。尼爾森2013年的調查顯示,94%的中國受訪者都喜好與他人分享,排名榜首。尤其是90后,他們更愿意為專業經驗和生活解決方案付費,希望有專業的人告訴他“去北美留學和去硅谷找工作”或者“互聯網時代創業”的事情。他們不會再為了省一場電影票的錢,而在家里等著電影片源來下載,因為他們希望第一時間看到最新上映的電影,并且享受影院3D模式更酷的視聽效果。他們不再為了一款標價1.99元的手機APP而去破解手機,因為他們不想在玩游戲時還要被垃圾廣告騷擾。他們也不再隨便從網上下載泰勒·斯威夫特的新專輯,因為他們知道iTunes上能夠第一時間付費買到高品質的專輯。
專業人士頭腦中的信息
究竟值多少錢
在花樣百出的付費問答產品爭相上線后,人們不禁要問:專業人士頭腦中隱藏的信息究竟值多少錢?對這個問題,知乎Live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交出了一份成績單:上線47天里共舉辦了132場Live,總收入超過200萬元。而另一邊,分答上線的42天里,1000多萬的微信授權用戶創造了1800萬元的訂單金額,付費率是43%,并獲得了上億元的融資。
黃山是資深美酒達人,在威士忌和清酒圈是“大V”級人物。一個月前他就在值乎、知乎Live和分答上開設了以“大山”為名的個人專欄。在值乎上,他回答了5個問題,獲得135.5元的收入,并有將近2萬人的關注;6月,他在知乎Live開過一場關于清酒的Live,以一張19.99元的價格售出206張門票,當場收入4118元……黃山說他現在基本不去回答問題了,因為日常繁忙的工作讓他實在擠不出多余的精力去回答問題。
知識市場需要的是延續性,而不是短暫的爆款,過后就被人們拋諸腦后,但像黃山這種低黏性的優質“大V”并非少數。有調查發現,在維基百科中,是最有時間的用戶而不是最有專業知識的用戶貢獻并維護了更多的詞條。認知盈余與付費經濟的矛盾在于,認知盈余的行家往往時間并不盈余,而可以批量提供時間盈余的所謂行家,多半可能是認知不盈余的混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無可避免。
知識付費的時代剛剛開始,付費問答的商業模式已被大肆討論,有人已小有收入,有人還無法接受。但知識付費已經是共享經濟中兵家必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