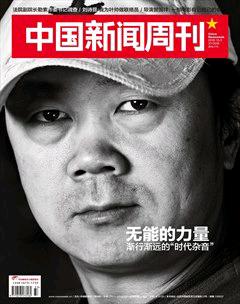到格拉茨拜訪藝術
張璐詩
格拉茨人口不過30萬出頭,這里有著行動派風氣:
旁觀、評論與記錄并不足夠,藝術家們更講求實踐參與。
每年9月至10月進行的秋季當代藝術節就是一個典范
6年前,奧地利人托馬斯與我在芬蘭的一次媒體團旅行中認識,一見如故。他比我大10歲,但并不妨礙我們推心置腹。
托馬斯來自格拉茨,也因此為我打開了一扇門。從5年前開始,我每年至少來兩次格拉茨,一次為6月的夏季古典音樂節而來,另一次則是為9月和10月的秋季先鋒藝術節(Steirischer Herbst)。
這是一個步行或乘幾站有軌電車就能走遍的歐洲小城,沒有大城市的交通成本,一天也就能拉得很長,看許多的景致了。特別的是,乍看與一般歐洲小城無異的格拉茨,在來了不下10次之后,仍讓我感覺到新鮮。這實在算是奇事。
前兩天,我從希臘海島飛格拉茨,去看秋季藝術節。機上鄰座是一對鹿特丹的老夫婦,他們聽說格拉茨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評定的“設計之都”,于是決定去看看那里的建筑和設計。我于是立即想到要向他們推薦自己十分喜歡的圣安德魯教堂。
這座始建于1270年的天主教堂可不一般。教堂經過了幾輪重建,2010年又經全面翻新,里外都充滿了一般宗教場所少有的現代藝術裝飾與裝置。比如說,你遠遠就能看到教堂門前的基督像上方刻著碩大的綠色英文字體:科幻小說。
新外墻是格拉茨藝術家古斯塔夫·特羅格的杰作。幾年前他以行為雕塑“玻璃人”聞名全球藝術界。他選擇了色彩世界中的50種顏色,將這些顏色與它們的名字以不同字體和大小印到教堂外墻上。他在日常生活經驗與教堂的“神圣”之間制造出張力,時不時就能讀到冷幽默:除了最顯眼的“科幻小說”之外,在“光環”上寫著小小一行赭紅色的“皮諾曹”,正門邊的墻上大寫著灰藍色的“懷疑”。他還為圣安德魯教堂的內部裝飾度身創作了三樣玻璃雕塑:一根連接地板與教堂穹頂的玻璃柱,柱子上切割成不規則形狀的玻璃片拼貼在一起,隨著日光的不同角度,反射出抽象而有趣的鏡像。
但這里并不是藝術展廳。教堂開發的手機APP會提醒你:這里仍然是“連通上帝與人類的精神空間”,藝術的角色只是打開一扇門,介入神圣與世俗的對話。
這次到了格拉茨后的第二天,我又到了圣安德魯“朝圣”,往回走時忽然看到那對鹿特丹老夫婦正向我走來,大家都驚訝得合不攏嘴。
教堂所在的Kernstock街也有一段故事。街名來自20世紀奧地利一位著名藝術家,但他二戰期間有親納粹之嫌,戰后這條街一直沒改名,遭到當地居民質疑。20年前,美國搖滾界涅槃樂隊來格拉茨演出,樂隊離開后,當地居民很干脆地將涅槃樂隊靈魂人物科特·柯本的名字放在街牌上,替代了Kernstock。不過最近不知怎么的,名字又換了回來。

藝術節的多媒體戲劇《鼴鼠之夜(歡迎來到洞穴世界!)》。
在格拉茨期間,每天我都與老朋友托馬斯見面,吃飯喝酒。他是老派新聞人,一輩子住在這個小城,與擔任奧地利綠黨發言人的太太一人一輛自行車,堅持不買車。與這樣的朋友交往,套用一句粵諺,是可以“牙齒當金使”的:說一句話,是一句話。和他可以提前一周約定某天幾點在哪條街的哪家酒館里,不需要短信或Facebook多此一舉的確認。每次都準時,從來不放鴿子。
有時作為旅行者的我日程不能完全確定,托馬斯會跟我說:每星期天,下午6點到7點,我會在那里,看報紙喝咖啡。你來就來,來不了就來不了。反正我在。
阿諾·施瓦辛格是格拉茨人。托馬斯的丈母娘會對每個來客說起她少女時代爬山扭了腳被施瓦辛格抱起過的往事。在格拉茨市中心有一個熱狗攤,門臉上掛了幾張施瓦辛格回家鄉來這里吃香腸的照片。我嘗了附近的幾家熱狗攤,這家確實是風味最佳的。
上世紀60年代,格拉茨由自由開明的斯泰爾人民黨執政,政府對文化藝術發展的投入是當時奧地利之最。實驗風起,建筑設計上的“格拉茨學派”也逐漸成型,基于傳統之上的創新與反叛精神十分濃郁,當時連首都維也納也只能望其項背。“格拉茨學派”的傳統今日依然強盛,與柏林、蒙特利爾并肩躋身全球“設計十強城市”。
格拉茨人口不過30萬出頭,這里有著行動派風氣:旁觀、評論與記錄并不足夠,藝術家們更講求實踐參與。每年9月至10月進行的秋季當代藝術節就是一個典范。它最初是一個學院型節慶,逐年進化,如今已是新藝術誕生與呈現的獨立平臺,以打破高雅藝術造成的障礙并極力跳出歐洲中心的視角為特色。
擔任藝術節總監已有11年的維羅尼卡·考普-哈斯勒的辦公室位于一幢18世紀的老樓內,樓對面就是一戰前夕遇刺的費迪南大公的故居。她告訴我,“中國人正在做些什么”,是他們初步設計的2016年藝術節的主題。“我們想探索與呈現中國在經濟之外、文化圖景方面的變遷。如今世上除了西方,還存在別的完全自主的中心,這種自主性是驕傲的歐洲與美國所不習慣的。”
去過威尼斯雙年展、巴塞爾藝術展的人,都能體會到藝術界是極為封閉和圈子化的。到紐約去看場戲,臺下觀眾也全是業界的。維羅尼卡說,當場互相交流時感覺固然良好,但她對藝術界這種井底之蛙的視野和自我安全感是反對的。“當代藝術工作者在人群中也就占0.1%吧。”因此,她所領頭策展的格拉茨秋季藝術節試圖從整體社會語境切入,觸及普通人的生活。
這兩年是歐洲的多事之秋,藝術節也將視角集中到了“老歐洲與它周圍世界的關系”之上。兩年前,藝術節就將把大批敘利亞難民推向偷渡船的“蛇頭”現象搬上舞臺。維羅尼卡希望觀眾跳出歐洲中心視角,用“去殖民化”的新思路去反思現狀。用她的話來講,到了今天,在臺上脫得一絲不掛、談論最私密的話題,早就不在話下;今天最大的丑聞其實來自政治,如難民的處境、歐洲對自身價值觀的缺乏反思等。去年和今年的藝術節,都能看到探討當前中國和非洲的貿易和文化現狀的舞臺與影響裝置演出“建設中的中非關系”,聚焦中國礦工在贊比亞欽戈拉地區的生活,直擊人稱“小非洲”的廣州寶漢直街的攤檔小販生態。
“前衛”是過時的名詞,現在說起都難逃諷刺的意味,但斯泰爾馬克之秋藝術節最獨特之處就是其先鋒性,每年都面向本地和國際征集各個領域的新藝術。
不輕易外租的格拉茨社會民主黨活動大樓這次破例借給了藝術節的核心項目“敞開”(Open Wide)。位于城市花園邊上的這個古典四合院內,由英國藝術家Morag Myerscough裝飾上明亮的粉紅色綢帶,搭建出一個門庭開放的亭園,寓意歡迎各地和各界人士,當然也包括難民。在藝術節進行的一個月內,這個亭園里每天由不同國籍的移民主持和組織活動,如非洲移民給大家泡茶,格拉茨中餐館老板來做飯,阿富汗移民唱自家民歌等等。
2016年藝術節以一場隱喻作為開幕演出。法國人Philippe Quesne創作了多媒體戲劇《鼴鼠之夜(歡迎來到洞穴世界!)》。碩大的鼴鼠是人類的比喻,它們像西西弗斯,花費全部時間去搬石頭;它們日夜在等候并不會發生的事情,令人想起賽繆爾·貝克特荒誕劇本里的角色,也令人聯想起柏拉圖的“洞見”說。
當然了,藝術節也不全是以形而上的形式探討社會意義的節目。一晚,我看了由比利時四人舞蹈劇團Need company演出的《永遠》。這場演出與中國文化很有關系。創作靈感來自馬勒的聲樂與交響創作《大地之歌》,而《大地之歌》的詞全部來自中國唐詩的譯文。《永遠》中的男主角全場一人清唱了這部作品的多首曲目。
舞臺上擺滿了“瓷器樹”,多片白色瓷器被大型裁紙刀切割成葉片形狀。四位舞者以肢體表現基于四季與大自然之上對生死的思考。最后,“瓷葉”從樹上掉落,跌碎一地,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