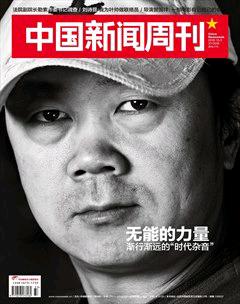“關鍵是,要活過斯大林”
云也退
活下來的都是有污點的人,至少是道德不夠完美的人,
我若描寫苦難、描寫集中營里人們互相壓迫、互相摧殘,
就難免要讓讀者覺得我比他們都高尚
“我寫的不是短篇小說,也不是什么個人回憶。”《科雷馬故事》的作者瓦爾拉姆·沙拉莫夫如此描述自己的書。既非虛構又非非虛構,那這些殘酷悲苦的故事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替他作個回答:在零下五十度的氣溫下,真實還是虛構,已經沒那么分明了。
科雷馬,俄羅斯的一角,東邊是太平洋,北邊是北冰洋,另一邊是群山聳峙,抵達這里尚且不易,更不用說逃出去了。沙拉莫夫所在勞動營就設在此處,一年有四分之一的日子,要在零下五十度的氣候里勞動。“古拉格”是蘇聯勞動營的通稱,國際異見分子大衛·魯塞率先傳播了它,后因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進入史冊。但就是索爾仁尼琴都承認,他受過的古拉格之苦,跟沙拉莫夫不可同日而語,沙拉莫夫所在的科雷馬是通稱“古拉格”的眾多蘇聯勞動營里最恐怖的一個。
1929年沙拉莫夫就曾被捕,罪名是企圖公開一封列寧的密信,三年勞役之后他被釋放,但在1937年斯大林發動“大清洗”時他再次“落網”,在科雷馬,他度過了整整十七年。索爾仁尼琴的話更有分量一點,“整個勞動營生活把我們拽進了殘酷和絕望之中。是沙拉莫夫,而不是我,觸及了這殘酷和絕望之淵底。”
節奏緩慢,因為沙拉莫夫要記下每個人說的每句話。大多數故事都是關于草菅人命的,比如《欠債賭》這篇,兩個老資格的囚犯賭博,賭到最后缺少賭注,隨手就殺掉一個資淺的“圍觀群眾”,將他的毛衣剝下來。《漿果》,寫一個囚徒生無可戀,多次激怒看守,看守指望把他引誘到止步警告牌那里,越過一點點就可以合法地槍殺他,誰知,他的一個難友,一個順從的、埋頭采集漿果給上級的人做了替死鬼。
在科雷馬,殺人完全是例行公事,被派來殺人的人自己也隨時有被抓的可能,但他們還是像冷血動物一樣,只知執行命令,守住崗位,心硬如石。沙拉莫夫的筆法與索爾仁尼琴相似,“情懷”則讓人想起了20世紀上半葉的俄蘇作家伊薩克·巴別爾,巴別爾的短篇小說同樣以殺戮為主題,寫蘇聯五年內戰的慘酷,國仇、家恨、民族矛盾統統摻和在一起。雖然都反映一個以殺人為常態的世界,但和巴別爾相比,沙拉莫夫更加沉痛,對于人性泯滅的體驗更深刻,更浸入,也更少旁觀者的嘲諷態度,他筆下的人物還不時地討論“我們該怎么辦”“為什么會如此”“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
索爾仁尼琴曾邀請沙拉莫夫合作撰寫《古拉格群島》,卻碰了一鼻子灰。沙拉莫夫曾說過,勞動營經歷可以造就一百個索爾仁尼琴這個級別的作家,卻只能產生五個托爾斯泰。沙拉莫夫的意思是別指望在勞動營里能產生悲憫眾生的偉人,從勞動營出來的人,誰也沒資格說自己要寫偉大的作品。
因為文學的使命是銘刻人性的光輝,而勞動營的苦難只能將人貶值,把優秀的人降為平庸,將平庸的人降為邪惡,根本不可能升華出什么人性來;與此同時,書寫勞動營,卻又不可避免地要帶上一種幸存者自我拔高的意識。倘若一個人總是慣于對自己的行為作嚴酷的道德考量,他一定會發現,對勞動營作“文學表達”是一件尷尬做作的事情。正像大屠殺幸存者、猶太裔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所說,他幸存之后心心念念的一件事就是“那些更優秀的人死去了”:活下來的都是有污點的人,至少是道德不夠完美的人,我若描寫苦難、描寫集中營里人們互相壓迫、互相摧殘,就難免要讓讀者覺得我比他們都高尚。
科雷馬是一切希望的墳場,雖然活著離開了那里,也終于開始寫作,沙拉莫夫認定文學創作只會扭曲他所經歷的事。我們經常贊頌絕境中人的堅持,但蘇聯勞動營里最頑強、最閃亮的堅持,也不過是一種詛咒,正如《一個魏斯曼主義者》這篇故事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勸誡所表現的:“關鍵是,是要活過斯大林。活過斯大林的人,全會活下來。您明白嗎?”
︻科雷馬故事︼
作者:[俄]瓦爾拉姆·沙拉莫夫
出版:廣西師大出版社
定價:11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