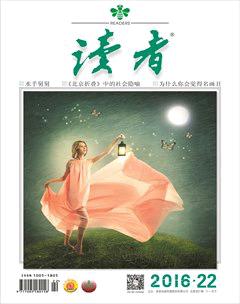木然的鄉(xiāng)愁
劉荒田
1874年11月14日,隸屬太平洋郵輪公司的“日本號(hào)”蒸汽船,在經(jīng)驗(yàn)豐富、聲望卓著的船長(zhǎng)華索指揮下,從舊金山起航,目的地是香港。它在航行26個(gè)晝夜后,于12月10日在日本橫濱港靠岸,船上補(bǔ)充了600多噸燃煤。次日,這艘擁有4個(gè)鍋爐、每日消耗燃煤45噸的巨輪往終點(diǎn)駛?cè)ァ4嫌写瑔T128名,客艙乘客2名,統(tǒng)艙乘客中,有歐洲人2名、中國(guó)人426名,還有975噸貨物(包含乘客的行李和在美國(guó)去世的中國(guó)人的靈柩)、168個(gè)珠寶盒(總值約30萬(wàn)美元)、21袋郵件。

3天以后,黃昏,船駛?cè)胫袊?guó)東海海域。15日,福州附近海面的白犬列島遙遙在望。這當(dāng)口,在舊金山碼頭付出50美元購(gòu)買(mǎi)最便宜的統(tǒng)艙船票的中國(guó)人,他們有怎樣的反應(yīng)呢?一位叫康奈爾的洋人寫(xiě)下他在船上看到的一幕。
“懷著些微憂(yōu)慮,望著福州一帶的中國(guó)海岸線(xiàn),這就是船長(zhǎng)說(shuō)的,我們?cè)絹?lái)越靠近的地方。一大群中國(guó)苦力從統(tǒng)艙擁上來(lái),為的是要看最先出現(xiàn)的陸地。他們出國(guó)以后,在加州待了很久很久,終于看到故國(guó)的海岸。幾個(gè)人問(wèn)我,這是中國(guó)嗎?我說(shuō)就是,他們發(fā)出微笑。然而,其他人冷冷地坐著,竭力抑制自己,不露出任何表情,一個(gè)勁地壓低聲音談話(huà)。懸崖近了,更近了,拂曉時(shí)分的天光益發(fā)明亮,空氣益發(fā)清澈。他們依然不動(dòng)聲色地坐著,都對(duì)別人的舉止毫不在意。
“更有甚者,直到船離岸近得連海灣里的垃圾和岸上耕作者的身影都清晰可見(jiàn),這些萬(wàn)里而來(lái)的歸人,臉上依然木然,連起碼的好奇心也沒(méi)有。”
關(guān)于還鄉(xiāng)的心情和姿態(tài),我們的祖宗以詩(shī)詞提供了若干范本,如“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的陶淵明式,“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wèn)來(lái)人”的宋之問(wèn)式,“兒童相見(jiàn)不相識(shí),笑問(wèn)客從何處來(lái)”的賀知章式……可是,沒(méi)有哪一種,比這一段白描更加令人震撼。
對(duì)這一類(lèi)乘坐從舊金山橫跨太平洋前往香港的蒸汽輪的中國(guó)人,另一個(gè)洋人以獵奇的筆墨作了如下描述。
“一個(gè)統(tǒng)艙旅客,是小個(gè)子,他告訴我,他在舊金山中國(guó)城當(dāng)廚師,老板包食宿,月薪50元。
“統(tǒng)艙旅客中的中國(guó)人,以男人居多,也有婦女和孩子,他們要回到中國(guó)去。他們之中有些人英語(yǔ)很不錯(cuò)。我問(wèn)他們?yōu)槭裁匆貒?guó),其中一個(gè)回答說(shuō),回去娶老婆,然后返回加州。我問(wèn)他是不是已選定一個(gè)了,他說(shuō)還沒(méi)有。我問(wèn)他娶老婆要花多少錢(qián),他回答,90塊錢(qián),娶個(gè)靚女,腳小小的。
“連有錢(qián)的中國(guó)人也住價(jià)錢(qián)比客艙少一半以上的統(tǒng)艙,圖的是統(tǒng)艙供應(yīng)的飯菜有故鄉(xiāng)的味道。
“獲得船長(zhǎng)的準(zhǔn)許以后,中國(guó)的樂(lè)手在后艙奏樂(lè),樂(lè)器有3件:一件類(lèi)似班卓琴,一件類(lèi)似小提琴(拉一個(gè)調(diào)子),一人以鼻音唱另一個(gè)調(diào)子,純?nèi)粸槿?lè),并不為錢(qián)。”
他還寫(xiě)了船上的中國(guó)水手:“每個(gè)早上,甲板都那么干凈,銅器都擦得閃閃發(fā)亮,全船里外都那么整潔,這些都是中國(guó)水手干的。本來(lái),帆篷的升降和轉(zhuǎn)向由機(jī)器操縱,一天晚間,我們正在房間或甲板上抽煙,所有的帆篷都被卷起來(lái)了,我們居然聽(tīng)不到一點(diǎn)聲音。既沒(méi)人咒罵、吹口哨、跺腳,也沒(méi)有人起哄。就是這些沉默的中國(guó)人,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悄悄地卷起所有帆篷,拖走了。”
在140多年前的龐然“孤舟”上,面對(duì)朝思暮想的故園,先僑為何如此冷淡?康奈爾先生必欲一探究竟。
他寫(xiě)道:“我終于找到兩個(gè)可以交談的人,下面就是我和他們的對(duì)話(huà)。”
“你們?cè)诩又葑×硕嗑茫俊?/p>
“差不多8年。”
“這一次你們回去是看望親人,還是做生意?”
“當(dāng)然是為了看望親人,可是我們不曉得怎樣找到他們。我們離開(kāi)前他們住在廣州附近一個(gè)村莊。不過(guò),除了5年前我們遇到過(guò)一個(gè)從村里來(lái)的移民,就再也聽(tīng)不到親人的消息。”
“你認(rèn)為他們還活著嗎?”
“希望這樣吧!沒(méi)聽(tīng)說(shuō)過(guò)有搶掠、災(zāi)荒什么的,他們也還健康。警察并不知道我們出國(guó)去了,應(yīng)該不會(huì)因?yàn)槲覀兌鵀殡y他們。”
謎底在這里:即將重履故土的中國(guó)移民,最大的心病乃是怕在多年音信隔絕后,他們將面對(duì)家散人亡。不錯(cuò),他們的腰帶里有金條,用多年血汗熔鑄的“衣錦還鄉(xiāng)”夢(mèng)想將變?yōu)楝F(xiàn)實(shí),哪怕只是可憐的縮寫(xiě)、改寫(xiě),好歹回家了!
所以說(shuō),在輪船上眺望家鄉(xiāng)的一幕,具有無(wú)與倫比的張力,以及催人淚下的悲劇力量。接下來(lái)的團(tuán)圓,曬金山箱,請(qǐng)客,一連串的熱鬧和風(fēng)光過(guò)去,平淡的家居日子,未必少得了煩惱和失望,但此刻,只有被懸念漲得近于爆裂的鄉(xiāng)思。
然而,正是這艘曾被馬克·吐溫稱(chēng)為“完美的船舶宮殿”的“日本號(hào)”,在船上的中國(guó)移民看到白犬列島的當(dāng)晚,因煤堆起火無(wú)法撲救而沉沒(méi)。兇猛之極的大火使人們無(wú)法接近救生艇,許多人被迫跳進(jìn)大海,然后被腰間塞著黃金的腰帶拖入海底,近400人喪生。他們刻骨銘心的鄉(xiāng)愁,也從此沉沒(méi)海底。
(余 娟摘自《羊城晚報(bào)》2016年3月8日,王 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