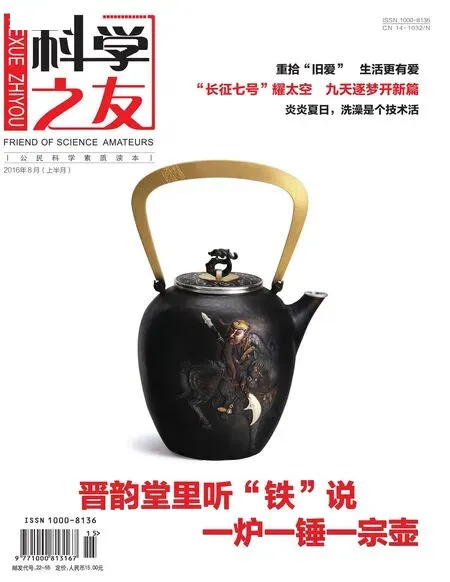圍觀螞蟻打架不只是童年樂趣
文|王企珂
圍觀螞蟻打架不只是童年樂趣
文|王企珂
它們可以吸引你駐足細心觀察,也能在你眼皮底下建立一座城市而不被察覺。它們有僅次于人類的復雜社會,卻又仿佛渺小的與人類的生活毫不相干。它們就是螞蟻,如此常見,可人類還是對它們所知甚少。螞蟻研究者工作最有趣的部分就是跟螞蟻打交道,和100多年以來無數的昆蟲學家們一樣,他們要干的活,就是花樣圍觀螞蟻打架,然后革新昆蟲學認知。
圍觀螞蟻的意外發現
看螞蟻打架估計是不少人的童年樂趣之一,而對一些昆蟲學家來說,這項樂趣以研究的名義延續到成年之后——1886年,時年38歲的瑞士著名昆蟲學家奧古斯特·弗雷爾就還在變著花樣地觀察螞蟻打架。那年8月,他將4種不同的螞蟻的觸角切除后放進了同一個盒子里。
在自然情況下,這些螞蟻一旦遇見就會相互攻擊。可這一次,它們卻并沒有表現出攻擊性行為,而是漸漸平和地聚集到了一起。到了第二天早上,這些螞蟻竟愉快地在一起玩耍了。這一場出人意料的“世界和平”,讓奧古斯特和其他科學家意識到,螞蟻的觸角應該可以感知到一些重要的信號。
可是,19世紀的科學家并不清楚觸角感受的信號本質是什么,有人猜想是觸角震動的頻率在傳遞一定信息。等科學家證明螞蟻是通過化學信號來分辨敵友的時候,已經是一個世紀后的事了。
用更高端的方式“挑撥”螞蟻打架
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人發現,只要往螞蟻身體上涂抹從別的螞蟻身上提取的有機化合物,這些螞蟻就不再被自己的同伴們當成朋友,而會被它們攻擊。不知道人們在為這一發現感到喜悅的同時,是不是也為這些慘遭“外星蟻”(其實就是人類)綁架,回家后發現所有朋友都不認識自己了的螞蟻感到過一絲心塞。但是話說回來,這些實驗仍然有一定缺陷——因為這樣的提取物組成其實很復雜,除了包括碳氫化合物外還包含一些別的有機物。
到了1999年,一群跨國合作的科學家開始采用更高端的方式“挑撥”螞蟻打架:他們首先提取了螞蟻身上的一組有機物,用一系列的純化工作將這些物質分成了碳氫化合物和脂類兩大類,再分別將這些物質的溶液涂在螞蟻身上。他們發現,只有碳氫化合物的組分可以干擾螞蟻的識別——如果在同一窩螞蟻身上涂上別窩螞蟻的碳氫化合物,這些螞蟻就會受到“室友”的攻擊。
至此,在奧古斯特的螞蟻為科學獻出觸角一百多年后,人們才終于確定,螞蟻是基于身體表面的碳氫化合物進行同窩識別的。事實上,螞蟻的絕大多數化學信號都是依靠這類蠟質的長鏈烴類物質來傳遞的。除了傳遞信息,這類物質還具有黏附、感受和防止昆蟲脫水等重要作用。
“你們夠了,能不能不再花樣‘挑撥’我們打架了?至少……別打觸角的主意了?”可惜螞蟻并不會發出這樣的吶喊。即使有,以人類目前的科技水平,也沒法聽懂。而接下來的研究者,將會再次利用小螞蟻們打破一項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
觸角,不僅僅是信號接收器
新的研究者就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馬克·埃爾加的研究團隊。他們注意到,大型動物會利用身體各部位不同腺體的產物來發揮不同的功能,比如標記領地、吸引異性、表現社會地位等。可是在社會性昆蟲的研究里,卻一直都假設昆蟲的身體表面信號是均勻的,而螞蟻的觸角則充當著信號感受器的作用。這個假設到底成不成立?
實際情況似乎復雜得多。最初,研究人員采用了簡單粗暴的方式展開調查——將澳洲肉蟻身體各個部位大卸八塊,分別研究這些部位的碳氫化合物組成。結果發現,同一個螞蟻不同身體部位的碳氫化合物,差別竟然比不同窩螞蟻之間的差別還要大。而且,不同窩的螞蟻彼此似乎都對對方的觸角更加感興趣,而較少去感受對方的足或者腹部。
一般而言,當不同窩的澳洲肉蟻相遇時,它們不但不去愛自己的鄰居,反而常常會相互做出一種帶有敵對意味的展示行為。有時候,數百只螞蟻會從早到晚在它們領地的邊界上這樣“打架”,形成夏天澳洲鄉間的一景。
不過,當研究人員改進先人研究的手段,將一部分螞蟻的觸角切除,將它們與完整的、不同窩的螞蟻放在一起時,我們發現它們不再能引起敵對行為。為什么丟掉觸角的螞蟻也就“丟失”自己的身份了呢?難道螞蟻識別是否同窩的信號,在于觸角之上嗎?

為了證明這一猜想,研究人員將螞蟻放在冰箱里“凍暈”后,小心地將它們觸角上的那些信號物質用有機溶劑除掉,再重復前面的實驗。果然,同樣的情況再次發生:這些被折騰過的螞蟻雖然可以認出對方是敵人,但是不再被當做敵人遭到攻擊了——簡直堪稱螞蟻界的間諜。
這樣的實驗,也第一次證明了昆蟲的觸角除了起感知信號的作用外,還能夠傳遞重要的化學信號,同窩識別信號至少是其中一種。這兩次異窩螞蟻間的和平,也再一次無情地宣告了人類對昆蟲如何交流的了解實在太少。
不斷探索帶來新發現
了解昆蟲的信號交流可不只是為了解釋螞蟻為什么打架或不打架。這些知識還可以應用在病蟲害防治、入侵物種控制和仿生學等方面。經典的實驗設計和實驗觀察能夠提供全新的觀點,新的研究手段和故事也必將繼續帶來新的發現。
下次,當你們再看見螞蟻打架時,不用為自己的好奇心感到不好意思——這已然是一項古老的傳統,從奧古斯特第一次將螞蟻的觸角切掉開始,這個故事就延續了100多年,還將一直發展下去。因為,在不斷探索這些行為的過程中,人類也在一點一點地改變昆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