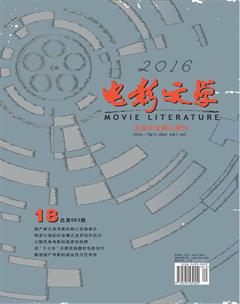陳可辛電影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摘 要] 是否能塑造出成功的、豐滿的人物形象,對于一部電影的成功至關重要。在表現具體的性別話語時,不同的導演有著不同的潛在傾向或優勢。從陳可辛塑造出的一個個面目鮮明、具有針對性的男性形象中不難看出,這位電影人不僅善于實現自己的藝術追求,也善于把握商業的脈搏,最終獲得票房與藝術的平衡。本文從男性形象與“被看”時代、男性形象與觀眾情感的激發以及男性形象與個性化三方面,分析了導演陳可辛電影中的男性形象。
[關鍵詞] 陳可辛;電影;男性形象
在現代社會中,無論男女,電影中的人物形象應具備的品質等也隨著人們觀念的變化而變化,但兩性在社會風尚、文化話語之中的形象又有所區別,應該分別看待。盡管當下絕大多數導演并不將其電影的受眾僅僅定位為男性或女性觀眾,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表現具體的男(女)性生活,傳達男(女)性話語時,不同的導演是有著不同的潛在傾向或優勢的,甚至有可能在其中帶有一定的性別刻板印象。香港導演陳可辛(Peter Chan,1962— )電影中有著光芒四射的女性形象,如《甜蜜蜜》(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1996)中張曼玉飾演的李翹,《金雞》(Golden Chicken,2002)中又如其擔任監制及制片人的吳君如飾演的金如等。同時,陳可辛電影中的男性形象以及由這些人物構成的男性群像,也值得人們給予一定的關注。
一、男性形象與“被看”時代
長久以來,由于社會分工的固化,女性一般居于次要的、從屬的地位,而男性則占據了生產生活主要的、主導的地位,女性是男性欣賞、觀看的對象。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在經濟、政治制度以及思想上的不斷進步,社會分工中兩性的差異已經逐漸由明確變為模糊,男性也可以置于被看的位置了。尤其是隨著消費時代的到來,包括電影在內的大眾文化開始以“娛樂化、休閑化、感官化趨勢勇往直前,大眾文化成為中國文化格局中一支不斷上升的重要力量”①。與此同時,中國電影中的男性形象從原本單一的勞動者與保衛者(如工人、軍人等)形象擴展到剛柔分化,男性在生產力提高的今天已經不必再與強調孔武有力的勞動、保衛等行為聯系起來,五官柔美,皮膚白膩,具有陰性氣息的“花樣美男”形象開始成為廣大觀眾追捧的對象,人物形象在被塑造時也開始強調文化、情調等更具個體意識的特點。陳可辛對于電影首先是一個工業行為這一點有著清晰的認識,曾經直言拍電影重要的是和觀眾“接近”,最忌諱的便是理想主義。陳可辛一直能夠及時了解大眾的審美需求,在保證電影藝術性的同時追求最大限度的商業利潤,他十分清楚在男性的“被看”時代應該給觀眾提供怎樣的觀賞對象。
如在《中國合伙人》(American Dreams in China,2013)中,陳可辛除了借用“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等人的創業故事外,還有意識地根據當下觀眾的需求為成東青、王陽以及孟曉駿三人打造了不同的形象。成東青出身草根,在成功路上一再受挫,先是考不上大學,上了北大之后又因為自己從農村來,口音奇怪而被同學嘲笑,畢業留校后又收入微薄且很快被開除,想去美國卻一次又一次被拒簽,直到開始創辦“新夢想”,他的人生才出現曙光。這是一個在當下流行話語語境中典型的“屌絲”形象,電影也借孟曉駿之口稱呼成東青為“土鱉”。這一形象能夠在“被看”的同時給予觀眾某種虛幻的、勵志性的希望,即成東青起點如此之低,但依然可以通過努力改變命運,那么條件相較成東青更好的人無疑也可以;而另一方面,陳可辛又有意回避了俗套的“失敗—成功”敘事模式。成東青盡管最后獲取了巨大的財富,但是他在感情上依然是失敗的,他不僅在曾經青澀稚嫩的時候失去了自己的愛人,并且在自己功成名就后重遇對方的時候,已經單身的對方不僅沒有重回成東青的懷抱,對他此時的身家也毫不在意。而孟曉駿則是典型的“海歸”形象。他出身優越,擁有他人不具備的英文功底,畢業后與女朋友雙雙順利去到美國。如果說孟曉駿在國外求職的挫折是因為在情節上要實現孟、成二人的合作,那么孟曉駿在入職“新夢想”之后才發現自己有無法在大庭廣眾之下說話的致命缺陷則顯然是為了迎合觀眾做出的藝術加工。作為一個“被看”的對象,觀眾顯然并不歡迎一個人生一帆風順或太完美的形象,由于孟曉駿前期的過分優秀,此時導演必須給予這個形象更多的弱點才能滿足觀眾將自己代入成東青后的心態。而王陽則是一個作為調劑品出現的“文藝青年”形象。他的長發,玩世不恭,熱衷于找外國女留學生說話,靠打乒乓球追到美國女友,甚至為了女友而放棄去美國等,都是陳可辛給電影制造娛樂感而添加的細節。甚至為了讓觀眾獲取更多“看”的快感,電影中有意設置了三個人赤身裸體洗澡,美國女友主動與王陽發生性關系,正好被成東青撞見,后者趕緊躲開的情節。這些與電影的“平民奮斗”主題無關,與整部電影的時代感也無關,但是有助于讓觀眾得到一個更有觀看樂趣的、吊兒郎當的風流才子形象。
二、男性形象與觀眾情感的激發
人具有多樣的情感,成功的電影可以通過敘事節奏恰到好處地調動、激發觀眾的情感,而在這其中,人物形象作為觀眾最大的共情對象,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并且電影與廣告等體量短小,追求更迅捷的傳播速度的媒介不同,電影中激發出來的情感并不僅僅是單純的道德感、理智感等,而是復雜的、流動的、人物與人物之間相互映襯的。陳可辛的電影往往圍繞著處于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展開,他關注著普通民眾的命運以及珍貴的情感,其電影中人物身上發生的諸般情節往往對于觀眾來說是真實而清晰的。這樣一來,觀眾的情感體驗也勢必是復雜多樣的,觀眾能理解電影中人物在浮沉的人世中的無奈選擇,并不會單純因角色的某些品質而對其進行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這些人物勇敢與怯懦、光明與陰暗等的對比又以體現在男性形象身上更為明顯。
在陳可辛“一女二男”敘事模式的電影中,這種對觀眾情感的激發體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在《雙城故事》(Alan & Eric: Between Hello and Goodbye,1991)中,阿倫與志偉便可以視作一對“對照組”形象。兩個人自小便是好朋友,都有著出海尋找“金銀島”的夢,成年之后又都愛上了女孩奧利弗。然而阿倫英俊瀟灑,溫柔體貼,并且有著唱歌的才藝,后來還成為當紅歌手,舞臺上的他讓奧利弗心動不已,兩人也就順理成章地展開了一段感情。而由曾志偉飾演的志偉則相貌普通,并且與立志成為歌星的阿倫不同,志偉勤勤懇懇地經營著自己的養雞場,在兄弟情面前,深知自己平庸的志偉只好將他對奧利弗的感情埋在心底。這兩個人中無疑后者更能激發觀眾的同情情感,可以說,陳可辛將阿倫塑造得越優秀和強勢,越是能讓觀眾產生對阿倫的對立者志偉的同情,盡管阿倫本人也并無大錯。尤其是在阿倫走紅后,仍然是蕓蕓眾生中一員的奧利弗與志偉都成為被冷落的對象,加上臺風對志偉養雞場的摧毀,導致志偉遠走他鄉當了一名居無定所的水手,更讓觀眾增加了對這個老實人的同情。而這種情感在十年后三人在舊金山重會時達到頂峰,志偉此時已經身患絕癥,三人在志偉最后的時光中盡情玩樂,向往著三人相愛,永不分離,然而電影依然以志偉的死結束。志偉與阿倫之間在外表、事業上有天壤之別,但是奧利弗又同時愛著他們兩個。志偉為了阿倫一直自我犧牲,怕阿倫失望,很早就揚言自己不喜歡奧利弗。這些都使觀眾給予他無限的同情。
與之類似的還有《甜蜜蜜》中同樣由曾志偉飾演的豹哥。與《雙城故事》中不同,豹哥在《甜蜜蜜》中只是配角,并且在社會地位上也與志偉不可同日而語,陳可辛安排豹哥與李翹的第一次見面時以一句“港督欠錢也得還啊,要不我們吃大便啊!砍他!”吸引了觀眾和李翹的注意,一個無法無天、粗暴易怒的黑社會老大形象瞬間便被樹立了起來,但是這一形象依然讓觀眾十分同情。電影中李翹一直喜歡著英俊溫柔,然而又因為外來者身份只能在香港苦苦打拼的黎小軍,出于現實的考量,她跟了其貌不揚的黑社會老大豹哥。豹哥在明知李翹心有所屬的情況下依舊對她百般包容,愿意在自己出事后趕李翹回黎小軍身邊,并且安慰李翹說:“回家洗個熱水澡,好好睡一覺,明天出去,滿大街的男人,個個都比豹哥好。”并且故意說自己有很多老婆在臺灣以打消李翹的愧疚之情,正是這句話讓李翹堅定了留在他身邊的決心。然而曾經叱咤風云的豹哥卻在美國街頭被小混混打死,李翹最終還是與黎小軍重逢。在電影中,黎小軍細膩敏感,但畢竟木訥,對愛情的處理拖泥帶水,既無法撇下青梅竹馬的妻子,也無法忘記在香港曾一同吃苦的李翹,而豹哥則給予了李翹蕩氣回腸的愛。觀眾無法苛責黎小軍,他貧弱的經濟基礎注定了他在感情上也只能進退維谷,而對敢愛敢恨,最終死在自己夢想前夕的豹哥,觀眾則會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同情。
三、男性形象與個性化
相比以虛妄晦澀之風見長的王家衛和開創“無厘頭”風格的周星馳等人來說,陳可辛所執導的電影本身并不具備某種強烈的個人風格,他對于愛情片、喜劇片、動作片以及恐怖片都有所涉獵,他樂于探索不同背景下的故事,并且盡可能地表達出具有深度的內容,如《如果·愛》(Perhaps Love,2005)中人們在愛情與面包之間如何選擇,《武俠》(Swordsmen,2011)之中法律與人情的對立等,這些話題之宏大,都是難以用簡單的話語闡釋清楚的。然而陳可辛電影中的男性形象又往往是被簡化了的,他們是高度個性化的,觀眾可以很快定位其身份、個性,并且這些不同的個性往往能迎合不同年齡段、不同背景的觀眾,以實現電影的雅俗共賞。
這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出現了男性群像的《投名狀》(The Warlords,2007)和《十月圍城》(Bodyguards and Assassins,2009),尤其這兩部電影的時間背景都距觀眾生活的時代有一定距離,因此,如何讓觀眾迅速在群像中辨別出不同的角色,除了運用明星效應外,便是使形象個性化。如《十月圍城》講述的是為保護孫中山,香港眾多市民在商人李玉堂、《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的組織下開展了一次“護孫”行動,上演了一曲亂世兒女有情有義的悲歌。其中李玉堂之子年僅17歲,是少數明白這次“護孫”意義的保護者,最后也為“護孫”而死。為了讓觀眾對這一人物印象深刻,陳可辛親自給其寫臺詞:“我活了十七年,原來就是為了這一小時,這一小時是國家大事,我們死了算什么……我告訴你,我每晚一閉上眼睛,就看到中國的未來。”
這些臺詞當時遭到了劇組其他人的反對,原因是太過天真直白,而陳可辛堅持使用這些臺詞,因為越是天真直白,越能塑造出一個熱血青年的形象。事實也證明,觀眾并沒有對其反感,而是深深為其中的理想主義情懷感動。又如在《投名狀》中,龐青云與趙二虎盡管納過投名狀結為異姓兄弟,但是他們是截然不同的人。龐青云是正統武官出身,胸懷大志,而趙二虎則是草莽中人,匪氣十足。陳可辛想借兩人形象表達的便是知識分子和武夫冰炭難以同爐的悲哀。而這一復雜話題是基于兩人迥然有別的個性(這也是由階級決定的)上的,并且個性直接導致了他們的沖突。龐青云在俘虜太平軍后違諾殺降,曾與太平軍談判的趙二虎痛不欲生,而趙二虎又曾在攻城后說過“強奸有什么不對”,龐青云則堅持執行軍紀斬殺了強奸犯。龐青云和趙二虎兩人在道德觀上都有污點,最后的結局也都是死于“自己人”手中,但是觀眾完全可以看出兩個形象的巨大差別。
從陳可辛塑造出的一個個面目鮮明、具有針對性的男性形象中不難看出,這位電影人不僅善于實現自己的藝術追求,也善于把握商業的脈搏,最終獲得票房與藝術的平衡。
[參考文獻]
[1] 胡智鋒.影視文化前沿“轉型期”大眾審美文化透視(下)[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
[2] 趙寧.論陳可辛電影的藝術性與商業性[D].太原:山西大學,2013.
[3] 沈冬娜.陳可辛電影作品的人物情感張力[J].電影文學,2016(04).
[4] 盧磊.陳可辛電影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15.
[作者簡介] 劉曉東(1964— ),男,重慶人,碩士,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傳媒藝術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視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