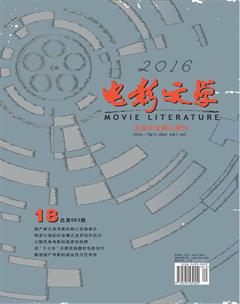多重視角下《狼圖騰》的生態美學解析
[摘 要] 電影《狼圖騰》改編自作家姜戎的同名小說,從前期籌備到后期拍攝,歷時四年,導演讓·雅克·阿諾才將姜戎書中描繪的人性、狼性與生態草原影像化,搬上大銀幕。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狼圖騰》的研究視角廣泛而多元化,本文在多重視域的審視高度,從生態美學的角度出發,對電影《狼圖騰》做一系統的研究分析,以期整理出從小說到電影的美學演變路徑,感受導演讓·雅克·阿諾在電影中建構的生態美學體驗。
[關鍵詞] 電影《狼圖騰》;讓·雅克·阿諾;生態美學
小說《狼圖騰》在2004年問世之初,就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關于“狼性”的話題潮,讀者將書中描寫的“狼性哲學”延伸至人性的范疇,甚至很多企業和團體更將這種“狼性”視作人類體內曾經具有、現在缺少的一部分精神層面的東西。作家姜戎在小說中描繪的讓人心馳神往的內蒙古大草原,人與草原狼之間的微妙關系和互動,以及世世代代依靠草原而生的蒙古人神圣的精神世界,既是這部小說改編成為電影的理由,同時也是改編的難點。2015年,電影《狼圖騰》終于和觀眾見面,從前期籌備到后期拍攝整整歷時四年時間,導演讓·雅克·阿諾才將姜戎書中描繪的人性、狼性與生態草原影像化并搬上大銀幕。
無論是小說《狼圖騰》還是同名電影,二者的美學呈現最大的重合之處是對于生態美學的極致表現,同時在小說和電影當中對于其他的美學也都有所涉獵。《狼圖騰》的研究視角廣泛而多元化,本文在多重視域的審視高度,從生態美學的角度出發,對電影《狼圖騰》做一系統的研究分析,以期整理出從小說到電影的美學演變路徑,感受導演讓·雅克·阿諾在電影中建構的生態美學體驗。
一、從小說到電影的美學演變
作家姜戎的著名小說《狼圖騰》并不是一部容易影像化的作品,書中對于草原狼的大量描寫為小說文本的影像化設置了重重障礙,如果缺少了對于草原狼的單獨呈現以及草原狼與人類之間的互動式呈現,對小說的改編也就無從談起。因此,電影版《狼圖騰》的制作過程異常艱難,從前期籌備到后期拍攝用了整整四年的時間,這對于一部商業電影來說,無疑是一次挑戰和冒險。觀眾對于電影版《狼圖騰》的關注熱情是否會隨著小說逐漸淡出讀者的視野而減弱,電影中呈現出的“草原狼”的草原世界是否能夠符合當下觀眾的審美眼光,都是電影改編遇到的考驗。因此,在前期籌備電影時,電影《狼圖騰》劇組就花費三年的時間訓練狼崽,為的就是能夠將草原狼的世界、人與草原狼共生的世界完整地呈現出來,尤其對于小說中描繪的“人狼對峙”“狼馬大戰”等具有轉折意義的關鍵性情節的影像化有著重要意義。
從小說到電影,導演讓·雅克·阿諾更看重的是小說中的神奇而獨特的草原文化和生態自然世界。導演讓·雅克·阿諾與作家姜戎有著不同的身份背景和文化背景,作為一名法國籍導演,他更加傾向于將電影《狼圖騰》作為展示內蒙古文化的媒介,而小說中所謂的敏感的“文革”背景則成為電影的敘事背景,虛化為一個歷史符號嵌入電影改編的故事當中。弱化了政治色彩的電影版《狼圖騰》對于草原文化的呈現更加純粹,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也更為明晰地映入觀眾眼簾,導演讓·雅克·阿諾進一步將姜戎小說中體現的生態美學在電影中放大,并使其成為電影創作的核心美學思想。讓·雅克·阿諾作為一名法國導演,其骨子里的人文關懷與浪漫風情,在電影版《狼圖騰》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呈現。
如果從美學角度來看,《狼圖騰》從小說到電影的美學演變,是一次具有現實意義的美學塑造和加強。作家姜戎在小說《狼圖騰》中以紀實性的寫作手法描繪了草原狼自由奔放、狡猾多端、不可馴服的“狼性”,與“文革”中的北京知青對于內蒙古草原文明的探索和狂熱,以及人們對草原生態環境的肆意踐踏導致的不可逆轉的惡劣影響。可以說,作家姜戎企圖通過紀實文學《狼圖騰》,呈現他眼中的內蒙古草原文明、“狼文化”,以及那個充滿盲目、激進和狂妄的時代,他企圖告誡人們正視破壞草原生態環境的錯誤行徑,期待人們能夠從草原狼的“狼性”中得到一些有用的生活啟示。
導演讓·雅克·阿諾則讓姜戎在小說中表達的現實主義更進一步。陳陣從首都北京來到偏遠的內蒙古草原腹地,親眼見證了草原人民與其世代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草原人民相信貪婪是導致災難的根源,唯有在一個彼此尊重的關系下,人與自然才能和諧共生。借著知青陳陣的雙眼,草原的壯美,狼群的神秘,人性的復雜、貪婪和征服欲,草原生態與草原人民精神世界的純潔和不可侵犯,狼群、草原在人類的踐踏下千瘡百孔,所有這些都一一呈現出來。在希望與毀滅、美好與丑陋之間的反復比對中,尤其在極具視覺沖擊的影像化語言的表現下,關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容和主題呈現出更為強烈的現實意義。
因此,在小說文本轉向電影文本時,生態美學得到了繼承,現實主義得到了加強,導演讓·雅克·阿諾將《狼圖騰》進行了從繁到簡的改編。
二、溫情與殘酷共生:敘事中的生態美學
生態美學是小說和電影《狼圖騰》主要呈現的美學方向,尤其在電影當中,導演讓·雅克·阿諾充分展現了法國導演在電影創作上的浪漫情懷和審美理想。在電影《狼圖騰》構建生態美學的過程中,透過一個簡單明了的二元對立關系將生態美學展現出來,即影片的前半部分極盡所能地呈現內蒙古腹地草原的神秘和壯美,到了影片的后半段則展現了在人類的欲望和無知的驅動下,純潔美麗的大草原生態被打破、毀壞,在美麗與丑陋、完美與損壞的比對中,實現了美學表達。
電影《狼圖騰》敘事中的生態之美在于,利用兩個不同的視角呈現了內蒙古草原腹地的生態和諧之美,一個是蒙古族畢利格老人的本土視角,一個是北京知青陳陣作為一個外來人的視角。北京知青陳陣初到內蒙古大草原時,遠離了紛繁復雜、吵吵嚷嚷的北京城,草原的遼闊和純美讓他禁不住贊嘆。在畢利格老人的帶領下,陳陣眼前徐徐展開的內蒙古腹地草原的優美畫卷讓他不能自已。在畢利格老人的眼中,草原是養育蒙古人的母親,草原是神圣的;而在知青陳陣的眼中,內蒙古大草原是一個古老而神秘的處女地,他急于探索其中的奧秘,而草原呈現的,也正是一種奇觀化的美。草原的生態之美,一方面在畢利格老人的引導和講述中呈現,另一方面則在陳陣不斷探索、不斷碰壁的過程中呈現。
同時,影片和小說相一致的,企圖在故事情節和戲劇沖突中呈現內蒙古草原獨有的生態美學。“人狼對峙”“狼馬大戰”等情節都表現了生態之美,導演讓·雅克·阿諾也在利用影像告訴觀眾,生態美學是一種人與其他生物、大自然和諧共生之美,其中也包含著大自然的生存法則,有弱肉強食,有血腥的犧牲,生態美學的內涵絕非一味地強調安逸的美好。
三、生態美學觀照下的人類精神世界
在作家姜戎的小說《狼圖騰》中,他借助北京知青陳陣的視角,展現的是蒙古族人民高尚而富足的精神世界,無論是蒙古族人民崇敬的騰格里,還是他們世代傳承的草原生態自然思想,都代表了蒙古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生態覺悟,無論是在陳陣的眼中,還是小說讀者、電影觀眾的眼中,他們都有著超越都市人的精神世界。
在土生土長的畢利格老人的眼中,廣袤的大草原有著自然的靈性,草原上任何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固有的規律和意義,人類需要尊敬自然、敬畏自然,對草原代表的大自然有獲取,也有付出。而蒙古族人世代口口相傳的關于狼的生存法則,則是蒙古族人民對于生態平衡思想的深刻理解。狼雖然狡猾、兇狠,但卻是守護草原、維護草原生態平衡的衛士。因此,蒙古人都敬重狼,在適當的尺度范圍內與狼爭奪食物,而絕不是從根本上將其趕盡殺絕。這種對于狼的敬畏之心,在攫取冰凍湖中的黃羊時可見一斑,蒙古族人只拿走了兩車黃羊,剩下的留給狼群過冬,因為他們深知,如果狼群沒有了存活的口糧,那么毫無疑問,它們將要襲擊村落,蒙古族人民將以血的代價還給狼群。
除了借助畢利格老人之口講述內蒙古草原的生態環境以及人與狼和諧共生的自然法則,影片通過兩次蒙古族天葬表現了根植于蒙古族人精神世界的生態思想,正如畢利格老人所言:“我們草原人生前吃了那么多肉,唯有以這種方式,將我們的肉還給草原。”蒙古族人的生態思想,讓他們取之于草原,也以自己的方式還給草原。
而陳陣代表的外來者,對于蒙古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十分好奇,但是外來者的身份使他即便聽畢利格老人講述了那么多草原精神和道理,仍然不免認為這些是一種自遠古時代傳承過來的道理,甚至有些是落后的思想。因此,從陳陣的精神世界出發,他想要改變這種傳統的思想,改變草原。但是,無法馴服的小狼,親眼見證了草原生態被外來者破壞,草原人民賴以生存的土地逐漸貧瘠,這些都讓陳陣理解了畢利格老人曾經說過的所謂的“傳統文化和精神”的正確性,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草原生態之美。
四、詩意鏡頭中的生態美學
導演讓·雅克·阿諾為了表現內蒙古草原的生態美學,從敘事方式到畫面構圖等電影語言,都著力發掘多種方式的美學表達的可能性。他將鏡頭語言的表達極致渲染,利用畫面內容、畫面色彩、畫面構圖的敘事性和隱喻性,輔助電影藝術的功能性表達。
影片開始,在一種過度曝光的不真實畫面色彩的渲染中,北京知青紛紛坐上大巴車前往祖國各地。畫面中出現的綠色山巒夾著蜿蜒迂回的山間公路,而陳陣等知青乘坐的大巴車蜿蜒前行,此時的下鄉知青正如同從北京輸送到全國各地的血液一樣,緩緩流動。在這里,導演讓·雅克·阿諾以公路隱喻血管,不斷行進的紅色大巴車串聯起來如同血液一般,在快節奏的鏡頭切換中,表現出了“文革”時期的大環境以及人們的精神面貌。入夜后,陳陣將視線投向車窗外無盡的黑暗中,此時遠處有一點微弱的光亮吸引了他的目光,這也預示了他對于未來的生活和陌生的世界感到無限憧憬、滿懷希望。
電影《狼圖騰》強調畫面構圖的功能性,表現人物的情緒狀態、精神世界以及故事發展的現實世界狀態,都在強調比例的畫面構圖中完成。為了展現內蒙古草原的生態之美,影片運用了大量的遠鏡頭,展現遠方地平線的邊界,完整地將內蒙古草原上的高低起伏、錯落有致的丘陵地勢呈現出來,在人物縮小為畫面中運動的一點時,人與自然之間的大小對比,自然對人類的包容狀態,大自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統統在遠鏡頭的畫面中表現出來。
而在畫面構圖上,影片結尾處,陳陣飼養的小狼重回自然,蒙古族老人畢利格被外來者埋在草原上炸狼的土雷炸傷、不幸死去。當拉著畢利格老人尸體的馬車出現在畫面中時,畫面被傾斜的山坡一分為二,左邊是送畢利格老人最后一程的眾人,畫面另一側則是從馬車上滾落在地面的畢利格老人的尸體。在視覺上傾斜的畫面和這種一分為二的構圖方式,一方面表明畢利格老人已經和眾人生死分隔,另一方面表現了作為陳陣精神導師的畢利格老人的死去,小狼被放回自然,都已經導致陳陣精神世界的顛覆,傾斜的不僅是陳陣此前學到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傾斜的畫面更代表了外來者對于草原的侵略導致草原世界的生態失衡。在影片的最后一個畫面中,草原已經不再是綠色,而是灰蒙蒙的一片,貧瘠的土壤和湛藍的天空形成強烈的視覺沖突。遠方的畫面中出現了小狼的身影,它在凝視陳陣許久后轉身離去,而陳陣也深情地呼喚著小狼。陳陣抬頭看到天上剛好有一朵狼形的云,顯然,遠處小狼的身影或許只是陳陣的幻覺,陳陣的理想與現實已經重疊,生態思想已經融入了他的血液中,他已經懂得敬畏自然、善待自然,在其內心已經涌動著回歸自然的生態呼喚。
[參考文獻]
[1] 電影《狼圖騰》詞條[OL].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205/10780875.htm.
[2] 李迪.原始草原的美麗與哀愁——《狼圖騰》的圖騰震撼與沖擊[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02).
[3] 顧斌.從生態批評視野看狼圖騰文化[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5).
[4] 段斌.《狼圖騰》的“文明形態”觀——從文化視角解讀《狼圖騰》[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3).
[5] 錢力.《狼圖騰》:法式浪漫與中國邏輯怎樣“合拍”?[N].光明日報,2015-03-02(014).
[作者簡介] 楊寧(1976— ),女,吉林長春人,碩士,吉林藝術學院設計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