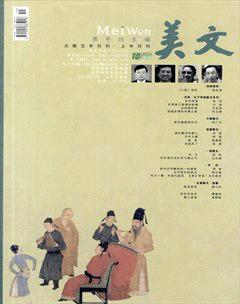閣西一夜聽落月
已近歲末。陰陽昏曉被時光的長鞭一抽,分明變幻,恍若發生在一夜之間。日光漸短,暮色卻隨著愁緒越拉越長。飄泊無依的我,無言地聽著黃昏奏出那一曲綿長的挽歌,看著邊城的霜雪漸衰漸弱,數縷銀魂空留下無邊的落寞,恍惚間,便已覺到了天涯。
自然是無心入眠了。那么就這樣吧,獨臥于一床枕席之間,聽那一夜落月。
我瘋了嗎?也許吧。但是旅居見聞告訴我,這里的夜帶來的大都是恐懼,而非睡眠。這里的人們,家中都有親人,在邊境駐守。區區兩里地,便是從民居到戰場的距離,每近一步,危險便增一分。
讓我聽一聽那落月吧!白日里我已聽慣了兵刃與馬蹄聲。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我醒著,月亮偏西的時候,光芒從西閣的床照到了我的臉上,我聽見它溫柔的低語,心稍稍安定了一些。
一切歸于沉寂,但我忘了,過分的沉寂永遠是爆發的前奏。
短促急切的號角聲尖銳地劃破了靜溢,接著響起的是沉悶的戰鼓。我驚坐而起,開始已經老花的雙眼看見天邊清晰地燃燒著一片火焰。抬頭仰望明月,現在才剛過五更,天還未明——天還未明啊!然而戰事已起,除了遭偷襲,還有什么別的可能嗎?
再一次聽見兵刃與馬蹄聲,伴隨著我的月亮漸漸偏西。光芒依舊皎潔,似能照入心靈,撫平傷痛。
但是它溫暖不了我啊!
冰冷的天幕墜落于三峽,星影在湍急的江流中搖曳不定。然而另一邊,在不遠處的戰場,戰士們的血液已匯集成另一個山峽。鮮血裹著夜空的清冷,在這黎明時分染紅了廣袤的大地。
我呆坐著,望向窗外,如同千百夔洲人家一樣,驚得發不出一點兒聲音。
悲壯的鼓角停滯。一片死寂。在這死寂中,我聽到了月亮的一聲嘆息。待回頭去尋,它已不知何時悄然隱沒。
前方戰地的大火咀嚼著余燼漸弱,同一個方向升起的初陽灼傷了盼歸者的眼。信使縱馬奔回,卻只在村口面對眾人神色凝重地搖了搖頭。曠野里,不知是誰哭出聲來,彌散開的聲音很快連成一片,這是一種直入肺腑的傷。
哭聲中響起了微弱的歌聲,溫柔,婉轉,似能撫慰人心。人們隨著低吟淺唱,他們所熟知的歌曲此時竟煥發出無窮的力量。他們唱著,哽咽著,忘情著,百感交集卻偏偏無人記得,這是一首夷歌。
我真的想過,也沖上戰場,佩劍披甲,在喊殺震天中揮灑豪氣,在鎩羽而歸時橫刀長嘯。然而那只是少年人輕狂的幻想罷了。現在的我只剩下老朽的身軀和簡單的筆墨書籍。作詩寫文不能平復蜀中大亂,何況我也是黃土沒到下巴的人了。人啊,這一輩子到頭不就只值那一個土坑,一塊石碑么?
難道不是嗎?不論當年運籌帷幄的臥龍諸葛,還是漢末躍馬稱帝的公孫述,他們早已沒于黃土,枯骨暗銹。對于生老病死的輪回,我又能說什么呢?承認。只能承認。
我的親人中,沒有人上戰場。他們都健在,此刻我本應慶幸,但卻感到了更深沉、更可悲的寂寥,寂寥得就像昨晚聽的那輪月。
我徙然地再次將目光望向窗外。歷經戰亂的人們心中的月落了,太陽卻遲遲沒有升起,所剩的只有甚于極夜的黑暗與冰冷。在淚水燃盡了的空洞雙眼中,再無光芒。
天已大亮。
黑暗,徹底泛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