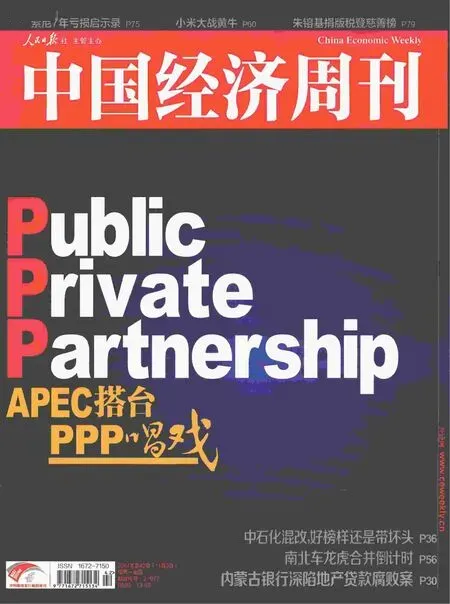以法治型市場經濟為目標重建經濟增長體制
黃衛挺
當前,我國正處于新舊社會秩序轉換的過渡階段。在舊的社會運轉機制和秩序不斷消解,新的機制和秩序尚未成型之前,大眾對未來的預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由于這種不確定產生于深層次的制度變革過程,其影響是系統性的。市場天生厭惡風險和規避不確定,經濟領域出現的民間投資意愿不強,資本外逃壓力持續等多與這種系統性的不確定有關。
經濟增長體制正在重建
從系統聯動的角度看,在新的社會秩序成型并有效發揮作用之前,經濟領域存在的這些問題難以徹底根除。而如何恰當地掌握秩序調整進度和力度,是一項考驗智慧的政治決斷,筆者并沒有足夠的智識對此展開分析。但是,經濟發展是維護內部穩定和拓展我國外部發展空間的最重要基礎,如何重建經濟增長體制,使其及早發揮穩定預期、規范市場和政府行為的作用,卻顯得尤為重要。在舊經濟增長體制不斷失效的過程中,新的經濟增長體制正開始逐步形成。
具體而言,舊的經濟增長體制主要由兩大關系構成,分別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央地關系)和“政府和企業關系”(政商關系)。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漸進式過程中,政府行為方式、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之間始終存在很強的聯動性。以過去30多年為例,在我國特殊的央地關系下,政府以發展經濟為重要目標,并通過手頭握有的權力對資源配置施加影響,最終決定經濟增長方式。央地關系影響第一個環節,即政府行為方式,政商關系主要影響第二個環節,即資源配置方式。當然,從市場化的大趨勢看,經濟領域中政府和企業的角色此消彼長,央地關系的經濟影響最終會在政府和市場邊界的調整中逐步弱化,但分析過去30多年的發展,第一個環節的政府行為依然非常重要。
事實上,以分稅制為象征的央地關系被很多學者視為中國經濟增長體制中最重要的制度設計,官員政績追求(或稱為“晉升錦標賽”)和地方財政資源最大化對各地政府發展經濟形成了強大的制度性激勵。這對創造中國經濟奇跡功不可沒,但同時也形成了很多短視的發展行為,如犧牲環境、一哄而上等。在政商關系方面,過去30多年市場邊界的擴張主要集中在產品市場,要素市場的市場化卻相當有限,這給各級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留下了重要手段。他們可以利用手中握有的土地資源以及稅收優惠等進行招商引資,形成了政商關系中相對中性的一面。但是,在權力監督機制不完備的情況下,不管是中央部門握有的審批權力,還是地方政府握有的土地、稅收優惠等可交換資源,也導致了一些公權私用、資本圍獵公權、權錢交易等違法腐敗現象,這些則是政商關系中現實存在的陰暗一面。
當前,中央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考核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但隨著反腐力度和官員紀律約束的不斷加大,政府官員及公務員群體的目標訴求、行為方式已經發生重要變化。根據官方媒體報道,不少官員從以前的“積極有為”轉為“為官不為”,一些中央政令遭遇到了執行層面的問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從以前的“座上賓”“家中客”轉變為“背靠背”,對于很多適應了舊政商關系的企業和企業家來說,面對這些新情況顯得甚為憂慮和無所適從。可以說,整肅吏治是一個催化劑,其影響超越政治領域,通過影響央地和政企兩大關系,使得舊的經濟增長體制逐步失效。
從長遠發展看,整肅吏治是一個好的,也是必須開展的工作,只是需要權衡和掌控好潛在風險,盡快建立新的秩序。從決策層發出的信號看,目前,新的經濟增長體制已露端倪。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以“親”和“清”為核心的新型政商關系;2016年8月,國務院對外公布了《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這些都意味著決策層已經關注到了經濟增長體制方面發生的變化,也預示著新的經濟增長體制正開始建立。
堅守法治型市場經濟目標
新的經濟增長體制必須有明確的目標,同時要與其他領域的制度構建相銜接。根據目前觀察到的種種信號,社會各界對決策層心中的未來經濟圖景存在一定的不同理解,尤其是走出經濟層面去思考,這種理解上的差異或許更大。但是,無論如何,站在更宏大的人類發展歷史進程去思考,新的經濟增長體制必須以形成法治型市場經濟為目標,這是我們必須堅守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重申和論述了“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等重要論斷,也反映出了決策層建立法治型市場經濟的立場。
從法治型市場經濟這個目標去分析央地和政商關系,可以找到重建經濟增長體制的主線。從中長期看,各級政府保有發展經濟的動機并不是壞事,只是應該在法治框架下,從制度設計上給予更為適當的激勵,比如優化政績考核制度。這也是《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的初衷,它所調整的是不符合發展趨勢的各種“不清晰、不合理、不規范”的地方,但仍堅持“調動和保護地方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與此同時,在市場化改革繼續向前推進的過程中,宏觀層面的政商關系,即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將繼續調整,當前的建設型政府最終將轉型為服務型政府。為此,央地關系調整在整個社會秩序調整中雖然很重要,但不是新經濟增長體制中最重要的部分,相反,政商關系的重建才是主線。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親”和“清”為核心的新型政商關系,并對領導干部和企業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被視為政商關系調整的基調,也引起了企業家和社會各界的熱議。筆者認為,以我國經濟轉型所處的階段,特別是在法治型市場經濟的目標下,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應重點關注以下幾點:
一是理念方面,除了進一步簡政放權,明確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邊界外,要重點矯正所有權差別對待問題。在一些政府官員心中,企業分為“官商”(國企)和“民商”(民企),在資源和服務支持方面差別對待,存在所有權歧視。在新型政商關系下,政府不僅要與官商親,更要與民商親,檢驗“親”的關鍵取決于政府和民商的關系。
二是制度建設方面,目前,很多官員和企業家對政商關系到底怎么擺存在困惑,存在“只怕不清,不怕不親”“保清棄親”等心態,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目標下,必須在制度層面劃定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的互動邊界,盡早出臺詳細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讓官員和企業家都吃下“定心丸”。
三是預期重建方面,新型政商關系能否發揮現實效用,取決于能否盡快重建預期。預期重建涉及很多方面,除了高層表態之外,應盡快從中央層面制定公布相關制度規則,并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一些案例性措施釋放確切信號。當然,在預期重建過程中,政府和企業恪守契約精神最為重要,特別是各級政府之前與企業訂立的契約,在不違規違法的情況下,均應該給予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