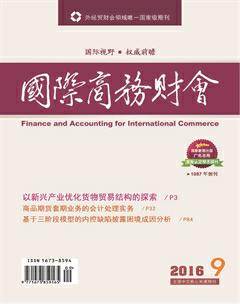我國碳減排的選擇——碳稅與碳交易的比較
管亞梅+王瑋
【摘要】在縮減碳排放量的措施中,碳稅和碳交易是最主要的措施,也是目前學界研究的重點,越來越多國家實行碳稅制度,世界碳交易體系也日益完善。我國雖然是排放量在世界前列的國家,但在減排問題上尚處于起步階段,碳減排之路任務重大。本文試圖對碳稅與碳交易制度進行比較分析,討論兩種措施的優缺點,以期為我國在未來的碳減排策略上提供一定參考。
【關鍵詞】碳稅碳交易中國碳減排
【中圖分類號】F124
一、碳稅與碳交易的涵義及現狀
碳稅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單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稅。在嚴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對于傳統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來分別征稅,以期達到延緩全球變暖速度的效果。碳稅機制下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則是碳排放的邊際成本與碳稅相等。從全球看來,美國、日本以及北歐各國等碳制度研究較早的國家都已陸續建立了旨在減少碳排放量的稅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稅制度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其碳減排已經取得了相當成效。
在我國,國家發改委聯合財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稅問題作出專題報告,報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應該首先推出生產型而非消費型的碳稅模式,即應先向排放碳的企業征收暫不針對個人。該專題報告不僅提出了我國碳稅制度實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碳稅征收的路線圖以及相關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議。
碳交易是針對全球碳排放總量而采取的市場機制措施。1997年,《京都議定書》上決定將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可交易商品,先嚴格限定全球碳排放總額,企業可以在碳市場中交易許可證,許可證額度內允許排放溫室氣體。從而形成了排放權的交易,目的是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尋減排新路徑。《議定書》同時規定了三種靈活履行機制,分別是:發達國家適用的“聯合履行”(JI)、適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以及“排放限額交易”(ET)。
我國碳交易方面,實際參與的只有碳交易體系中的清潔發展機制。2011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首次批準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湖北、廣東和深圳等七省市開展碳交易試點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啟動全國首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為中國碳交易的實施拉開了序幕。
二、碳稅與碳交易的比較分析
(一)減排成本比較
1.碳稅:實施成本低,社會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機制來說,碳稅的實施成本較低。碳稅以各國現有的稅收法律為基礎,其實施方式即為增加一個稅種。各國現有的稅收制度非常完備,并且已經存在燃油稅、資源稅等各類針對能源的稅目,碳稅可以在此基礎上開征,不必重新設計一種新的制度體系以及配備相關的機構設施。這不僅降低了碳稅實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隨時征收,減少為構建新體系花費的時間。同時,碳稅計量較碳交易簡單,征收環節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強。
但是就社會成本而言,征收碳稅有著諸多弊端,例如增加產品成本、通貨膨脹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時,很多人認為一旦征收碳稅,生產企業會將其稅負轉移到消費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稅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稅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僅影響國家經濟命脈的能源部門反對征收碳稅,消費產品的個人為避免稅負的轉移也不支持實行碳稅。所以,碳稅的征收不僅要考慮其實施有效程度,也要考慮社會成本,研究其會不會對健康的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2.碳交易:社會成本低,實施成本高
由于溫室效應是均勻分布在全球的負外部性,所以無論碳減排發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鑒于各國經濟發達程度不同,各地的減排成本卻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碳交易核定的總排放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利用地域成本差異,使碳減排成本最小化,這無疑做到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兼顧。《京都議定書》中設計的三種靈活履行機制確保了在各類不同的情況下,其減排都以最低的成本發生。從微觀層面來看,碳額度的交易比較靈活,在核定碳排放額度預計不夠的情況下,企業既能選擇從自身方面提升創新水平,也能選擇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場購買需要的額度,多途徑的實現碳減排的目標。
但是,構架碳交易體系成本卻很高。創建一個完善的新型市場機制對于碳交易體系的順利運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權變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國碳排放的具體數據,為了保證真實性,也具有監測成本。第二,為了使碳排放權成為稀缺資源,強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設立監管機構,制定嚴格的懲罰措施,產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場運作后,為了監測不斷波動的碳價格也給交易雙方帶來額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實際上實施碳交易的成本要遠高于理論成果,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二)減排效果比較
1.碳稅:減排效果不確定性高
理論上,碳稅的高低與實際碳減排效果呈現正相關關系,稅率越高,減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兩者間沒有確定的數量關系,量化困難。也就是說,碳稅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無法確切的將碳排放降到警戒線以下。同時,隨著碳稅的不斷增加,其碳減排效果存在邊際遞減效應,然而其減排成本卻有邊際遞增的效應,到達一定程度之后,碳稅的征收可能會導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業很可能將額外的碳稅稅負轉移給消費者,這使減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縱觀碳稅制度的實施國家,只有北歐國家由于經濟發達,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實施,剩余國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學界有觀點認為,僅僅依賴單一的碳稅來實現我國核定的碳減排目標可操作性低,同時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
2.碳交易:減排效果不確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優點就在于減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預計與量化。碳交易設置全球總排放目標后,根據一系列因素將其分配至各國,國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減排額,將其分配到地區,行業甚至微觀企業。通過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額不斷進行流轉,最終以市場來實現全球減排的目標。同時,輔以完善的監督機制有效管制各級排放主體的遵約狀況,保證減排的實施。
《議定書》參與國家承諾于2008~2012年間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減5.2%,這就為這些國家碳排放量設定了一個上限。根據世界銀行研究數據,在2005~2007年期間,碳交易體系使總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減少4 000萬噸~1億噸排放。同時,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機制幫助了許多不發達參與國進行低碳工程的建設。碳交易措施的減排量是確定的,這對延緩氣候變化有很大幫助。
(三)未來前景比較
1.碳稅:靈活多變,但前景不足
對比碳交易制度,碳稅制度更加靈活多變。碳稅作為稅種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權在各國政府稅務部門手中,稅務部門可根據對宏觀經濟的把握,隨之調整征稅范圍、稅率水平等。這樣可以使碳稅跟著經濟走,減少對經濟的影響,最大化提升其減排效果。
然而,額外開征碳稅對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較大。碳稅的較早征收國荷蘭,經濟一度受到較大的沖擊。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國征收20元每噸的碳稅,會使我國GDP減少0.015%,就業減少0.008%,出口減少0.548%,而碳減排僅僅為2%左右,若是繼續提升標準,追求減排量的達標,碳稅會使普通能源的價格提高,企業可能會將額外稅負以價格形式轉移到消費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損,這對于我國的社會發展有著很不利的影響,因此,碳稅并不是一個可以作為長期國策的制度。
2.碳交易:體系僵化,但前景廣闊
碳交易的體系設計比較僵化。首先,減排基準量的確定不準確。由于各國經濟差異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據減排基年判斷的減排基準量會有較大誤差,這可能導致某些國家配額過少,而另外一些國家配額溢出,從而出現浪費資源的情況。其次,制度的適應性與靈活性較差。與碳稅類似,最佳配額的確定與經濟發展情況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受到視野的限制,未來狀況具有不可預見性,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額計劃趕不上經濟形勢變化,產生過少的分配導致高昂的成本,過多的分配導致浪費的情況,經濟效率的實現非常困難。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場的構建正在持續加速。對于碳排放交易體系的構建成為當前全球能源規劃中的重要部分。據統計,全球碳交易額2007年為630億美元,2008年1 263.5億美元,2009年1 140億美元,2010年達到1 200億美元。據世界銀行預測,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額將提升到3.5萬億美元,漲幅驚人。隨著交易額的迅速攀升,交易額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場地位很可能將被碳交易市場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廣闊。
三、相對減排目標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減排的目標被分為絕對與相對兩種。絕對減排目標,就是針對總量進行絕對的碳排放削減,同時嚴格監督以達到預期的減排效果。而相對減排目標則較為溫和,以碳減排與產出值等衡量因素構造相對比例,不以重大經濟損失為代價而達到相對減排效果。碳稅與碳交易在這兩種不同目標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絕對減排目標,相對減排目標更加靈活具有彈性。但相對減排目標并不嚴格遵照減排總量,所以其減排效果具有相當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面對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雙重壓力,必須在其中尋找平衡點,所以中國選擇相對減排目標更符合現實需要。
相對減排目標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對總量進行絕對的碳排放削減,所以其減排目標有著動態性,不會出現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時,科技水平的上升會產生更多減排技術以促進減排。企業在碳稅制度下節約的排放額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廣闊的市場。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響,碳稅制度也能制約控制企業的碳排放。此時,碳稅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雖然在相對減排目標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強,但在完成低碳減排目標上具有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減排效果較好,這對于保持健康經濟下的碳減排有著積極影響。
結合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碳減排的實際經驗觀察后可以發現,對于不同類型的企業,碳稅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適用優勢。大中型排放主體由于其監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較大,從經濟效率考慮,推行碳交易比較合適。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體,由于其實施和監督成本較低,更適用于碳稅制度。從經驗中可以得出,當單個政策無法有效率的解決問題時,使用多層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較好的效果,所以結合我國實際國情,在碳減排問題上,應將碳稅和碳交易在時間的跨度上結合使用。
四、我國減排之路的建議
中國在國際上公開承諾大力推行碳減排,以2020年為目標年,我國單位GDP碳排放將會降至2005基準年的40%-45%。作為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任務,如何選擇適合自身的減排之路、實現社會經濟低碳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認為短期內采用碳稅措施,將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為一個長期規劃,是碳減排措施在中國實施的最佳選擇。
(一)短期采用碳稅措施
短期可以實行碳稅制度。減少碳排放有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兩種措施,分別對應碳稅和碳交易。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政府具有最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內運用行政力量鋪設好碳稅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減排承諾。在短期內,碳稅的征收并不需要額外的資金支持,只需在我國原有稅收體系中進行針對性調整即可運行。但在長期內,由于目前中國稅負已經很高,稅收體制改革勢在必行,長期征收碳稅加重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不具有可行性。同時,北歐、美國等發達國家十幾年征收碳稅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為我國碳稅制度的建設提供借鑒,例如確定碳稅的征收范圍,具有經濟效率的稅率設置,以及怎樣避免其對健康經濟發展的沖擊等。
在征收碳稅時,為了兼顧經濟增長的平穩發展,可采用稅收中性原則,即在征收碳稅的同時,減少其它稅收的稅率,最終保持稅額不變。或者將多出的稅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補貼或者投資,保持政府儲蓄不變,采用這種形式,補貼的對象應該針對高碳行業、主動減排行業、居民。
(二)轉型期采用雙策并舉模式
有學者研究顯示,采用單一的碳稅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國碳排放較基準年下降30.85%,明顯與我國承諾的40%~45%的減排目標有差距,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減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單一的碳稅制度還是單一的碳交易制度均無法讓我國取得合規滿意的效果。
通過上述的對比分析與兼容性分析,無疑結合實際國情,將碳稅和碳交易在時間的跨度上結合使用是一個較優的選擇。鑒于短期和長期所采取的政策差異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過渡時期內,可以采取改進的雙策并舉模式。這樣既可以在前期發揮碳稅靈活多變的優點,為碳減排的建設積累經驗,又可以為碳交易市場的建設提供資金與實踐,同時也可以接軌國際碳減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國碳減排大國的積極形象,此外也不損害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長期實行碳交易制度
中國作為聯合國CDM項目的最大實施方,卻只有CERs的一級市場,國際買家可以在中國市場上買入CERs在國際市場進行套利,這只會加大中國經濟與其它國家的差距,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在長期積極參與碳交易體系。
我國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壟斷行業中試行碳交易制度,這有助于緩解經濟沖擊。由于我國中小企業吸收了90%以上的就業人數,所以在大型壟斷企業中試行碳交易制度對整體就業的影響相對較低。而大型企業雖然也受到一些影響,但其巨大的體量決定其對損失的容忍度較高,不會對企業的生存造成重大打擊。同時,壟斷企業資金豐富,人才眾多,能為國家碳減排目標提供強大的創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給予企業較大的靈活度,相比于會造成經濟效率損失的碳稅,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無疑將經濟損失最小化。最后,我國不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場,而且要大力推動其國際化,爭取利益最大化。目前發達國家碳交易制度相對完善,我們需要緊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機。根據《京都協議書》,發展中國家在目前的碳減排情況上具有相對優勢,這有助于我國抓住機會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碳交易體系。殊途同歸,無論是碳稅還是碳交易,其目標都是保證世界碳減排的實施,可以綜合采用兩種手段,達到維護全球氣候的目的。
主要參考文獻:
[1]許光.碳稅與碳交易在中國環境規制中的比較及運用[J].北方經濟,2011,(06): 3-4.
[2]朱蘇榮.碳稅與碳交易的國際經驗和比較分析[J].金融發展評論,2012,(12) : 71-75.
[3]石敏俊,袁永娜,周晟呂.碳減排政策:碳稅、碳交易還是二者兼之?[J].管理科學學報,2013,16(9) : 9-17.
[4]鄭爽,竇勇.利用經濟手段應對氣候變化:碳稅與碳交易對比分析[J].中國能源,2013,35(10) : 11-15.
[5]陳洪宛、張磊.我國當前實行碳稅促進溫室氣體減排的可行性思考[J].財經論叢,2009,(1):35-40.
[6]魏慶坡.碳交易與碳稅兼容性分析——兼論中國減排路徑的選擇[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5):3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