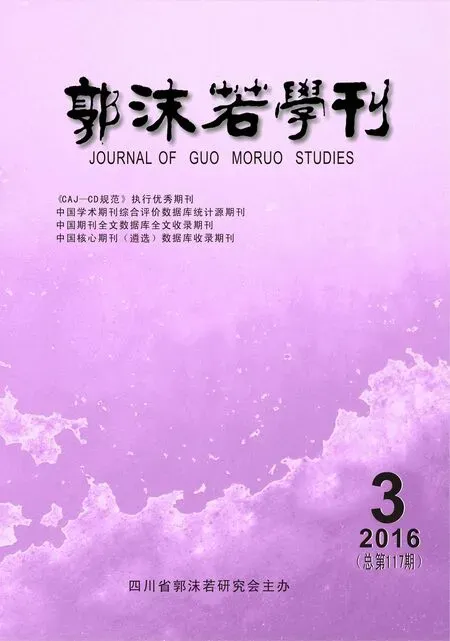長河中一小簇細微的浪花——巴金先生保存的“追悼馬宗融先生特刊”
李存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1)
長河中一小簇細微的浪花——巴金先生保存的“追悼馬宗融先生特刊”
李存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1)

20世紀前半期,巴金向被稱為“自由作家”,即在文學領域,他不屬于特定派系,是一個“自由的”個體。但巴金又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一批懷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志趣的文學工作者或文化、教育工作者,若隱若現地聚集在他的周圍,構成了一個有形無形的群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中鮮有黨派團體的“顯赫”人物,大都是一些“平凡”的人。這些人熱愛祖國家鄉,心系社會民生,追求真理信仰,埋頭認真工作,大都如巴金的《〈懷念〉前記》中所說:“那些人雖說平凡,卻也能閃出一股純潔的心靈的光,那是一般大人物少有的。他們不害人,不欺世;謙遜,和善,而有毅力堅守崗位;物質貧乏而心靈豐富;愛朋友,愛工作,對人誠懇,重‘給予’而不求‘取得’。他們是任何人的益友。我從他們那里得到過不少好處”。[1]469認識這些人的行為、情懷和品格、理念,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20世紀20-40年代某類中國知識人,也有助于解讀那一時期巴金的思想和作品。巴金最好的朋友之一馬宗融,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位年長者。
2012年,我在1992年出版的《馬宗融文集》基礎上,重編內容更豐富、收羅更完善的新文集《拾荒與拓荒》,立民寄來從巴金先生留下的大量書籍報刊等文獻中發現的一份報紙大樣圖片,使我如獲珍寶。該報右上側印有“追悼馬宗融先生特刊”九個手書大字,以整版的篇幅刊載了四篇文章和一首長達121行的詩。文章為胡鑒民《宗融與我》(未署寫作日期)、盧劍波《悼念馬大哥》(1949年5月14日作)、張履謙《記馬大哥》(1949年5月4日作)、謙弟《懷念》(1949年5月7日作),詩作為牧子《該活的人死了》(1949年4月25日夜9時作)。經我考訂,謙弟、牧子是張履謙的筆名,因此,五篇作品實際只有三位作者。這份“特刊”未及公開刊出、廣為傳播,但其中蘊含的信息值得關注介紹。同時,它留下的一些懸疑也需要做初步探究。
一
先簡略介紹作為“特刊”追悼對象的馬宗融先生。
馬宗融(1892—1949),四川成都人。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5年回上海后,開始翻譯法國文學作品,12月在《東方雜志》發表所譯第一篇法國短篇小說《倉庫里的男子》。此后,《小說月報》刊出他撰寫的《羅曼·羅蘭傳略》和長篇小說《紅與黑》、《巴黎圣母院》譯述。1929年,他與后來以筆名“羅淑”發表小說驚動文壇的羅世彌同返里昂,并在那里結婚。1933年冬偕妻女回上海,任復旦大學教授。此后,在陳望道主編的《太白》發表散文及多篇關于非洲、澳洲風土人情的“風俗志”,并在《文學》、《作家》、《譯文》等刊發表譯文、散文、雜文、論文和評介法國文學名家名著及文壇近況的文章。這期間,與巴金、靳以、方令孺、陳子展、李健吾、黎烈文等文藝界人士交往甚密。1936年秋,攜家赴桂林,任廣西大學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后返回成都,任四川大學教授。以極大的熱情,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文化活動,并發表雜文、散文和譯作。他多次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或候補理事,并兼任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政治部第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曾發表詩作《贈沫若》,[2]力挺郭沫若的心胸,熱力和文化貢獻。他還任“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五位常務理事之一,倡議并發起組織“回教文化研究會”,堅持回漢團結,強調社會進步。1939年夏任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教授,直至1946年秋。這期間結識了葉圣陶、老舍等眾多在渝文學界人士。老舍先生所寫幽默小品《馬宗融先生的時間觀念》[3],活脫脫展現出馬宗融那古道熱腸、天真有趣的生動形象,風靡一時,至今流傳不衰。1947年去臺北,任臺灣大學教授,與許壽裳、黎烈文、喬大壯等關系甚篤。1949年2月帶病攜子女乘船返回上海,4月10日逝于貧病之中,遺留的一女一子為巴金收養。
馬宗融先生的著譯散見于《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文學》、《作家》、《譯文》、《太白》、《新蜀報》、《抗戰文藝》等多種報刊,結集出版的有史著《法國革命史》、雜文集《拾荒》、通俗讀物《倫敦》和《羅馬》、寓言《蜜蜂與蠶兒》和《兩個狐貍》等,以及法國米爾博著短篇小說集《倉房里的男子》、俄國屠格涅夫著中篇小說《春潮》等譯著。馬宗融先生對我國新型的文學、文化事業別開生面的貢獻在于:
其一,他的著譯為新文學增加了新的成分和新的色彩。作為翻譯家,馬宗融先生是我國較早翻譯介紹法國文學和阿拉伯文學的人之一。他本著“于社會有益,于本國文學進步有些幫助”的宗旨,譯介阿拉伯和法國文學,他涉及的法國不同時期、不同流派作家就達20余人,顯示出他對法國文學的深厚修養和全面了解。他撰寫的《浪漫主義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阿拉伯文學對于歐洲文學的影響》等長篇論文,是30年代我國評析研究浪漫主義文學和阿拉伯文學的重要論文。他對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意義和方式方法的意見,眼光遠大,見解深邃,至今仍閃著動人的光彩。作為作家,他不多的散文、雜文作品始終貼近現實生活,始終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其散文題材多樣,知識豐富,不論是介紹域外風土人情,還是抒寫身邊見聞感受,大都有深邃的聯想、雋永的含義;其雜文發揚了魯迅的硬骨頭精神,或燭照黑暗、揭發丑惡,或禮贊所愛、頌揚正義,均文詞尖銳,真率明朗,充溢著憎愛分明、嫉惡如仇的凜然正氣。
其二,他不僅是一位獨立思考、耿直爽快、見義勇為、極有個性的可敬可愛的知識分子,還是中國現代文化、文學史上一位有著特別意義的回族人士。在現代中國,像他這樣既是學者、教授,又是翻譯家、作家和社會文化活動家的回族人,絕無僅有。他不愧為中國現代發起和倡導回族文學、回族文化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促進和推動抗戰時期回族文藝的第一人和促使回族文化主動融入多民族的新文化潮流的主要推動者。他撰寫的《我為什么提倡研究回教文化》、《理解回教人的必要》、《抗戰四年來的回教文藝》、《中華民族是一個》等,表現出開放的、富有遠見的、符合中國實際并具有時代精神的回族文藝觀、文化觀,至今仍富于啟迪意義。他既倡導發展本民族的文學和文化,又盡力倡導各民族間的互補和回族與非回族文藝家合作交流。中國回族文學是在像他這樣有卓識遠見者的倡導和推動下,才進入了自覺的時期,才主動融入了多民族的新文學潮流之中。他對促進漢回民族團結共濟,對增進漢回之間思想和文化的理解、溝通、交流所做的貢獻,在新文學發展的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這是觀照馬宗融先生文學建樹時應有的一個視角,和一個不應忘記的重要事實。
馬宗融先生逝世三十三年后,1982年農歷正月初五深夜,78歲的巴金先生坐在寓所的書桌前,沒有爐火,沒有暖氣,老人不顧手僵腳凍,寫作《隨想錄》第76篇——《懷念馬宗融大哥》。在這篇7000字的長文中,巴金先生以無限的深情和哀思,回憶與馬宗融這位“一見如故”的“長兄似的友人”二十年交往中的點點滴滴。他大方好客,愛書如命,熱情、健康,性格耿直,對人真誠。巴金說,他有一個長處可以掩蓋他一切的缺點,這就是他做到了“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巴金表示:“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的身上閃閃發光。”[4]353-3631992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紀念“紀念馬宗融誕辰一百周年學術座談會”,研討他的文學文化業績,緬懷他那真誠正直的人格。巴金送來花籃,冰心手書題詞稱他“愛書如命,嫉惡如仇”,曹禺為新出版的《馬宗融文集》題寫書名,陽翰笙、蕭乾等發來賀信,老舍夫人胡絜青題詞“急公好義披肝瀝膽博學多聞桃李滿園”,盛成、吳祖光、樊駿、馬賢、林松,老舍之子舒乙和學生鄒荻帆、苑茵(葉君健夫人)等60余位作家、學者、伊斯蘭教界人士與會。對馬宗融先生來說,這是一次遲到卻十分必要的憶念。
“特刊”詩文的撰著者胡鑒民、盧劍波、張履謙,也需略作介紹。
胡鑒民(1896—1966),江蘇宜興人。社會學學者。1921年到新加坡,在華僑舉辦的《新中華日報》社任編輯,后考入法國里昂斯坦斯堡大學,攻讀社會學、心理學等,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在法國與馬宗融和巴金先后相識。1931年春回國,不久受聘于中央大學,任社會學科教授。1936年受聘任四川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成都解放后,任文學院代理院長兼歷史系主任。1954年后辭去行政職務,專任歷史系教授。
盧劍波(1904—1991),四川合江人。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早年在瀘州等地從事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經重慶“適社”負責人陳小我介紹,開始與巴金通信。1922年到南京求學,參與創辦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鋒》,次年與巴金在南京首次見面。1928年于上海國民大學畢業后,在上海、四川教中學。1944年受四川大學邀請授課,1946年正式任教于四川大學直至逝世。1947年6月,巴金從盧劍波寄來的40多篇文章中選出26篇,編成散文集《心字》,由他主持編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在《后記》中寫道:“劍波是一個病弱的人。但是他卻有著極強的精神力量。他過刻苦的生活,做過度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不僅物質的缺乏折磨著他,他還受到常人無法從其中自拔的精神上的煎熬。”他“始終保持年輕人的認真與熱情”,他“不會失去他那顆‘赤子心’”。“雖然他至今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學教師,可是我喜歡我有這樣一個朋友,我更以能夠代他編輯這一本集子為我的光榮。”[5]345-3481987年10月,84歲高齡的巴金回故鄉,兩位同齡老友在成都最后一次見面。
張履謙(?-1957),四川人。筆名有謙弟、呂千、牧子、吳為等。早年與盧劍波一起在川南師范進行無政府主義活動,后來到長沙參加星社,出版《破壞》等刊物,1926年至1928年在上海參與編輯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鋒》。30年代初在成都主編《興中日報》副刊《大地》。20-40年代出版過《病中裁判》《婦女與社會》《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民眾讀物調查》《民眾娛樂調查》《暹羅紀行》等。1957年后曾在四川大學任教,后退職。
通過以上簡介,有兩點值得一提:
第一,三位作者不僅與馬宗融熟識,且都與巴金相識或熟識,盧劍波、張履謙是巴金早年在成都的同志和朋友,胡鑒民與巴金20年代末相識于法國。
第二,三位作者、馬宗融和巴金都與四川大學有密切聯系。胡鑒民、盧劍波、張履謙都曾任四川大學師長,其中,盧劍波、胡鑒民任教達三、四十年。馬宗融1937—1939年也曾任教于四川大學。巴金離蓉前就讀的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1926年并入公立四川大學,算是該校校友。
二
現在,該看看“特刊”上的詩文。
比馬宗融小四歲的胡鑒民是三位作者中的長者,也最早結識馬宗融,他的文章《宗融與我》列于刊首。文章開頭寫道:
生當這個年頭,誰不懷著一顆沉重的心呢?動不動要撞到□□①,舉目便見燹燧干戈,真是憂國憂民又憂己,怎令人不思盡望得“中山千日酒”,妄想著“酩然直到太平時”的幻境?
宗融兄的噩耗傳來更加深了,我這已經斷傷了的心病……
接著,回憶1922年冬在巴黎“一個心情很閑適的晚上,空濛的月色和零落的散布在拉丁區的街燈相映為輝的時候”,與馬宗融初次見面的場景,以及1929年在上海的交往和馬宗融對人類學的愛好。
盧劍波《悼念馬大哥》開篇寫道:
以沉默而哀痛地接受傳來的馬大哥的死信。
馬大哥魁偉,健談,朗爽,坦率,幽默,比起我他應該后死,可是,遇著這么一個時會,他反而先死。他先死,和我之拖著病軀還要拖下去而未死,難道是他的不幸和我的幸?
這是不堪回答的問題。
在這么一個“反淘汰”的年歲,他怎會不病?病了怎會不死?死對于殘存者只是一個時間的“晷刻”問題。
“瓶之罄矣,維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也!”
我要吟哦這一首“詩經”,以慰馬大哥“在天之靈”。
然而,文章簡述二十多年來與“馬大哥”的交往和情誼。最后說:
我記得他那坦直,朗爽,而又幽默的風格但他卻不是沒有棱角,沒有鋒芒,更不是那種泯滅善善惡惡之辨的“鄉愿君子”,他雖則沒有宗派教條意味,他卻有嫉惡與直指的真率和氣魄。這不合處亂世的“明哲保身”之道。但我喜歡馬大哥的地方卻正在這些地方。也正因為這些,所以他一樣否塞,一樣流離,一樣窮病,以至于“早”死,和那些敢于指斥社會之不公正,而倡導一種更合于理想□□□□□□組織與生□□□□□□,同其命運□□。
馬大哥譯作的數量頗不少,他曾贈送過我一章隨筆集子,可惜早不在身邊了,但我還記得他引證了不少人類學或文化社會學上的許多例證,以指駁那些閱見與心胸都窄狹的老頑固和新頑固。
但言文與肉身都會朽滅;也用不著替死去的老友傷感,“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我們相信“薪盡火傳”的真理與事實,即使有朝一日馬大哥之名,已消滅在人們的口上和心上,而馬大哥也是不朽的。
張履謙《記馬大哥》回憶抗戰爆發后在成都和重慶與馬宗融交往中的若干事例。其中有兩個細節。一是馬宗融在妻子羅淑(世彌)難產去世后的表現:
我記得世彌從醫院的病床上抬到樓下裝殮時,他□直是抱尸□□,那時一波、一萍和我三人曾拉開他若干次,他對世彌那種無邪的、童真的愛,使我們今天回想起來,真覺得是我們這冷酷的世界中少有的,而且也令我們這登報結婚,離婚的社會的人感到羞恥呵!
一是馬宗融與小學同窗,成都竹琴大師賈樹三的關系:
當他同賈樹三先生說話時,兩個人不但無新與舊的爭執,而且也沒有藝人教授的鴻溝。好像小學同學時的操場并肩走著散步樣的真誠,這使我非常感動。我有一天同李劼人兄說到這點,曾說,“宗融這人確不像我們這樣越大越不天真,越大越不長進;他實在是一個越大越天真,越大越長進的人!”
張履謙用筆名“謙弟”所寫《懷念》,與前篇的敘事不同,采用第二人稱直抒胸臆。
我們好似垂危待斃的衰弱老人,在惡劣的環境中要倒下去了,換句話說,便是不睡在死亡的棺里,也得掉在“奈何橋”下后回到人間前吃一碗“孟婆婆”的“茶”!
宗融兄,這就是我們今日的生活。在這生活中您是被考驗過,您是被折磨而且在您五十八年的歲月里,也曾目睹過不少被侮辱、被損害的血案,而且使您憤怒過,使您發狂過,竟走向了為萬人爭安樂,為萬人爭自由的路上。
就在這路上,我認識了您高大的個子,胖胖的身材,智慧的頭顱,和悅的臉譜,無邪而充滿了熱情與摯愛的心靈,愛人,您也被人愛的偉大。
我總沒有想到您這么健康,這么有活力的人會被病魔劫到墳墓里去,而像我們這樣瘦弱,這樣無活力的小弟弟們還生存著呵!
宗融兄,說您死了,說您患病而死了,這消息誰不驚駭,誰不驚駭?!
當我在十三號的報上讀到了臺大教授馬宗融病逝的消息時,我以為不是您,而以為臺大還另有一位馬宗融教授哩;因為我知道您已經回到了上海,并聽說您又接了復旦之聘。
但十六號接到一萍寄來航信,報告您病逝的消息,我又將十三號報載的新聞找來重讀,您死的噩耗竟證實了!
哀痛窒息了我,死亡威脅了我,宗融兄,您在我們心中燃起的愛焰熄了,播下的正義火種滅了。我沒有哭,我是呆著了,我一言不發地就在寫此文的桌前納悶了半天,晚間連飯也沒有吃便蒙頭睡了。
整夜沒有入睡,我的淚不由自主的流出,淚水濕透了被角,濕透了汗衫,到這個時候,才意味著您的死,您不復與我相談,再笑,再吃,再玩,再一塊兒工作了!
死,帶給了我以恐怖,帶給了我以迫害,而且把您給我的友情,給我的革命火種也帶到回教公墓里去了!
可是在您的墳前,我不僅未親手埋一撮土,而連最后的喪禮也沒有行一個,亡友,這該是何等殘酷的事,這懲罰將永遠地,永遠地伴著我長眠地下。
記得你由臺灣返滬療養時,我曾存心寫封信慰問您,可是,多次提起筆來均擱下了,原因是,在今天除了只許說“天氣好外”,其余話是不喜歡你說的。而今我們這時代,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時代,我們應當識趣些;這樣就一直到你的“死訊”從東海之濱傳來時,我還是沒有寫完那封信,而那封信怕也就永遠也寫不完了。
宗融兄,就讓我欠下您一筆信債吧!
張履謙用另一筆名“牧子”寫的詩歌《該活的人死了》,朗聲贊揚馬宗融的品格信念,嚴厲指斥社會的黑暗骯臟,沉痛悲愴,激憤之情溢于言表。全詩值得引述:
我們的世界,
該活的人死了,
不該活的人活著,
宗融兄,
這便是自古以來的人哲理,
“好人命不長
禍害一千年。”
你這走近花甲的好人,
不死也應當“生藏”?
在這個男盜女娼的社會內——
你是越大越天真,
越大越進步,
不向豪門拜倒,
不向權貴乞憐的傻子——
你貧,
你病,
你死,
寡婦孤兒無人照料,
亡妻墳塋無人祭奠,
——那是活該!
而今人類,
還是走不出: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道路,
宗融兄,
你撫養過你的孩子,
你育過的學生,
何能了解你不向勝利者,
不向強權者
低頭,崇拜的“理想”,
這世界,
是有“強權”的勝利者的世界,
這社會,
是擁有“奴隸”的資產者的社會,
這人群,
是口蜜腹劍的偽善者的人群,
像你這樣愛真理,愛世界,
愛自由,愛和平,
宣傳正義的窮教授,
——怎能生存!
你該死,
該死在這迷信強權,
殺人不眨眼的烽火漫天的時代,
在你的幼年,
飽嘗過寒冷與饑餓,
在你的青年,
輟學而做過錦城的警兵,
在你的壯年,
沖破云圍工讀與革命的巴黎首都,
在你的中年,
曾執教于天南地北的各個大學,
盧溝橋的反侵略的炮聲響了,
你逃亡,
回到了你的故鄉,
留給你的:
只有亡妻的悲痛,
孤兒的哀傷,
你的血,
你的淚,
你的汗,
流盡了,流盡了,
卻沒有療好你的創傷,
是生活壓迫你,
是思想苦惱你,
作了工商業社會中的游牧時代的人,
在戰爭中流浪,流浪,
逃亡,逃亡,
一家五口,
離開了只宜養花的蓉城,
寄生嘉陵江上,
在忍饑,受難的歲月中,
渡過了二次大戰的洶濤黑浪,
世界敵人倒了,
以血洗血的崎嶇道走過了,
和平的勝利,
光榮的日子,
終于來到,
我們慶祝勝利,
我們高歌勝利,
而且卅四年,
在錦城的朋友們,
也曾為你五五的壽辰,
舉杯祝賀你精神不老!
呵,誰知今朝,
誰知今朝,你竟與我們永別——,
從臺灣,
到上海,
一病九月便慵慵地死掉,
我不知道,
你是否有遺言(?)
你彌留時是哭(?)是笑(?),
你一生為真理奮斗,
為信念犧牲,
為愛而忘餐,
為情而廢寢,
在生之歷程中,
你并不是只開給我們一張空頭支票。
你的誠摯,
你的坦白,
你的豪爽,
你的熱情,
是永遠地,
永遠地烙印在我們心上。
你魁偉的軀體,
有力的拳頭,
慈愛的笑顏,
無邪的心靈,
也是永遠地
永遠地會令我們不能忘卻,
宗融兄,
□□,
狂風在吹,
暴雨在落
你教養過的孩子沒有了你,
你撫育過的學生沒有了你,
朋友們也沒有了你,
這世界,
該是何等的凄涼,
這社會,
將是多么的凄涼,
這人間,
該是怎樣的感傷……
三
說到馬宗融先生的離世,不能不聯想到他的妻子、作家羅淑病逝后文壇的反應。1938年2月27日羅淑因產褥熱在成都去世后,成都《華西日報》3月6、7日連出二期“幻想羅淑逝世特輯”,揭載鄧天矞、毛一波、謙弟、沙汀、吳先憂、周文、陳翔鶴等的紀念詩文。6月,巴金、靳以編輯的《文叢》第2卷第2號開辟“紀念羅淑女士”專欄,發表黎烈文、巴金、靳以的悼念文章。此后,《魯迅風》1939年6月第16期以《寫在羅淑遺著的前面》為題,刊發巴金為羅淑小說集《地上的一角》所寫《后記》;《文藝復興》1946年第1卷第6期“抗戰八年死難作家紀念”專欄發表李健吾《記羅淑》。
以馬宗融先生的人脈、人望和影響,他離世后,各界人士的悼念和追思肯定紛至沓來。不幸的是他死不逢時。是時,社會正待巨變,歷史即將翻頁,上海物價飛漲,人心忐忑。他在這個時段去世,“凄然一棺,蕭條身后,子幼女弱”(《募集馬宗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啟》),情景冷落而凄涼。
1949年4月12月即馬宗融遺體殯葬那一天,方令孺、巴金等82位文學、教育、新聞出版等界和伊斯蘭教界人士聯名發布《募集馬宗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啟》②,全文如下:
馬宗融先生以本月十日病逝上海,享年五十八。噩耗傳來,凡在知好,同深悲悼!宗融先生一生獻身教育,從事譯著,溝通回教文化,貢獻良多。而其為人性情真率,仗義勇為,熱情盈溢,朋友皆敬而愛之。今忽于兵戈擾攘之中,和平將臨之際,溘焉長逝,凄然一棺,蕭條身后,子幼女弱,后死者能不興悲!同人等集議,擬以薄奠之儀,為賻贈其教育基金。如荷海內友好贊同斯議,敬祈寄交:
江灣國立復旦大學靳以
巨鹿路一弄八號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
北京路二六六號中一大樓四樓文摘社
中正中路三九七號同昌首飾商店
為感!
1949年4月12日,上海《大公報》以一幅照片和一則簡訊報道馬宗融逝世。簡訊《馬宗融遺體昨舉行大殮》稱:“著名文藝翻譯家馬宗融,于十日在滬病逝,昨天上午在上天殯儀館大殮,文藝界李健吾、巴金、靳以、梅林等都參加祭吊。馬夫人現在臺,不及趕來奔喪,只有馬宗融的子女馬小彌(女)、馬紹彌(子)守在靈邊。又,馬氏遺體定今日上午十時,在徐家匯清真別墅(亞爾培路口)遵回教教典舉行殯葬儀式,并安葬于回教公墓。”簡訊上部配發的照片是4月11日巴金等四人與馬宗融遺體告別的場面,說明文字為:“圖為大殮時前往吊祭的文藝界人士,左起第一人為巴金。”此后,各地不多的報紙有簡短消息披露。至于哀悼文章,目前我查到的只有波多(即林松,回族)《哭宗融先生》③和濟生(巴金胞弟)《悼念馬宗融》④等寥寥幾篇,與十一年前妻子羅淑去世后的反應形成鮮明對照。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已經編竣的一整版“追悼馬宗融先生特刊”,殊為難得。
這版“特刊”的大樣當是最后一校,按四開報紙的版式編排,上端無報頭、日期(或許是待報社確定日期后再嵌入,因為報紙的報名大都是特殊字體),下端無廣告,頁面有明顯折疊揉皺痕跡,文字總體清晰但有若干文字因油墨過深難以辨識,還有五處被油墨黑團遮蓋。目前我沒有查到這份“特刊”正式刊出的線索。這樣就留下疑問:“特刊”依托的是何地、何種報紙?為何沒有正式面世?“特刊”大樣又何以保存在巴金先生手中?
何種報紙無從考查,但此報所在地和大樣何以留在巴金處,我揣度有兩種可能:一是上海某報。在成都的三位作者集稿后將文字稿寄巴金,依托上海某報編排付印,但因政權更迭或其他原因未能正式刊出;二是成都某報。依托成都某報編成并排版,終因故未能出版,后將報紙大樣轉送巴金留閱。我以為,最大的可能是后者。理由有二:
其一,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12日解放軍發動上海戰役,26日解放上海主要市區,27日上海完全解放。據“特刊”各篇作者所署寫作日期判斷,“特刊”最早編成于5月后半月。如從成都將文稿寄到上海,當是五月末甚至六月初了。成都組稿者已知上海情況,還從國統區寄去稿件,可能性不大,而上海在新政權剛剛建立之時,以專版公開悼念剛從臺灣返滬的馬宗融是否合時宜,也是一個費斟酌的事情。偏居西南的成都,情況有所不同。1949年上半年,成都雖然形勢緊張,人心不穩,但尚有言論的間隙。11月解放軍發起成都戰役,四川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相繼宣布起義,12月27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30日解放軍入城。因此,五六月間還有悼念“非共人士”馬宗融的空間。至于為何沒有正式見報,有多種可能,除當事人外,我輩無法揣度坐實。
其二,特刊題名的字跡與大樣校改文字筆跡相似,應是胡、盧、張三人中之一。我推測文稿的組織者和匯集人最大的可能是張履謙,刊名書寫和校改也可能是他承擔。一則在三人中,張履謙是列入82人署名的《募集馬宗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啟》唯一的一位;二則他一人為“特刊”獨撰二文一詩,熱情最高,且他同成都報界熟絡;三則大樣上的五篇作品,胡鑒民和盧劍波的文章無一字改動,有改動的只有張履謙寫的三篇,除去改正手民誤植的文字外,還作了一些字詞修改,如《懷念》中“一萍寄來航信”中的“寄來”原文為“復來”,“我一言不發地就在寫此文的桌前納悶了半天”中的“寫此文的”四字是校樣增加的。又如,詩作《該活的人死了》中“便”原文為“你”,“永遠地烙印在我們心上”中的“烙印”原文為“燒烙”,“你撫育過的學生沒有了你”中的“學生”原文為“人類”。這樣的改動當為作者自己所為。我無渠道見識張履謙的筆跡,這一判斷尚不能完全確認。
我還有另一種揣測,提出聊以備考。這就是組稿者有可能將稿作寄給正在重慶的巴金胞弟李濟生先生,⑤由他依托重慶某報排版出樣并將大樣寄成都校區。大樣校畢返渝后卻未能正式刊出,他只好帶回上海,交巴金先生一閱。就局勢和環境看,解放軍1949年11月27日、28日相繼攻克重慶外圍的江津、順江場、漁洞鎮等據點。30日進入重慶市區,五月末六月初籌劃在重慶發表“特刊”還是有可能的。
得見“追悼馬宗融先生特刊”這份欲公開披露而終未如愿的佚報,不免令人心生感慨。像馬宗融先生這種正直坦率、剛烈豪爽、一身正氣、可愛可敬類型的知識人,當時不多猶存,現今稀缺難覓,是幸事抑或是不幸之事?在特殊時段編排就緒追悼馬宗融先生的“特刊”,這一行動所體現的友朋情誼、良知閃光、正義追求,是無謂之舉抑或是值得珍視?我的回答是后者。在歷史長河中,“特刊”絕非巨浪驚濤,不過是尚未翻卷就轉瞬即逝的一小簇細微之極的浪花而已。六十七年后的今天,能夠摘取并定格這簇細小的浪花,要衷心感謝一直保存著它的巴金先生。
(責任編輯:王錦厚)
注釋:
①原報中殘損或完全無法辨識的黑團文字用方空格□表示。以下詩文同。
②本啟單行印發,未在報刊揭載,發出后也未實施。82位署名者為:方令孺、巴金、王辛笛、王理成、王叔磐、毛一波、伍蠡甫、任鈞、臺靜農、朱洗、朱錦江、沈子善、吳克剛、吳朗西、吳劍嵐、吳先憂、何德鶴、何廼仁、李健吾、李采臣、李蕃、李維時、李炳煥、李青崖、李翼安、金幼云、祝味菊、胡繼繩、胡文淑、周谷城、夏德儀、姚蓬子、梁祖輝、梁惠芳、畢修勺、盛成、孫繩曾、馬秀峰、馬松亭、馬受百、馬心田、馬樹禮、索非、常子萱、常子春、莫仲義、陳達夫、陳宅孚、陳白塵、陳望道、陳子展、陳仲誼、陳恩鳳、陳西禾、賈開基、曹亨聞、康嗣群、路順奎、梅林、章益、楊啟森、楊子輝、郭泰嘏、賀昌群、張明養、張履謙、張孟聞、張定夫、費鴻年、靳以、趙清閣、趙家璧、閣湘帆、蔣學模、鄧靜華、黎烈文、漆琪生、潘震亞、鮑正鵠、蕭乾、華林、衛惠林。
③載昆明《觀察報·伊斯蘭通訊》“宗融先生紀念專號”,1949年5月13日。
④載《重慶新民報日刊·新民附頁》第365期,1949年6月12日。
⑤1949年6月12日重慶《新民報日刊·新民附頁》第365期發表李濟生《悼念馬宗融》一文,文末署“一九四九,五,十二,于重慶。”
[1]懷念[M].開明書店,1947年8月,《巴金全集》第13卷[M].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2]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J].《新蜀報·蜀道》第530期,1941-11-9.
[3]《新民報晚刊》,重慶.1942-06-23.
[4]懷念馬宗融大哥[N].香港《大公報·大公園》,香港,1982年2月11-13日;《巴金全集》第16卷[M].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5]心字[M].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11月;《巴金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2016-07-27
李存光,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