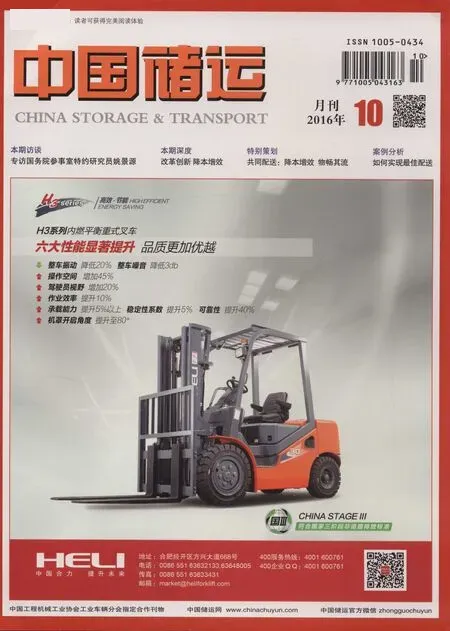凱恩斯主義仍是靈丹妙藥?
文/李煒光
凱恩斯主義仍是靈丹妙藥?
文/李煒光
G20峰會發布的公報稱,各國的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同時指出,僅靠貨幣政策是不能實現平衡增長的,還應強調財政戰略對于促進實現共同增長目標的同等重要性。公報的原文是這樣的:“在強調結構性改革發揮關鍵作用的同時,我們還強調財政戰略對于促進實現共同增長目標同樣重要”;“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我們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這一表述體現了20國集團的“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和關于財政政策的作用目標問題所達成的共識。
自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之后,各國央行普遍使用寬松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但效果并不理想。歐洲、日本在超常規的貨幣寬松和負利率下依然難以擺脫通縮陰影,并導致本幣競爭性貶值。G 20峰會認為這種現象說明各國貨幣放水的政策已經弊大于利,需要提升財政政策的正面溢出效應,才有可能拉動經濟增長。這次通過的《二十國集團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列出了促進財政改革的7個指導原則,即通過增長友好型稅收/繳費和支出措施的支持,推動可持續的、全面的社會保障項目;拓寬稅基,并逐步消除低效的稅收支出;確定增長友好型支出的重點,保持生產性公共投資并提高支出效率;提高稅款征收的透明度和效率;改善公共行政管理及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加強財政框架、規則和制度的作用和重點打擊騙稅和逃稅等。
各國政府對財政作用于經濟的政策可謂輕車熟路,老馬識途。2008年,中國實施了4萬億的刺激政策,美國也實施了總額為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與中國不同的是,其政策的重心不是投資,而是減稅,因而效果有限。當然,中國的4萬億用來提振經濟的效應也不過維持了兩年不到,2011年就出現了長周期疲態。美國在2008年10月成立了《緊急經濟穩定法案》,啟動了7000億美元的公共資金,主要用于對金融機構的資本注入等方面。這個政策對于挽救經濟起了明顯作用,并在2009年3月的道瓊斯工業指數出現觸底反彈中得到了證明。從2012年起美國經濟向好的跡象越來越明顯,而且是從實體經濟開始的強勁復蘇。相比之下,同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經濟卻沒有被激勵起來,反而下行趨勢越來越明顯。
美國通過財政政策支撐經濟上的需求面,可以認為是凱恩斯主義的又一次復活。在這之前,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加速期,曾迫使西方各國轉而接受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和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貨幣學派,即基于規則的貨幣政策和貨幣量,讓就業和生產通過市場的自發調節達到均衡。此后一直到本世紀初,經濟領域的主流都是重視市場功能、否定政府財政支出的干預。然后就是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凱恩斯學派再次占了上風。G20峰會的財政政策共識,證明了凱恩斯主義強大的生命力。也許歷史就是這樣,不停地在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自由主義與凱恩斯的干預主義之間搖擺。
中國經濟一直是凱恩斯主義的擁護者,從來沒有接受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但近年來效應已經明顯減弱,其表現就是力求避免量化寬松的政策選擇遇阻,而重拾刺激政策提振經濟的效果卻不明顯。可以預見到的是,中國將興起一股新的凱恩斯主義風潮,其標志是繼續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已有消息稱,G20峰會之后,中國將召開一次“重要的經濟會議”,討論中國的赤字率問題。言外之意,是原來設定的3%赤字率紅線不再適用了,“中國可能接受4%甚至于5%都問題不大”。
問題在于,凱恩斯主義雖能救敝于一時卻也會產生巨大的負效應。強大的政策刺激也會導致經濟結構調整懈怠、公共事業投資低效、“僵尸企業”得以茍活,家庭消費則因稅負的上升而被抑制,等等。李嘉圖的中立命題證明,財政支出的經濟刺激方案最終將是無效的。
雖然簽署了48條協議,但杭州共識并不會馬上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什么實際利益。比如就環境問題簽訂的3個協議,與其說是為了應對全球化危機,還不如說是一個務虛的結果,各國很難根據這個協議確定自己具體的政策。有關貿易或投資的爭議,牽涉到各國復雜的多變貿易關系,也不是一次峰會能夠解決的問題。峰會只是提出了一個框架,這個框架比原來的框架多了幾分新意而已。對我們百姓來說,還是踏下心來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實際一些。

偏方治大病? 梅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