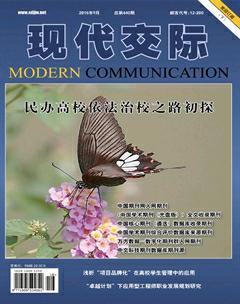公交司機“鳴笛”中的非語言互動
孔繁星
[摘要]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一些特定的社會群體,由于職業性質的原因,他們跟個人系統以外的群體以及個人進行互動的機會較少,相互之間互也缺少必要的交流與溝通。本文以“非語言符號”特寫銅川市公交六路司機——一個特定的群體,在公交六路線上通過“鳴笛”的非語言行為方式進行交流,重新解讀司機的鳴笛互動,以具有代表性的非語言符號來分析這種互動對司機群體的意義與作用。
[關鍵詞]鳴笛 非語言互動 符號 司機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8-0069-02
在狹義的符號互動論的視角下,人類的互動是以使用、解釋、符號以及探知另一個人的行動意義作為媒介的。[1]在以往的研究中都主要研究符號互動或非語言溝通,很少有人注意到符號互動中的非語言互動,尤其是對一些特定人群①的非語言互動研究甚少。細小的非語言行為應該引起人們注意,這些細節揭示了人們之間的關系如何以及如何思考。[2]在生活中有一些特定人群,他們創造了屬于自己領域的新的符號,或者說他們對原有的符號進行了新的定義。公交司機是一個“特定群體”,在銅川市的公交六路線上,就有一群公交司機創造了屬于他們自己的公路語言——“鳴笛”。
一、公交六路司機的“鳴笛”現象
由于公交司機工作的特殊性質,決定了他們在一天里與人交流與外界交流的時間較少,工作強度大,責任重壓力大,所以駕駛任務相當繁重。在所有的公交運輸制度中明確規定了司機不能與乘客攀談,時刻保持警惕。駕駛員也需要社會互動,駕駛員之間更需要交流工作經驗與釋放心中的負面情緒,但是大多數時間他們都是在線路上,面對面的交流時間可以說少之又少,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駕駛員在線路上通過“鳴笛”來相互之間打招呼。
汽車鳴笛在我生活中是常常見到的現象,“鳴笛”聲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它提醒前方的司機讓路或者提醒周圍司機自己的道路變換情況,有時也在警示行人讓路,我們也會看到,如果一個熟人走過,司機也會鳴笛示意。然而,“鳴笛”在公交司機那里變成了一種語言。
(一)鳴笛現象的產生
我們不知道這種現象是從什么時候、何人開始的,也不知道是否全國的公交司機都有這樣“鳴笛”打招呼的習慣。從網上了解到這樣一則新聞:2012年的8月份,在吉林省白山市11路和14路公交車經過某小區時通過鳴笛來打招呼,影響了該小區居民的生活。通過這個事例來看,公交司機用“鳴笛”致意并不是一個偶然事件。這是在司機在日常駕駛中逐漸性成的一種習慣,就像我們見人打招呼說“你好”一樣。而在銅川市乘坐公交六路車時,我們也會發現,過往的公交六路車駕駛員會和本車駕駛員通過按汽車喇叭進行問候。
(二)通過鳴笛來進行非語言交流
如果觀察這種現象就會發現,在車輛來回過往的馬路上留給兩個司機進行問候的時間只有兩三秒種,由于工作性質,他們無法通過手勢、對話和表情進行交談和問候。短短的相遇時的兩三秒鐘或許只夠司機按一下“喇叭”,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允許司機相互打量,甚至看清楚對方是不是熟悉的那張面孔,因為只要足夠熟悉,他們可以通過對方大致的輪廓來辨識身份,他們也可以通過車牌號來獲取對方的信息——每個司機都有一個固定的車牌號,這是每個司機的隱性名片。通過車牌號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我熟悉的同事,我有沒有必要和你“鳴笛問候”。這種鳴笛背后隱藏著一些暗語,因為只有兩三秒的時間,這些暗語必定不會太復雜,也不會太長,而且這是雙向互動,是一來一回、一問一答的過程,所以這種“鳴笛”必然不會包含太多的內容,因為如果足夠熟悉的話,想要知道的其他信息可以通過車牌號來獲取。
(三)鳴笛背后的對話
只要對公交系統有一點簡單了解,就可以猜測鳴笛所表示的暗語,這些“鳴笛”代表的是一種問候,如第一個人的問候是:“xxx,你好!/xxx,下午班?/xxx,早班?/”那么回答人也不必做多余的回答:“xxx你好!/嗯,哦。”不管問的人問什么問題,回答者的回答一定是確定性的,這種鳴笛只代表著一種選項:“是。”試想,在有限的時間內,在有限的問題范圍內,如果鳴笛還帶著一種否定性的答案,那么這樣的互動也是不成立的。如一方問:“xxx,早班?”對方回答:“不是。”這樣的互動已經進行不下去了,問候者也無法繼續提問,回答者也無法補充答案,因為兩輛車早已擦肩而過。所以兩聲“鳴笛”包含了一問一答的所有內容。
但是這種互動并不是在所有駕駛員身上都會發生,這通常是兩個熟悉的駕駛員間的交流。如果兩個司機相互并不熟悉或者曾經發生過一些小摩擦的,那么這種問候的方式就避免了面對面的尷尬,他們大多數時間在線路上不會像辦公室里的職員要面對面地打交道。當然,不排除一些司機把這種“鳴笛”當作一種樂趣,在馬路上除了駕駛并沒有什么其他的活動可以進行,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圍內,遇見一個同事按一下喇叭也可以當作活躍氣氛。通常也會發現一些司機在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中一下喇叭也不會按,對面行駛來的車輛也沒有一個司機對其“鳴笛”示意。我們可以推斷這個司機是性格孤僻,或者不受歡迎,或者是新來的,等等,從這些推斷中我們可以得到關于這個司機在人際交往方面的信息。
二、符號互動論視角下的“鳴笛”交流
我們要得知他人行為的意義以及接下來自己的行動,就必須理解他人通過符號傳達的意義。司機群體創造了一種類似語言的符號——選擇鳴笛的行為來控制自己的活動,通過這種非語言的符號行為和群體內的成員進行互動。
(一)鳴笛是一種特殊的符號
在社會行為發展的早期,某些手勢、姿勢開始被當作特定的行動標志,這些手勢、姿勢漸漸具有了符號的意義,它對于發出者和接受者都是同一個意思。[3]在符號互動中人們彼此理解姿勢,并在理解過程所獲的意義基礎上行動,[4]所以在“鳴笛”這個動作發出前,司機們已經知道了其所代表的全部意義,即使在他們心中所想的問題與答案出現了不一樣的情況,只要他們想交流的內容在這個“鳴笛”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范圍內,他們不用通過言語就可以相互交流。
從社會學理論的角度來看,這種“鳴笛”互動是狹義的符號互動,它包含了符號互動論的三個條件:(1)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互動主體;(2)互動主體之間必須發生某種形式的接觸;(3)參與互動的各方有意識地考慮到行動“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從兩個公交司機的互動過程來看,在特定的駕駛情景中通過車牌所代表的象征意義發生了短距離的接觸,“鳴笛”就是具有意義的符號,并且雙方都知道這種鳴笛所代表的意義,所以這種互動屬于狹義的符號互動。
但是“鳴笛”在司機駕駛過程中是具有有限意義的,它并不包括司機想交流的全部內容,就像握手代表著問候、友好、尊敬、合作的意義,而握手的雙方并不能單從握手這個動作知道對方中午吃了什么。也許在乘客,甚至司機本人看來,“鳴笛”無非就代表著司機間簡單地打招呼,但是“鳴笛”這個動作對司機而言就相當于在我們的日常交流中的符號和語言,以及包含的約定俗成的日常溝通規則。根據布魯默的觀點,事物的意義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解釋的過程中隨時加以修正,[5]在這個特定的情景中,鳴笛所代表的意義也是在變化的。根據情景的不同,每個司機會在既有的幾個問答里面選擇自己認為最佳的或者最合時宜的一個,一旦司機自己確定這就是要交流或者溝通的問答,他就會認為對方也是這么認為的。托馬斯定理告訴我們:“如果人們認定某種情境是真實的,那么這一種情境就具有真實的效果。”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真的相信某種現象存在,根據這一判斷,他就會真的采取某種行動,就會造成某種客觀效果。如,一個司機想要通過鳴笛表達“xxx,下午班”,但另一個司機心中的答案可能是“嗯,你好”,或者認為對方是在打趣的話,這種互動依然成立,因為在有效的信息范圍內,兩個司機心中會以他們各自認定的情景進行交流。
(二)司機的互動方式——個體間的非語言互動
司機在工作時間的互動屬于個體間互動,從社會互動的維度來看,兩個司機的情感關系是親密的,因為工作的性質,他們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利益上的沖突。他們之間的互動是短暫的,利益關聯小,情感投入較少,相互依賴性不強,屬于表層互動,如果雙方之間都相互了解屬于老朋友之間的問候,那么“鳴笛”就屬于深度互動。司機的主要工作是駕駛,這種工作性質限制了他們在車內情景之外的互動,局限于工作領域,然而互動頻度較大。這與一般的互動形式有所不同,也是這種“鳴笛”互動的特別之處。
非言語溝通行為具有普遍性、情景性、民族性、社會性,非言語符號可以用來傳遞信息、交流感情、溝通思想。在特定的場合非言語符號可以起到特定的作用,具有真實代替和強化的作用。[6]在普遍認同的規則下,司機通過“鳴笛”的非言語行為表達心中要表達的意思。很多人認為詞匯和語法比各種表情動作更易于表達,非言語行為在社會互動中起輔助作用,“鳴笛”現象則說明了非語言行為在社會互動中可以單獨發揮表達情感和意圖的作用。
三、非言語互動對司機群體的重要影響
司機是一個特定群體,他們的“鳴笛”行為是非語言行為。他們是在特定的工作情境中,這個工作情景是與其他互動情景不相同的,他們的語言交流的時間是有限的,對他們來說“鳴笛”具有符號意義,從心理上來說更是一種自我關愛。“鳴笛”的非語言行為有三種作用:
(一)增強情感,維持社會關系,代替語言符號
公交司機在車內的工作時間較長,與人交流很少,而“鳴笛”就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雖然這種交流是短暫的。“鳴笛”這種非語言符號代替了語言符號,包含了語言要表達的內容,又滿足了時間和空間的條件,使交流成為可能,維持了原有的同事間的關系。在公交線路上的特定情境中,非語言行為——鳴笛就有特定的意義,它能夠穩定對方的情緒,改善對方不良的心理狀態,增強對方信心,使交流氛圍更和諧,使對方得到關心、體貼,更多一份理解與共鳴,滿足了對方的心理需求,[7]使司機在他們的群體中找到了歸屬感和安全感。
(二)釋放壓力,對外宣泄,心理調適
作為公共服務行業,很多人對自己工作的描述是“微笑至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我們發現在全國各地都有乘客對公交司機打罵的現象發生,也會發現有司機為了一車人的生命安全忍住病痛將公交車停靠在安全的區域內,等等。其實公交司機壓力大,休息時間少,身體負荷大,精神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重壓之下,就有可能出現心理異常,行為偏差,或者可能導致抑郁癥。[8]通過“鳴笛”進行同事之間的打招呼和交流,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駕駛的無聊程度,“鳴笛”對司機來說是一種適當的調節和宣泄,通過互相交流的方式使壓力得以釋放,進行自我心理調適。
(三)避免尷尬,減少摩擦
利益相同的人難免會發生或多或少的矛盾與沖突,即使打照面相對較少的司機也不例外,有時會因為班次而發生摩擦與口角。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選擇自己愿意互動的對象,不認識或關系疏遠的人可以不用打招呼,不用擔心對方因此心生不滿,也不用為此感到尷尬,因為“鳴笛”是一種選擇性的行為,沒有硬性規定,司機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發揮他們的自主性,選擇自己認為適合的時間和對象進行互動。
四、結論
在公交司機這個特定群體中,非語言行為的“鳴笛”對社會互動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幫助司機群體交流情感、維持社會關系、釋放心中的壓力……在其他的特定群體中我們也能見到類似這樣的現象,所以以非語言行為為方式的互動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是社會互動的一個重要的方式,我們必須對其加以重視。
注釋:
①許堯.關于使用特定群體稱謂的建議[N].人權,2015-2.
【參考文獻】
[1][4]侯鈞生.西方社會學理論教程[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徐曉梅.非語言溝通研究的進展[N].浙江社會科學,2002-07.
[3][5]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第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6]李建.淺析非語言在溝通中的重要作用[N].山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09
[7]徐曉梅.非語言溝通研究的進展[N].浙江社會科學,2002-07.
[8]李劍.公交司機付出——獲得不平等與抑郁癥狀關系[N].中國公共衛生,2009-06.
責任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