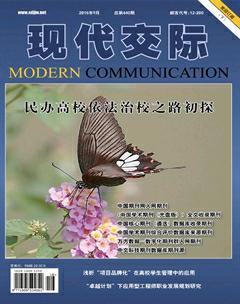集團或個人:中西法律本位的比較研究
郭書影+劉杰
[摘要]法律本位對法律文化的構建至關重要,中國的集團本位法與西方的個人本位法截然相反,卻均是歷史的選擇。二者的比較和辨析可為我國尋找正確的法律出發點,醞釀國家和個人并重的法律本位選擇,提供經驗和思路。
[關鍵詞]法律 集團本位 個人本位 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8-0023-02
法律本位是法律的立足點和側重點。個人與家庭、社會、國家的關系是法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究竟孰重孰輕,中西法律文化作出了截然相反的法律本位選擇。
一、中西法律本位的不同歷史路徑
與現代社會的個人中心主義相反,遠古社會的社會組織表現形式為氏族、氏族聯盟(部族)、或家族、宗族等各種集體組織,組成社會最基本的單元是“個人的集合”而非“個人”。英國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梅因對此有著精湛的考論:“我們在社會的幼年時代中……人們不是被視為一個人而是始終被視為一個特定的團體成員……他的個性為其‘家庭所吞沒了”[1]。可見在人類早期階段,世界法律均處于集團本位時代。雖然出發點相同,但是中西法律本位在演進和轉化過程中卻背道而馳。
(一)中國傳統法律的集團本位
1.“集團本位”與“家族本位”之爭
關于中國法律本位究竟為何學界展開了論戰,張中秋教授將其概括為“集團本位”,但是范忠信博士認為雖然其結論基本能夠成立,但是中國古代社會是依血緣家族的宗法原則建立起來的,家庭為最基本單位,而其他的幫會宗教甚至國家的內部關系也是家庭的翻版。“集團本位”的說法易被人誤解為類似西方平等“個人”的集合,因此“家族本位”概念更為貼切。張中秋教授回應道家族本位的觀點確實比較鮮明,但是“集團本位”更具包容性,能夠體現出中國法律本位的歷史變遷。而且早期西方社會中并不存在平等個人,只是家族和氏族的集合,無須擔心誤解。筆者認為“家族本位”的概念范圍過小,其他學者主張的“國家本位”又無法體現中國古代社會的宗族血緣性,因此采用“集團本位”說法更為合適。民國時期我國內憂外患的國情要求中華民族聯合起來才能抵御外侮、振興中華,雖然當時受到了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影響,法律學界產生了社會本位和個人本位的大論戰,但是社會本位觀點仍毫無懸念地勝出了。
2.中國集團本位法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法律經歷了從氏族(部族)到家族(宗族)再到國家(社會)的集團本位道路,日益集團化。上古時期中國古代法因部族征戰師出以律、兵獄同制的需要應運而生。部族戰爭是不同血緣集團之間的戰爭,中國古代法律“刑起于兵”,因此也具有明顯的氏族(部族)集團主義的特征。夏禹時期,地域劃分原則取代了血緣原則,但是血緣關系仍以家族(宗族)制度的形式保留下來。原始的氏族(部族)法逐漸被注入家族(宗族)的意志。春秋戰國時期,同姓血緣的宗法家族統治土崩瓦解,家國分離。百家爭鳴中,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對“忠”與“孝”作出溝通性解釋,提出新的非血緣性的君父一體制,孟子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將“家”作為國家政治體制的基礎。法家則主張采取單純的國家本位來制定和實施法律,雖然失敗,但是漢代儒法合流之后直至清末,中國法律是家族(宗族)本位和國家本位并存的。對此范忠信博士并不認同,“本位只能有一個……漢以后雖說儒法合流,但以儒為主,不過是吸收了一下法家的‘尊君重國思想……法律的重心仍在家族”[2]。 對此張中秋教授則認為雙本位作為法律精神的支點是可行的,而且家族本位是基礎國家本位是核心,二者并非同層均等,況且傳統中國本是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反應到法律上的雙位一體也不例外,因此不必過于糾纏。
(二)西方個人本位法的形成與發展
1.形成階段:從氏族到個人
雖然從相同的起點出發,西方的法律本位走上了與中國截然不同的道路,經歷了從氏族到個人再到上帝(氏族)最后到個人的歷程。雅典法早期是以氏族本位的習慣法,后經提修斯改革成為雅典民族法。此后又經過德拉古、梭倫和克里斯提尼的變法,實行主權在民,輪番為政,雅典法轉變成以公民個人為支點的公民本位法。與雅典法相同,古羅馬法最初也是氏族法,賽維阿·塔里阿改革后氏族制度被破壞,家和家族地位逐漸提高,《十二銅表法》就是以家為基礎制定的,此后羅馬法一直為家本位法。直到共和國晚期,由于經濟發展和軍事擴張,家本位衰落,個人本位取而代之逐漸形成。雖然雅典式的公民本位和民主政治稀世罕見,羅馬法中的個人本位法律觀極其接近現代西方法律價值觀,但是其囿于父權夫權之中仍是不同于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
2.發展階段:從氏族、上帝到個人
隨著羅馬帝國的衰弱和蠻族入侵,個人本位的羅馬法停止了發展。蠻族推行的是以部族集團為本位的原始習慣法,不但歧視羅馬氏族,對內對也推崇本氏族、家族的利益,個人意志則無關重要,家庭內部則推行父權和夫權統治,無不體現血緣主義的集團精神。但在宗教方面,蠻族接受了羅馬國教天主教,認為神的意志高于人的意志,神法優于制定法或習慣法,歐洲法律出現了巨大倒退。到了中世紀,上帝的意志成為最高標準,神學權威托馬斯·阿奎那極力推崇上帝的偉大和神法的正當性。但是在封建制、文藝復興、商業革命和宗教改革運動等浪潮的沖擊下,羅馬法復興運動將人本主義的法律觀和法律制度重新賦予生命。古典自然法學派猛烈抨擊神權和封建制度,大力提倡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使得資產階級的人權理論在法律中得到廣泛貫徹,西方個人本位法獲得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3.再次確立階段:從社會到個人
19世紀末,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人文主義古典自然法學派本位遭到了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社會連帶主義法學派的抨擊,個人本位和價值被否定。英、美、法等國開始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原則進行限制。反個人本位思潮后來成為了少數壟斷集團和官僚階層推行其專斷意志的理論工具,對兩次世界大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戰后人們開始反思,“希特勒第三帝國垮臺后,價值取向的法律哲學在德國和奧地利得到了迅速的復興”[3],西方各國在立法方面糾正了偏差。至此,經過三次從集團到個人的變遷,西方法律本位被打上了不可磨滅的個人主義烙印。
二、中西法律本位的優劣辨析
“傳統中國的集團本位法實質上是一種血緣性的身法義務法,準確說是一種基于身份的道德責任法”[4],而西方法律則經歷了從身法到契約的過程,形成了以非身份血緣為基礎以權利為中心的個人本位主義。中西法律本位從相同的起點出發卻分道揚鑣,是受政治、經濟、地理、文化等多種要素影響的結果。至此人們不禁要問道,中西法律本位究竟孰優孰劣?集團本位是否應當全盤拋棄?當今中國的法律應當如何選擇出發點才是正確的?是否應當改造為類似西方的個人本位法呢?
(一)集團本位是否應全盤拋棄
由于集團本位法框架下民眾的權利受到了嚴格的限制,甚至被忽略,衍生出了君權、族權、父權和夫權四大繩索束縛民眾權利,壓制人性,還阻礙了中國法律權利和社會結構的發展。法學界對其作出的否定性評價毋容置疑,但我們應當將其置于歷史中去看,集團本位法與中國古代自然經濟的特點、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和中華民族的向心力一拍即合,比較法學家威格摩爾贊嘆道:“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頑強地生存下來,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他們強有力的宗族和家庭組織,在這方面只有猶太人能與比相提并論。”[5]可見其對中華民族的存續和發展功不可沒。而且如今在平衡權利和義務,人和社會、國家的關系時,其中的合理精神又未嘗沒有借鑒意義。
(二)個人本位是否為法律的最終歸宿
從法律哲學視角來看,西方法律個人本位的確立過程是一場解放人性、發展人權的運動,是社會文明的表現。個人本位法中權利在私法體系中占有中心地位。每個人積極實行自己的權利是推動民主政治發展的直接動力,這樣一來又矯正了政治和法律生活中的權力傾向。而其對中國獨特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專業化的獨特視角,為中國法學在上世紀80年代擺脫政治意識形態,促進理論的革新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但是個人本位的弊端在于如果任其發展就會產生有損人類集體價值觀的危險。任何制度和思想發展到極端就會產生危害,西方法律的個人主義應謹慎前行。而且對當下的中國來說,難道法律只有一種出發點去表達嗎?是否必須緊隨西方法律本位才能選擇出適用于中國社會的法律嗎?中國基于本國國情發展出來的法律又是否有被“改造”的意義和可能呢?
三、我國法律本位的選擇
學史以明智,學古以鑒今。探析中西傳統法律本位的優劣之后還應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進行選擇。目前我國外部國際形勢不容樂觀,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而從國內來看,我國正處痛苦的轉型期,必須由強有力的國家政權統一領導才能順利推行下去。此外日益加深的社會變革必然需要國家統籌并施以相配的法律制度加以解決。同時更應注意的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唯有保護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才能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增強民族凝聚力,實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論述到此,中國法律本位的選擇不言而喻,唯有吸收中西傳統法律的經驗和教訓,國家和個人本位并重,才能沿著正確的道路推進我國法律文化建設。
【參考文獻】
[1](英)梅因(著),沈景一(譯).古代法[M].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
[2]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與差異[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3](美)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4]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美)約翰·H.威格摩爾.世界法系概覽(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