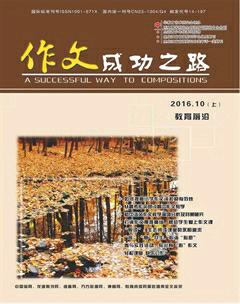淺析福樓拜作品人物無自我的緣由
史佳奇
【摘 要】
本文主要結合心理學上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理論知識,通過聯系小說《包法利夫人》中人物的心理活動等細節刻畫,從主觀和客觀分析為什么愛瑪沒有自我,同時還考慮到小說作者福樓拜自身的特殊性,由此得出愛瑪的無自我是一種必然結果。
【關鍵詞】
包法利夫人 愛瑪 福樓拜 人格理論
一、從主觀理想的破滅分析人物沒有自我的原因
居斯塔夫福樓拜是法國文學史上一位偉大的作家。《包法利夫人》是里程碑式的代表作,歷來受到人們的議論與研究。由此衍生出的一些專有名詞,諸如“包法利主義”“福樓拜問題”等,對于后世學者的研究起到了開創引領的作用。
愛瑪是一個鄉下佃農的女兒,按照正常的人格發展順序,她本應該形成一種普通農村婦女所具有的自我概念。而愛瑪在自我還沒有發展完善的前提下,就去接受和她原有的思想觀念差異巨大的貴族式教育,再加上浪漫主義的美好幻想對她的迷惑吸引,妄圖飛上枝頭變鳳凰,將自我代入到一個不切實際的貴族身份中,導致錯誤超我的提前介入,一旦回到落差巨大的現實生活,必定會在本我和超我的強烈碰撞中走向崩潰。
弗洛伊德認為,“本我是一個人接觸外界以前就存在的內心世界,由先天的本能、基本欲望所組成,只遵循享樂原則。” 在過度追求超我理想的過程中,情愛的欲念使得愛瑪誤以為實現愛情就能實現自我,從她瘋狂地思念賴昂,再到第一次偷情后的心理活動,甚至于后來對羅道爾弗歇斯底里的告白等等,無不反映出愛瑪因為沒有自我,拋棄超我,而逐漸淪為男人的附屬品,本我的欲念讓她從一個少女變成一個蕩婦。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愛瑪在追求超我的過程中不斷受阻,所以便通過滿足本我的需要來麻痹自己,而這又導致她沒有辦法塑造正確的自我,以至于當理想愛情徹底破滅時,“她感到痛苦的,只是她的愛情。”沒有了自我的約束與限制,一味遵從本我的享樂原則,將主體寄托于不切實際的愛情幻影之上,一旦愛情破滅,愛瑪也終將走向毀滅。
二、從客觀物象表現隱喻人物失去自我的內因
小說中通過對一些客觀物象的描寫來反映愛瑪的無自我性的發展過程。先是狗,書中特意寫到有一個獵警送給了包法利夫人一只意大利種小母獵犬,這只狗被賦予了一種短暫的重要意義,成為愛瑪墮落的見證者。“她望著它憂郁的嘴臉,心軟了,于是把它當成自己,好像安慰一個受苦人一樣,大聲同它說話。”這就是那條狗的第一次出現,一段微妙的插敘,愛瑪的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她自己說的,通過對動物的描寫來側面反映出愛瑪內心的混亂與痛苦。狗的第二次出現,也是它的最后一次出現。查理和愛瑪搬到了永鎮寺,這一次旅行標志著愛瑪從幻想向現實墮落的轉變。在旅途中,愛瑪的獵犬跑了,這只狗的離開也許就象征著愛瑪的自我將一去不復返。作者別出心裁的安排布局中,愛瑪失去自我走向毀滅,雖在情理之外,但早在意料之中。
對于愛瑪眼睛的描寫也是容易被人忽視的細節。眼睛作為心靈的窗戶,其實最能反映出一個人內心的波動起伏。愛瑪第一次出場時,書中描寫:“她美在眼睛:由于睫毛緣故,棕顏色仿佛是黑顏色。眼睛朝你望來,毫無顧忌,有一種天真無邪的膽大神情。”在第一次偷情后,她的眼睛也發生了變化:“但是一照鏡子,她驚異起來了。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眼睛這樣大,這樣黑,這樣深。”書中多次提到愛瑪的眼睛,幾乎每一次都有所差異,且不論這是作者有意為之還是無心之舉,表面上看到的似乎只是愛瑪的眼睛,從少女時期的清澈澄明到變成人婦后的烏黑深沉,實質上眼睛失去的只是原有的美麗光澤,而愛瑪失去的卻是自我。
三、從福樓拜的創作理念理解人物沒有自我的初衷
為什么福樓拜一定要把愛瑪塑造成一種沒有自我的形象呢?這其實和福樓拜本身自我概念的模糊以及他寫作方式的特點有關。在《福樓拜的鸚鵡》一書中,朱利安對福樓拜給出了一個有趣的定義:“克魯瓦塞的隱士、第一個現代小說家、現實主義之父、浪漫主義的屠夫、連接巴爾扎克至喬伊斯的浮橋、普魯斯特的先驅、在自己洞穴中的熊……”難以想象一個人竟然會有這么多種身份,而福樓拜也經常幻想不同的主觀自我。“薩特說福樓拜身上具有完整的非現實成分,自愿使他的自我成為想象物,這映射在故事文本中的人物身上,導致愛瑪自我存在的缺失和對自我本身的客體欲望的迷戀。”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福樓拜筆下的愛瑪為什么沒有自我了。
小說最后寫道:“她的生活仿佛一具被解剖的尸體,連最秘密的角落也露到外面,盡這三個人上上下下飽看。”每一個讀者又何嘗不是這三個人中的一個呢?我們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愛瑪這樣一個女性角色完完全全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她的生活,她的情感,她的性格,她的一切,我們都一覽無余。這句話讓我想起了書中的一幅插畫:福樓拜在解剖包法利夫人。他就是要將愛瑪完全徹底地剖析給每一個人看,因為當一個人被描寫到極致時,其實就演變成一種虛無的存在。你總能在他身上找到一處和你相似的地方,他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形象,而是代表了蕓蕓眾生的一種存在狀態。
福樓拜的創作理念就是非人格化的,他明確提出:“我的原則是藝術家的主體絕對不能是他自己。”在這種絕對客觀中立的敘述風格的影響下,愛瑪這一形象是否擁有自我對福樓拜而言無足輕重,他只是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社會的一個浪漫主義者的自我毀滅過程。從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中我們可以領悟到,愛瑪自我形象的虛無性正是體現了福樓拜對浪漫主義的批判,在他看來,脫離現實的浪漫主義追求終會把人引向毀滅與死亡。“愛瑪,就是我!”這句話也許就是福樓拜創作初衷的最好印證。
【參考文獻】
【1】張傳開,章忠民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述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
【2】葉浩生編.西方心理學的歷史與體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3】[法]福樓拜著,李健吾譯.包法利夫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4】[英]朱利安.巴恩斯著,湯永寬譯.福樓拜的鸚鵡.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5】柴鮮.論愛瑪自我之存在.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6】 Francis Steegmuller, ed.The Letter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