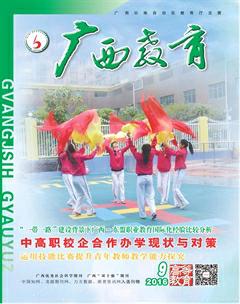簡析馮玉祥的“丘八詩”
高珊
【摘 要】馮玉祥的“丘八詩”,大多反映軍隊生活、抒發軍人情感,在抗戰詩壇上產生過較強烈的反響。從內容上看,馮玉祥的“丘八詩”鼓舞了我方民眾的抗戰士氣;從藝術風格上看,“丘八詩”吸取了民間舊形式的特點,力求通俗化、大眾化,利于傳播。
【關鍵詞】馮玉祥 丘八詩 抗戰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6)09C-0124-02
取得過赫赫戰功的名將馮玉祥,非常重視讀書和寫作,曾寫過很多通俗白話詩,他稱其是“丘八詩”,周恩來曾贊譽此詩體:“丘八詩體為先生所倡,興會所至,嬉笑怒罵,都成文章。”“丘八”是“兵”字的拆解,說明馮玉祥的詩歌創作大多反映軍隊生活、抒發軍人情感。“七七”事變后,他力主抗戰,雖肩負繁重的軍事政務,還是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支援抗戰的宣傳工作中去,很多鼓舞抗戰的歌謠就此出爐了。
一、“丘八詩”的內容
從內容上看,馮玉祥的“丘八詩”包含了以下四個方面:
(一)記敘將士在對敵斗爭中智勇雙全的表現,歌頌他們不畏犧牲的堅定信念
朱自清認為:“一般詩作者描寫抗戰,大都從側面著筆。”即用民眾的敘述視角來表現我軍的英勇,而作為一名親身經歷了無數次血與火的洗禮的軍人,馮玉祥對前線上戰士們所經受的殘酷考驗和他們的堅強意志都有著切身感觸,當他在歌謠里稱贊著這些將士們的時候,一方面是為了激發更多人對英雄的敬佩,從而親身投入到戰爭中去,另一方面也是作為一個高層將領,表現出對自己部下的盡職盡責的表彰。
例如《張慶余將軍》一詩:“我們不怕死不怕傷,/唯有拼命才能打勝仗。/我們是死里求生,/我們是向強盜抵抗。/勝一次固然光榮,/敗一次亦絕不沮喪。/我們抱定了犧牲決心,/直打到敵人投降。”(《攻克敵旅司令部》)將士們秉持著為正義、為國家而戰的強大自信和自豪感,愿以個體生命換取勝利的悲壯和豪邁讓人震撼。戰爭吞噬著無數的生命,可一些抗日英雄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日本如不早悔改,/一千一千把命斃!/六千萬人拼我四萬萬五千萬,/各死六千萬人看誰完!”詩中對日軍的詛咒夾雜著激憤的情緒,甚至是以龐大的生命數量為沉重的砝碼,來增強對于取勝的自信。
(二)揭露、斥責侵華日軍的種種劣跡、暴行,贊頌社會各階層民眾多種多樣的抗戰義舉,從而喚起大家共同抵御外敵的民族自尊心
“寇軍到南京,/殺我五萬人。/血腥聞數里,/尸體如山橫。/邪惡竟至此,/舉世皆震憤。/我們牢記仇,/我們牢記恨。/若不將寇除,/禽獸亦不如!”(《五萬人》)如此震懾人心的慘況,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會感覺到深刻的恥辱和憤怒,詩人記錄了事實,繼而發出激昂有力鼓舞,號召民眾將滿腔的怒火轉化為一致抗日的堅定決心和豪情。馮玉祥在詩里一次次發出這樣的呼喚:“同胞啊!/快起來啊!/我們若不報血仇,/簡直不如狗和豬!”(《蚌埠》)
《檢查》里,當兩個中國女子在候車室被日兵輕薄和侮辱時,難民們憤怒了:“女人遭受此侮辱,/同胞見者起公憤。/一聲怒吼如雷響,/齊同倭奴把命拼!”下層勞動人民面對侵略者,毫不畏懼,一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也同樣如此,如《山西二紳士》中的兩人“甘愿餓死以成仁,/不肯對敵把頭低”。在馮玉祥的筆下,抗戰不分性別,平時只操持“小家”的女性也能成為抗戰大軍中的一員,她們或在戰場上殺敵:“發槍射擊不容情,/打死一個傷兩個,/勇武堪稱女英雄。”(《女軍人》)或在后方慰問和照料傷兵,像《周夫人》中投身醫院作看護的周夫人,無微不至地照料將士們的生活,被馮玉祥稱頌為南丁格爾式的偉大女性。而向來被視為弱者的兒童,也為抗戰做了許多工作。抗戰時期有一個著名的孩子劇團,經常在廣播電臺或者收容所進行宣傳,十分優秀。馮玉祥在《孩子團》里夸贊了這些苦難的孩子們無懼艱苦、“抗敵救國不示弱”、“各地同胞都歡迎”的杰出表現。
馮詩給我們展現了一幅幅感人的民眾抗日圖:在生死榮辱的選擇面前,在民族危難之時,各階層民眾都抱定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決心。
(三)揭示日本軍隊內部彌漫的厭戰情緒
馮詩多處指出,侵華戰爭只不過是由少數野心家發動的,而很多日本士兵在背井離鄉、飽嘗侵略的惡果同時,越來越厭戰。“日本兵,來打仗,/最堪痛苦是受傷。”(《日本傷兵》)那些負傷的日兵遭受了日本軍隊的頭目們種種諸如槍殺、火葬之類慘無人道的處理,馮玉祥在同情和呼吁他們應該奮起反抗的同時,也在喚起我方軍民的信心:日軍不但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對待自己的將士也冷酷無情,這樣的“不義之師”終會覆滅。很多日兵都對戰爭的目的和后果疑慮重重,對前途感到無比迷惘,詩里借用一個日本旅長的口吻:“有一個旅團長親口承認,/他已經心驚膽寒:/弟兄都問為什么對中國打仗?/打完了又怎么辦?”(《敵兵反戰》)馮玉祥清醒地認識到,不是每個日本人都是天生殘暴的侵略者,實際上當時很多日本士兵都有對于戰爭的悲觀、厭戰心理。當然,他寫這些詩歌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給中國軍隊和民眾樹立心理優勢:日本的軍隊實際上軍心渙散,并不可怕。
(四)痛斥和批判一些漢奸的丑惡嘴臉
馮玉祥還以銳利的筆鋒為投槍,擊中了一些在抗戰中遭人唾罵的漢奸。《菜花黃》刻畫了汪精衛投敵前的陰險言行和投敵后的漢奸奴顏,預言了他最后一定不得善終。《姓殷的》從題目就看出馮玉祥對殷汝耕其人的不屑,嘲笑他“當初原圖富貴久,/到頭燕菜吃幾口?/賣國賊名留萬世,/人人笑罵下流狗!”勸這個“傀儡”悔改:“我盼懸崖早勒馬,/洗心革面仍英雄。”
可以說,馮詩抒發的絕不僅僅是詩人個人的情感,更是當時民眾普遍的情感。在嚴峻的現實面前,詩歌里沒有表現出任何悲觀和失望,就算是自己的愛將與親人犧牲,詩人也沒有表露出個人煩惱和哀愁,而是化悲憤為精神力量,鼓舞著每一個不愿做亡國奴的人為這場神圣的民族戰爭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二、“丘八詩”的風格
馮玉祥的抗戰詩歌在藝術上吸取了民間舊形式的特點,力求通俗化、大眾化,利于傳播,其風格概括如下:
(一)語言風格通俗易懂,大量明白曉暢的口語入詩,有新聞文體的特征
馮詩的口語化傾向非常明顯,在戰時,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傳播作用。當然,從詩歌的角度看,一些完全沒經過修飾、與日常語言沒有區別的詩句的審美意味就略顯平淡淺薄,如“到去年九月底為止,/一共逮捕了四五千民眾;/十二月間,/又抓了四百多名,/另外二百多作家,/都被判處了重刑,/許多有價值的書報,/一一嚴加查封。”(《抓反戰者》)這樣的詩句,如果不是因為分行,等同于新聞,沒有什么詩意,也沒有多少審美效果和想象空間。為了急于反映某個事件或者描述某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場景,以犧牲詩的審美效果為代價,這種急功近利的行為在當時的很多歌謠中都存在。馮詩中類似新聞文體的詩句還有很多,如:“事后詳細調查,/我們五百三十二人被殺掉。/可是假如大眾不起來抵抗,/三千五千也是難保!”(《大殺敵人》)詩里用類似新聞體般準確、冷靜、客觀的方式進行“報道”,雖看似未抒情,可令人震撼的數字浴血而出,驚心動魄,很難不讓讀者“動容”。
(二)運用“賦、比、興”等表現方式
大部分抗戰“丘八詩”的結構都是鋪陳敘事+抒情(或議論),從篇幅上看,似乎更加偏重于敘事,但實際上是為了因事生議、緣事抒情。詩歌的敘述應該說是非常生動的,特別是描寫作者熟悉的戰斗場面時,對于戰況的前因后果、戰士心理的微妙變化、戰斗場面的緊張刺激,都繪聲繪色,頗為跌宕起伏。不管是描述軍民如何英勇抗日的場面,還是反映日軍內部的動搖和懷疑,在將事情描述過后,馮玉祥都會歸結出極為類似的論點:所有民眾都應該覺醒起來、團結抗日,而且我們一定會取得最終勝利,如“新年已來,/最后勝利穩在我手!”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打蜈蚣》一詩中,以毒蟲蜈蚣的性狀與兇殘的日本侵略者作比,并嘲笑了二者最后都會被消滅的結局:“一足踏中。/頭已粉碎,/身尚搖動,/一分鐘后,/死骸寂靜。/為何踏死?/惡毒逞兇。/日本軍閥,/與此正同”。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馮玉祥在四川坐車時看見菜花正開,又黃又香,就提筆寫了一首揭露汪精衛丑惡面目的《菜花黃》,開頭先寫“時當二九天,蜀道菜花黃;/燦爛真悅目,風來陣陣香;/此花有傲骨,膽敢戰風霜”,抒發了詩人對于祖國河山的熱愛和對菜花黃的傲骨的贊美,并以菜花黃引發聯想,將汪精衛的無恥行為與之相比照,最后指出:“嗚呼!汪精衛!不如菜花黃!!”馮玉祥這些應用了比、興的歌謠與其他一些口號式的詩相比較,有比較鮮明的形象性,詩人的情感不再完全借由喉嚨吼出,而能夠較為婉轉含蓄地通過恰當的意象來傳遞。
(三)十分注重韻律和節奏
歌謠的流傳必定會對其音律有的嚴格的要求,朗朗上口的句子才利于傳播。馮詩的韻押得比較頻密,基本上每首都有韻,配合這些歌謠風格的激越和豪邁的氣勢,韻腳多押響亮的“江陽”韻或者“中東”韻,例如“日本兵,來打仗,/最堪痛苦是受傷。/受了重傷無處運,/挨苦等死口直嚷……”這首詩就有“仗”、“傷”、“嚷”、“喪”、“葬”、“亡”、“腸”、“抗”、“當”等字押韻。而《打蜈蚣》一詩中的“毒蟲蜈蚣,/頭部亮紅……凡我同胞,/痛須思痛……”就有“蚣”、“紅”、“縫”、“風”、“中”、“動”、“兇”、“同”、“眾”、“痛”、“蟲”等押韻,基本上是隔行押韻。在語音上,還使用了一些擬聲詞來突出語言的直觀性、形象性、生動性,如“飛機嗡嗡嗡!/炸彈轟轟轟!”之類的語句經常出現,不僅形象地模擬了音效,也極好地烘托出了緊張的氛圍,營造了緊迫的戰斗局勢。
【參考文獻】
[1]馮玉祥詩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朱自清.新詩雜話[M].北京:三聯書店,1984
【作者簡介】高 珊(1980— ),女,廣西桂林人,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基礎寫作和現當代文學。
(責編 劉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