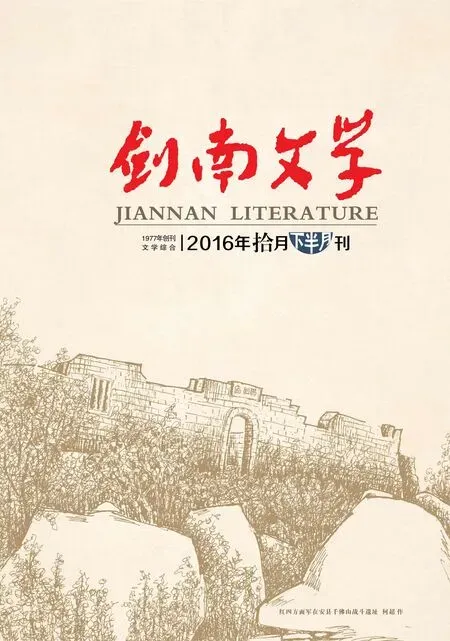張愛玲與曹雪芹的女性書寫比較分析
□陳壽琴
張愛玲與曹雪芹的女性書寫比較分析
□陳壽琴
引言:本文就張愛玲和曹雪芹小說中的年輕女性形象進行比較分析。從藝術旨趣、文化景觀、審美情感等角度來分析兩位作家筆下的女性人生悲劇,以及女性書寫的特點,并進而探求他們審美意趣的差異在于張愛玲的有人性深度的“俗”味與曹雪芹的有人生高度的“雅”美。
張愛玲和曹雪芹的小說都聚焦那些輾轉于家庭或家國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生存圖景之中的女性。兩位作家以生花妙筆描畫出不同時代的“仕女圖”。在他們描繪的圖卷中透出一種“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的悲劇意蘊,令無數讀者黯然神傷、唏噓不已。毋庸諱言,在悲劇女性的書寫上,張愛玲的小說深受《紅樓夢》的影響。但是兩位各稟才情的作家在女性書寫上又呈現出不同的藝術旨趣、文化景觀和審美情感。本文擬就對兩位作家筆下的年輕女性形象進行比較分析。
張愛玲和曹雪芹的小說都善于運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對女性人物進行真切地描寫。不過,兩位作家在藝術旨趣上似乎又體現出不同的追求:一位直面殘酷的現實,以冷峻的筆墨勾勒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化夾縫中的“新閨閣”里的悲劇女性形象;一位營構理想的境界,以超凡脫俗的筆觸勾畫出眾多才貌兼備的古典悲情女性形象。
一、世俗的庸常
張愛玲筆下的悲劇女性形象最具特色的是新舊時代交替中的沒落淑女。根據其現實處境來看,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比較舊式的川嫦、長安們。她們生在敗落的封建大家庭,現代的自由、平等思想對她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到底還是撼不動中國數千年來形成的倫常文化,所以就其生活底子來說,依然還是舊的暗淡的。《花凋》中的鄭家已經徹底走向敗落,但是鄭家的女兒不能出去做工掙錢,那是丟不起面子的。所幸鄭家的女兒個個貌美,于是她們就有了成為女“結婚員”的資本。溫柔的鄭川嫦在“媒妁之言”的婚約里,對未婚夫產生了一種愛意。然而,正沐浴在“愛情”陽光中或婚姻的展望中時,她卻被肺病糾纏。她的肺病不像林黛玉的肺病那樣具有一種特別的詩意,反而成為她悲劇命運的現實緣由,因為它讓勢利的親人厭棄,使講究傳宗接代實用目的的戀人“移情別戀”。她的生存處境岌岌可危,無助的她愛又不得,生又不能,只能孤獨地死去。她的死沒有悲壯,只有無盡的悲哀,因為她始終都沒有抗爭過。因為她所受的家庭教育使她不可能“抗爭”。川嫦的悲劇人生在于親情的冷漠,愛情的幻滅,肉體的死亡。她的死何嘗又不是一種解脫呢?在此,張愛玲的筆墨正視人生的虛無和人性的自私。《金鎖記》中溫順的長安寂寥地活在家長的陰影下。她雖然進過洋學堂,但是始終都沒有想過要掙脫舊式倫常的束縛,任由青春變得灰暗無光。本來她與留過洋的童世舫相互喜歡,因為“變態”母親的干涉和莫須有的猜疑而葬送了愛的權利和享受平凡婚姻幸福的可能,早就斷了結婚的念頭,只能陪著衰老的母親枯萎下去。她不用擔心生存問題,可是謀愛無望,婚姻無著。她覺得她的犧牲是一個美麗、蒼涼的手勢。顯然,母愛異化和封建家長制導致了長安的悲劇人生。
另一類是比較新式的白流蘇、葛薇龍們。《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曾經如娜拉般勇敢地逃離了夫家,回到娘家。當娘家人把她的錢用光了,就打著“三綱五常”的旗幟勸她又回夫家去為剛死的前夫守寡。她為了擺脫在娘家尷尬的處境,為了生存,放下自尊和體面不得不選擇做范柳原的情婦。所幸,在香港淪陷的特殊戰爭情景下,她用尊嚴和身體換來了生存的保證,得到了她想要的婚姻和名分。叛逃此一夫家的流蘇,又回到了彼一夫家。流蘇對柳原是有愛情的,但是謀生的迫切性壓抑了謀愛的詩意性。因為流蘇謀生與謀愛是一致的,所以,就少了因愛與生存的錯位所造成的撕裂般的痛苦。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在謀生與謀愛的嚴重錯位中痛楚周旋。薇龍是封建家庭中的女兒,因為家道不濟,有主見的她主動接受了姑媽梁太太的“物質幫助”。她父母回上海了,她留在香港繼續求學,從而脫離了封建家庭的約束。而后她被姑媽培養成香港華人交際圈中的新秀,從此她就逐漸陷入了物欲的泥沼里。后來她愛上了漂亮的混血兒喬琪喬,又陷入了愛情和婚姻的黑洞里。為了滿足姑媽的淫欲和喬琪喬的金錢欲,她自愿混跡香港社交圈,成為為姑媽弄人和為丈夫弄錢的工具。葛薇龍明白她自己想要什么,而且知道自己的艱難處境,就是難以超脫現實物欲與情欲。如果她是艷麗的,那也是一種俗艷,交際花式的功利性艷麗。她的職業就是以美好的身體取悅中上層社會的男人,在經濟上依附于眾多男人,而不是唯一男性——丈夫。這里,傳統家庭倫理和道德被現代欲望消解了。在她的婚姻中,她愛丈夫而丈夫不愛她,丈夫愛的是錢,因為錢可以買來各種感官享樂。現代都市社會,婚姻成為愛與物質的交換,她不是為了謀生而結婚,是為了謀愛;可是謀愛不得,婚姻給人一種不可靠的虛無感覺。婚姻成了飲食男女實現欲求的一種載體,而少了現世安穩的那份篤定。
由上觀之,張愛玲筆下的這些悲劇女性既要承受封建大家庭衰敗的生存壓力,又在依稀存在的愛情糾葛與人倫桎梏中承受日常生活的壓抑。新舊轉換的社會里,這些敗落舊家庭中的年輕女性幾乎沒有求生或追求愛情的本領和勇氣,所以她們大多首先以求取婚姻來謀求生存或愛情。這就可能導致愛情與婚姻的錯位或愛情從婚姻中的滑落,于是婚姻變成了一種理性的實用性的選擇,缺少了自由感情的審美性。張愛玲借這些女性人物悲劇性的荒謬處境反觀了人情的冷漠和人性的變異。
二、優雅的超逸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畫了各具風采的女性群像,簡直就是一副中國古典仕女的“清明上河圖”。曹雪芹筆下的女性人物大都才貌雙全。以林黛玉、薛寶釵、妙玉、史湘云、“賈府四春”等為代表的女性人物無不是才華橫溢,美艷如花,都是兼具外美與內美的古典“美女”典型代表。不過,這些悲情女子宿命般地演繹著其優美傷感的故事,真應了那句“紅顏薄命”的讖言。
頗有詩人氣質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傷春悲秋,又孤高標世,風流裊娜,目無下塵,自有一種閬苑仙葩的脫俗氣韻。她對純潔、真摯愛情的全身心投入最令人動容。姑且不論神瑛與絳珠仙草的凄美神話對這位“世外仙姝”宿命般的影響,單就她為愛情淚干、嘔血而逝來論,黛玉的塑造最具詩意;因為她為情而生,為情而死,她是人間至情至愛的化身。她始終保持了靈魂的高貴和情感的自由,所以能超逸出世俗的牽絆。正如有論者所說,林黛玉“以感傷為人生主調。她摒棄了世俗生活追求,把生命純然升華為審美化的情感追求。[1]”作為封建時代的女性,黛玉的愛好不在女紅,而在讀書作詩。她讀寫是無功利性的,是一種純粹的精神追求。細讀她的那些纏綿悱惻的詩,可以見出一種超然與高潔的精神品質。盡管她活在世俗之中,卻又超然于外。這位大觀園才女的才情心性積淀著中華民族文化心理,寄寓著封建時代理想化文人雅士的高標風范和人生形態,即保持生活的“入世”情懷,追求精神“出世”的自由。
博學的薛寶釵艷壓群芳,艷麗嫵媚,嫻靜華貴,別有一種端莊典雅的韻致。雖然“金玉良緣”在世俗中取代了“木石前盟”,然而這朵嬌艷“牡丹”在得到了寶二奶奶的頭銜時,卻在婚姻中失去了愛情。薛寶釵的悲劇人生和葛薇龍的悲劇人生很相似,為愛而謀取婚姻,可是丈夫的愛卻在婚姻中缺席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葛薇龍就是現代版的薛寶釵。妙玉氣質美如蘭,才情出眾,富有靈氣,多情曼妙,另有一種高潔雅致的風度;她以“出家人”的身份小心翼翼地愛著賈寶玉,卻無法得到寶玉的完整的真心,而且在后來還遭難陷泥淖。實際上,黛玉、寶釵和妙玉都可歸為謀愛而不得的悲情女性。相對而言,史湘云任性自然,活潑灑脫,真實率真,具有一種自然瀟灑的美質;但是她的命運依然不在她自己的掌握之中。賈探春不僅頗有才華,“文采斐然”,善長下棋和書法;而且志向高遠,熱情大方,膽識過人,霸氣凌然,令人“見之忘俗”,理家的能力緊趕璉二奶奶王熙鳳,最終卻遠嫁他鄉。賈惜春畫畫得好,雖逃過家難,卻只能青燈古佛,孤獨終老。其他女性人物幾乎沒有什么好的結局,賈元春榮寵等身,最后還不是富年“薨逝”;隱忍的賈迎春、秦可卿等都是如花年紀就凋零了。她們個個都飽讀詩書,詩詞歌賦酬答,琴棋書畫俱佳。好一道絕美的風景線,這風景中有的是風姿卓絕的閨秀,舞文弄墨的佳人。可是,這些佳人逃不出“華美閨閣”的魔咒,她們的青春與愛情、才情與詩意、志趣與追求被埋沒于與世人隔絕的“理想世界”之大觀園,不為外人道,也不為外人知。這也是封建倫常文化或男權文化對女性最深重也“最自然”的鉗制與限定。
這些真情、率性、充滿活力的、富有才氣的美麗閨秀們溫文爾雅,矜持含蓄,生活情趣高雅,具有封建淑女特有的美德和優雅。她們不為考取功名利祿而讀寫,只為生命的快樂和精神追求而彈琴下棋,吟詩作畫。她們在大觀園的生活,充滿詩意,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棲居”。然而在現實中,家族的興衰直接影響到這些貴族女性的命運。賈家的衰敗使這些理想化的女性最后都走向悲劇人生的境地。曹雪芹又用超逸的筆為這些跌落現實的悲劇女性構筑了想象中的太虛幻境,將愛情、理想、生命交付給浮世外的虛幻之境。而曹雪芹的高超之筆還在借跛足道人的《好了歌》表現“萬般皆空”的人生感慨,他想向世俗之人揭示“人生無常”的這一超越性智慧。于此,她的女性書寫達到了一種超拔的人生境界。
比較而言,張愛玲的小說具有世俗的人間煙火味,所以她筆下的女性人物都活在居家過日子的日常生活中,活在庸常中。就如楊義先生所說,張愛玲在“中西境界相錯綜之處,變幻出一幅幅充滿蒼涼與不安的洋場仕女圖。”而曹雪芹飽蘸詩意情趣,為這些生在溫柔富貴鄉的才情卓著的仕宦閨秀們畫像,畫出了一幅幅優雅的深閨仕女圖;最后又將美麗毀掉,讓其在無望的愛情中死去或在措不及防的家族敗落之際承受滅頂之災。作者為他鐘愛的青春女性繪出了凄美的圖卷,目的何在?王國維認為,《紅樓夢》的精神告訴人們如何擺脫欲望、在俗世間得以解脫。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女性書寫的審美趣味上,張愛玲的有人性深度的“俗”味與曹雪芹的有人生高度的“雅”美構成了不同的女性書寫圖景。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似乎始終都有一種難以超脫的世俗之氣,她們耽誤于世俗化的生活內容和生活情趣,在人情的庸常中打轉,缺乏曹雪芹筆下那些才情女子的高雅志趣和精神追求。也許,她這樣寫似乎更真實,更貼切生活本身。她寫新舊文化更替時期的洋場淑女,將其置于“謀愛與無愛的困局中,用愛情與婚姻永遠的錯位來揭示女性生存的無奈與存在的荒誕。”也寫出飲食男女的生之欲求與現世安穩的追求。張愛玲世俗女性書寫的深刻在于,其在人生的無聊與庸常中發現了人生的虛無,揭示了人性的自私與虛偽。而且鋪寫出一種蒼涼、頹廢之美。再者,她營構的頹敗王國中的女性都有一種永恒性:“將來的荒原下,斷瓦頹垣里,只有蹦蹦戲花旦這樣的女人,她能夠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年代,任何社會,到處是她的家”。所以,在她《自己的文章》中說,“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意味”,能給人回味和啟示,也能展現美、人性。
而在曹雪芹的詩意“女兒國”則充溢著古代淑女的仙氣、才氣,充滿著美好的青春,純潔的愛情,率真的性情。文采精華,雅趣橫生,保持靈魂的雅潔和超逸。他還用神話與現實的二元對照來塑造人物,并以“情”為中心,在一種審美的人生境界中來刻畫理想化的古典美女。可是美終究被毀滅:現實故事以悲劇收束,從而揭示家族衰敗的現實利益、倫理規范等對女性的重重捆綁,進而展示人生的變幻莫測。臨了,他又以感傷的筆給眾女兒以新的歸宿,即太虛幻境,為情與美的幻滅譜寫一曲哀婉動人的挽歌。用周汝昌先生的話來說,曹雪芹“以詩心察物,以詩筆畫人,以詩境傳神,以詩情寫照”。由此可見,曹雪芹的女性書寫,境界高妙迷人,充盈著中國獨特的空靈飄渺的韻致與美感。
張愛玲與曹雪芹都擅長在特定的文化時空中表現悲情女性,并揭示出在婚戀、家庭(家族)和人生追求中的女性文化心理。其文化景觀迥異:一個揭示日漸式微的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的相互纏繞,一個展現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雅致與局限。其審美情感不同:一個“以深切的理解對女性的異化給予慈悲的同情”,一個“為女性青春之美的毀滅而慟傷”。其藝術思維取向上也存在差異:一個側重揭示傳統與現代文化沖突下謀愛與謀生的錯位和人性的脆弱、黯淡,一個側重展示封建倫理文化重壓下情的幻滅和美的毀滅,探詢人生虛幻的“色空”觀念和形而上的精神超越。
(重慶師范大學涉外商貿學院)
重慶師范大學涉外商貿學院人文社科項目“中國古典小說與現當代小說比較研究”(KY2015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