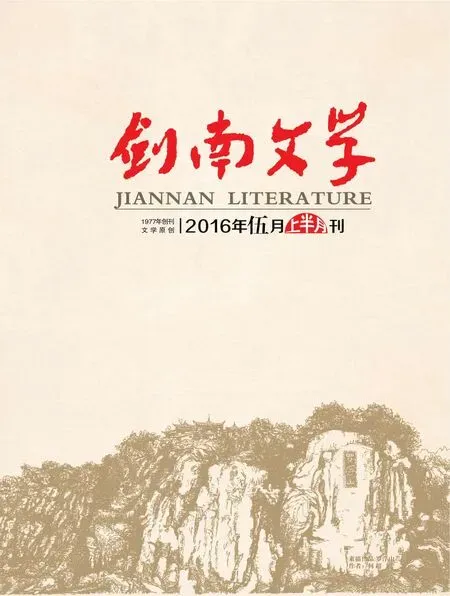日落大麥地
□楊天林
?
日落大麥地
□楊天林
1
大麥地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由太古界的混合巖和花崗巖所構成的緩慢延展的山體變化而成的宇宙景觀,也不是地質歷史上著名的加里東運動沉積的灰綠色巖層展示出來的厚重與深刻,而是刻鑿在大地之脊的巖畫。
這就是大麥地巖畫。它們一般是舊石器時代末新石器時代初人類原始思維出神入化的作品。集中體現了狩獵和游牧兩種存在方式和經濟形態。
可以肯定的是,遠古時代的大麥地,是一個草木茂盛、生態環境良好、食物鏈相對完整的地方。在大麥地,我想起了大地灣文化和仰韶彩陶文化,它們或許有一種相互的影響和滲透。在大的時空范圍內,它們不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作品,而是多個民族在上萬年的時間形成的歷史,它始終凝聚著自己獨特的視角。
我似乎看到了巖畫的創作者。他們是古代社會創造偉大文化工程的無名氏,他們是遠古歲月中自身歷史的直接經歷和記錄者。他們在美麗的創造中訴說著生存的艱辛。
日積月累的結果是,歷史不斷以新的面貌出現。雖然他們知道,生命是短暫的,但他們也許更清楚,他們的作品有可能永存下去。
在大麥地,巖畫傲然而立,引人注目。他們創作的動物形象沉睡在遠山腳下,他們用雕琢巖石的技術和手段,使失去時間的印記顯示了一個方向。也使自然環境的艱辛有了可靠的記錄。
2
就在他們用巖畫向時間和自然挑戰之際,他們卻在用形象模仿動物方面顯得有些保留、憂郁、甚至害怕。自然界的動物具有生命本身某些令人畏懼的神秘,他們留存下來的創造顯示了石器時代的人類作為形象制造者,已經具有一種靈感,能夠感受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們也差不多知道,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作為賀蘭山巖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麥地巖畫的存在形式暗示了那個時代人類創造力的勃發,這使得在石頭上作畫成了當時的一門專業和一種技巧,它肯定帶來了舊石器時代末新石器時代初狩獵民族視覺藝術的高度發展。
在他們的作品中,廣泛而且成功地創造出了許多動物的形象,他們就生活在這些動物之中,并以它們為基本的食物資源和生活背景。而在那之前的幾十萬年的悠悠歲月中,人們并沒有意識到宇宙的無限和自然力量的偉大。也不知道創造的重要性。
突然之間,人類開始將刻鑿巖畫變成了自己的一個重要活動,變成了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并將巖畫視為自己心愛的作品。這成為社會進步和繁榮的促進因素。因為在這個時候,人類在很多場合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原型思維、自然崇拜和生存巫術,也有更多的空閑時間在灰色巖石上展現他們的技術和想象了。
他們的美學基調是蒼涼的,他們的審美觀念是程式化的,他們的真實目的是各種動物的形象描繪,在描繪中抒發自己的心靈感應和最初愿望。
3
在試圖重現獵物的過程中,潛藏在他們心底的創造力得到了催生,他們描繪動物形象的能力在巖畫的刻鑿中得到了證明,這種能力對于人類了解自身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飛躍。
在刻鑿中,他們不僅想到了自身的生存受到了那些野獸的威脅,而且通過這些形象的描繪,感到一種來自自然的敬畏力量。
今天看來,巖畫作品仍然生氣勃勃,雖然我們并不完全清楚他們的終極目的,但我們不難從中領悟到一種創造者對空間的超越和對時間的蔑視。以及對于那些近于蒼涼的美學基調的欣賞。他們在巖畫的創作中找到了一種抒發內心體驗的方式,找到了一種留住記憶的最好辦法。
那些簡潔的動物形象不是某個個人愿望的特殊表達,而是集體潛意識的不朽豐碑。伴隨著日常生活的不變節奏,伴隨著日月星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個世紀一個世紀的周期性循環,巖畫也給我們留下了遠古時代人類生活狀況的豐富記錄。
那些狩獵者、游牧者和制陶人走在落日的光影中。他們沿著深山的邊緣走來,又向荒野大漠中走去。他們是過去巖畫的閱覽者,又是未來巖畫的創作者。他們可以不認識字,但卻普遍懂得符號的意義。
4
在遠山的崖壁之間,他們不辭辛勞,用笨拙的工具把心中美好的愿望變成了一種三維的演示。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是把他們的目的設想為將要傳達那些顯示在圖畫中的東西。他們的創作活動很有可能就是象形文字和神話故事有記錄的直接源頭。
不管他們創造巖畫的最初用意如何,其結果總是清晰地刻印在三維背景上的活生生的形象。他們的目的是選擇那些富有特色輪廓清楚的對象,因而可以純粹的線條再現它們。諸如獅子的威猛、大象的憨厚、鴕鳥的可愛、巖羊的柔弱,等等,在他們手里都有極好的表現。
由于他們的創造,藝術顯示了更多的真義。時間隨風而逝,但這些視覺形象卻要永存下去。并逐漸形成了一種品格和一種風格,這就是創作者存在價值的根本所在,這也是他們不曾意識到的。
今天,我們在閱讀這些寫在大地上的作品時,不要忘了,在他們心里,他們的創造有迫切的實用性,巖畫的功能總是伴隨著他們生存的方式。這些依托于巖石的各種符號所要體現的東西將隨著生命運作的一切而存在。
對于他們來說,自然狀況和地理環境已經成為遙遠的背景,刻鑿巖畫使重復循環的生活變得豐富,他們的創作實質上實現了以持久圖像再現自然真實的初衷。從這個角度看,巖畫創作濃縮著生命的體驗。
時間正在成為透射過去的一面鏡子,這主要不是一種心理的映射,而是一種運動的節奏。巖畫的周期性刻鑿,戲劇性地表現了這種節奏。這是一種對生命輪回的準確理解和對宇宙秩序的客觀把握。
5
這也使我更加堅信,巖畫的存在決定了時間和空間不是什么遙遠的東西,他們生存于此的既是一個永恒的世界,也是一個對稱的世界。巖畫對這種靜態生命的表現是最質樸的,也是最直觀的。他們持久的渴望體現在與天地自然、與宇宙永恒秩序的和諧上。
巖畫的刻鑿者很早就創造出自身的嚴格程式,這時,工匠的技藝成為想象力的束縛。他們在創作中使用了大量的點、劃、線,由此所構成的動物原型,在美術史上大概是最持久的。
在這里,傳統的程式化和原型的力量受到了考驗,視覺藝術只顯示了自然主義的短暫印記。風格的延伸是不可避免的。動物圖案由靜態的三維變成了動態的三維,由視覺的造型變成了知覺的造型。但仍然保持了客觀上的習以為常的程式制約。
他們不懂得透視法,但他們的作品組合起來卻能夠展示軀體堅實的程度和立體感。因而很容易產生一種漫畫化的效果。
他們是形象的作家,他們更是思想的作家。時間的遙遠和地域的阻隔并沒有抑制他們的想象力,他們在理性上所缺乏的東西借自然主義的手法得到了補償。
對巖畫的癡迷,不是某個民族,而是整個人類的共同特點。巖畫也是我們走進古代世界的最便捷的通道。今天,這些昔日沉睡在深山老溝里的巖畫正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氣候環境的變化、更隨著人類的肆意干涉破壞而面臨著瀕危的絕境。作為對一種文化資源的珍惜和保留,我們應該積極地采取措施,去拯救這些瀕危絕境的巖畫。
6
大麥地的早期巖畫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我們知道,早期巖畫距今1.6萬年~1萬年之間,中期巖畫距今為1萬~4千年。說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大麥地的先民們就已經掌握和學會了使用硬石塊制作巖畫和刻寫文字符號。
大麥地巖畫區的內容包括日月星辰、天地神靈、狩獵放牧和舞蹈祭祀等。這顯然是一處數量和種類驚人的史前巖畫。
令人吃驚的是,在大麥地巖畫群中,發現了比甲骨文還要早幾千年的圖畫文字。這大概是中國最古老的符號(圖形文字)表達了。
關于漢字的起源,一般的說法是,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了文字,許慎在《說文敘》中說:“倉頡之初,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毫無疑問,中國文字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甲骨文是中國最早最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形成的基礎應該是史前時代陶器圖案符號、巖畫符號及形象的創造和積累。
在大麥地巖畫區及其毗鄰地,我找到了一些遠古時代的石器和陶片。我堅信,遠古時期的大麥地,是人類居住、生活和活動的地區,他們在這里狩獵和采集,他們在這里籌劃著生存的夢想,他們在這里舉行祭祀天地的儀式,他們在這里創造著人類的文化。
大麥地巖畫區內的圖畫符號很可能就是我國原始文字之源頭的重要一支,在大麥地的這些巖畫面前,我發現,這許多象形圖畫與抽象符號已經具備了古老文字的基本要素。大麥地類似文字性質的符號,有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在形體表現和結構表達上,早期巖畫的象形符號與漢字中的象形字有著共同的根脈。
我們知道,文字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最偉大的符號系統。人類最早的書面交流,大概是從繪畫開始的,后來,演化出了部分抽象符號,以表達人類思維的一般過程,直到完全用抽象符號作為文字,表達人類豐富的思想和情感。
在大麥地,巖畫符號表現之豐富,刻畫之古樸,內容之廣泛,都令我驚嘆不已。這些符號大多呈圓形,刻畫渾樸。大麥地是北方游牧部落群體古老文化和原始文字的自然聚集地。
7
人類從未停止過尋找自己所處的位置和方向感,在通往過去和未來的路上獨享發現的樂趣。同一個蒼穹籠罩著我們,才使我們不覺得孤獨。但我們并沒有以自己的存在為存在的理由。我們在這里聽到了一個聲音,來自舊石器時代的這群人,這聲音響徹上萬年,跨越過有限的時空,而今,定格在這里。
在落日熔金的傍晚,我看到的大麥地,巖石表面因長期氧化而呈黑褐色,巖石上因古代人的刻鑿也產生了明顯的色差。巖畫在風吹、日曬、雨淋的共同作用下,變得模糊、遙遠而陌生。在我的感覺中,它們已經消失在昨天的陽光里。
在夕陽的余輝映成的紫色背景中,大麥地巖畫隨那一個時代的不可追溯也失去了燦爛的色彩。它使我想起了母系氏族社會充滿溫情的黃金歲月。那是人類歷史上民俗和文化最動人的一頁。
8
大麥地位于寧夏和內蒙古交界地段,古代羌戎、匈奴、鮮卑、黨項、蒙古等少數民族頻繁游牧于此,并將自己的形象與想象鐫刻在石壁上,成為大麥地巖畫的集體創作者。大麥地巖畫以其數量之宏富、匯聚之密集、內容之精彩,成為中華文明碩大根系中的一支。
據說大麥地巖畫群是一個地質隊員在二十世紀末意外發現的,其面積大約為15平方公里,有三千多組、八千多個巖畫個體圖形,平均每平方公里遺存圖像達到兩百多組,超出了世界公認的“巖畫主要地區”限定標準的20倍,填補了中國沒有"巖畫主要地區"的空白。其中,最大的一幅巖畫寬達9米,高約1.2米,刻畫了100多只動物、符號等形象,富有震撼力。就單幅巖畫看,大概是世界之最。
我的朋友老黑在中衛市環境保護局工作,他給我詳細介紹了大麥地巖畫的情況,聆聽著充滿鄉音的介紹,我想象著遠古時代的大麥地該是一副什么樣子。
聽說這里的方言是世界上最美麗最獨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