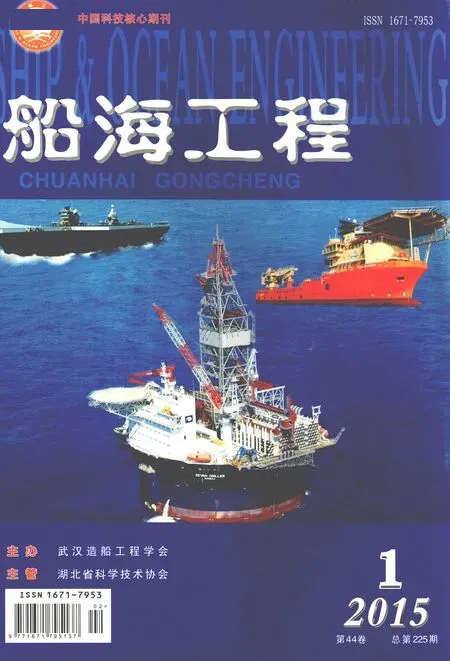船舶空調通風管路減振降噪分析
李艷華,張 成,田華安
(中國艦船研究設計中心, 武漢 430064)
船舶空調通風管路減振降噪分析
李艷華,張 成,田華安
(中國艦船研究設計中心, 武漢 430064)
為了降低船舶空調通風管路的振動噪聲,利用理論估算、數值計算等手段,對SID型隔聲阻尼帶自身的聲學性能以及在典型空調通風管路系統中的實際應用效果進行預報,分析結果表明,5 mm隔聲阻尼帶的應用插入損失效果為5.2 dB,厚度增加效果增大,實際應用收益良好。
空調通風;管路隔聲包覆;插入損失
艙室空氣噪聲能否滿足有關規定的限值,直接影響到船舶人員的居住性和設備的安全性。隨著對居住性要求的提高,空調通風系統的噪聲控制已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
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對如何控制空調通風系統的噪聲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對通風系統聲源的低噪聲設計、管路消聲設計、系統的控制技術和方法等[1-6],并已在實船上進行了實用驗證。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走在了世界前列,除采取常規的治理手段外,部分還采用了有源控制技術[7-8],對空調通風管道進行降噪研究。目前國內外對聲源、傳遞途徑都有大量研究,而管路系統減振降噪的一個重要的實用技術手段是采用管路外包覆隔離噪聲。國內外研究在管路包覆上主要采取隔聲材料,而通風管路的管壁通常比較薄,振動導致其產生的聲輻射也具有一定量級。因此,尋找一種有效的既能隔離輻射噪聲又能降低管壁振動而產生的二次聲輻射的管路包覆就顯得非常有意義。
文中首先對SID型隔聲阻尼帶自身聲學特性進行預報,利用理論和仿真方法得到阻尼帶自身插入損失隔聲量和減振量;然后利用統計能量法,選取典型空調通風系統管路段,建立其計算模型,分析不同厚度隔聲阻尼帶貼附在空調通風管路系統中的實船應用隔聲效果,并得到不同厚度下聲壓響應頻譜曲線。從以上兩方面分析隔聲阻尼帶減振降噪效果,不同方法的預報分析也為文中的預報方法和結果提供了相互驗證。
1 隔聲包覆材料聲學性能預報
SID型隔聲阻尼帶基體材料選用目前成熟應用的DFM型阻尼材料。DFM阻尼材料具有優異的耐海水性能、阻尼性能、阻燃性等。已廣泛應用于艙內管路等部位的減振降噪治理,使用效果良好,毒性符合相關標準要求。SID型隔聲阻尼帶不僅具有隔聲作用,同時還能兼顧降低空調通風管路的管壁振動,進一步降低管壁振動輻射的空氣噪聲。
SID型隔聲阻尼帶尺寸為400 mm×300 mm×5 mm,也可根據應用需求另行設計。
1.1 隔聲效果預報
文獻[9]中關于隔聲量理論計算公式為
R=20lg(fM)-42.5
(1)
式中:f——入射聲波的頻率,Hz;
M——板的面密度,kg/m2。
由式(1)可見,板的隔聲量取決于板的面密度和頻率的乘積(fM)。面密度越大,隔聲量越高。面密度提高1倍,隔聲量增加6 dB左右。實際上,由于受到勁度、吻合效應、阻尼和邊界條件的影響,實際的隔聲量達不到理論公式計算的結果。大量的試驗數據表明,面密度增加1倍時,隔聲量增加5 dB左右。通過長期經驗積累,總結出隔聲量(dB)經驗公式為
R=16lgM+14lgf-29
(2)
一般船舶通風管路壁厚約為0.8mm,根據以上經驗公式估算敷設SID型隔聲阻尼帶后的插入損失效果以及其敷設厚度,見表1。

表1 插入損失估算及材料尺寸
表1表明,當阻尼厚度選取4.5 mm時,插入損失就可以達到5 dB的隔聲量,其隔聲效果可觀。隨著阻尼帶厚度的增加,其隔聲量也增加,當然,重量也增加很多,這就要考慮到總體的重量限制,并且管壁比較薄,還需考慮管壁的承重能力。4.5 mm隔聲阻尼帶隔聲量能達到5 dB,此時面密度與0.8 mm的鋼板面密度(~6.28 kg/m2)相當,隨著隔聲量增大,其面密度是鋼板的2倍、3倍甚至8倍,并且比隔聲量增加倍數要快。因此,從隔聲效果以及總體資源兼顧考慮,建議阻尼帶處理厚度不要超過鋼板面密度的2倍,局部需要特殊處理的部位視具體情況而定。
1.2 減振效果預報
建立風管模型,采用有限元計算方法預估阻尼處理管道的減振效果。管道采用粘貼SID型隔聲阻尼帶的自由阻尼處理方式。通過頻響分析,計算得到阻尼處理前后管道的振動加速度級的衰減。
采用有限元計算軟件(MSC/PATRAN和NASTRAN)對管道以及阻尼處理管道建模。方形管道長×寬=280 mm×120 mm,管道軸向長度為2 m,壁厚0.8 mm。管道模型采用板單元,見圖1,采用QUAD4單元進行劃分,管道結構單元數為336,節點數為348。

圖1 管道有限元模型
對阻尼處理后的管道建立有限元模型,采取對阻尼層和管道結構分別劃分單元的方法。模型為分層有限元模型,按照基層/粘彈性層次序,為殼/實體模型,這種模型將基本結構層、粘彈性層在節點處進行位移協調。所用的橡膠阻尼材料硬度較高,且在工作過程中,變形較小。因此在有限元計算時,將橡膠視為線彈性材料。建立的管道阻尼處理有限元模型見圖2。

圖2 管道阻尼處理方式(在管道外壁四周包覆)
利用有限元計算軟件(MSC.NASTRAN),采取直接頻響法計算管道在采用厚度為5 mm的SID型隔聲阻尼帶進行阻尼處理前后的加速度響應。在距管道邊緣70 mm處(node391)施加100~2 000 Hz的單位正弦激勵信號。見圖3。

圖3 管道邊界約束條件及激勵方式
通過頻響計算,提取管道表面處響應(node249),計算得到管道阻尼處理前后響應點的振動加速度級隨頻率變化曲線見圖4。分析可知,采用SID型隔聲阻尼帶處理的管道的振動加速度級在200~2 000 Hz具有明顯的衰減;在各特征峰值點均有不同程度削弱,振動加速度級插入損失降低幅度達5~10 dB,平均振動加速度級處理前后分別約為153 dB和146dB,降低幅度達到約7 dB。

圖4 管道阻尼處理前后振動加速度級變化曲線
2 典型空調通風系統管路隔聲效果計算分析
為驗證隔聲阻尼帶的實船管路應用效果,選取典型的通風管路段,利用統計能量法對其進行預報。典型管路段見圖5,圖中數字代表管段編號。其中管壁厚為0.8 mm,材料為鋼,橫截面為矩形,其管段的橫截面面積、橫截面邊長和管線長見表2。

圖5 典型通風系統管路段

表2 管路尺寸
采用UG建立管路幾何模型見圖6。圖6中A點為離管路垂直距離1 m遠位置,以管路輻射到該點的噪聲級作為分析對象。

圖6 管路幾何模型
將幾何模型導入VAone建立統計能量模型,見圖7。管路的入口(坐標原點)與風機相連,施加風機的出口聲功率(見表3)。管路表面敷設SID型隔聲阻尼帶,分別為5、8以及10 mm厚,隔聲阻尼帶密度為1 450 kg/m3。

圖7 統計能量模型

表3 風機出口聲功率
通過提取A的輻射聲壓級,整理其輻射噪聲級見圖8。

圖8 A測點在不同厚度包覆下的噪聲級
計算結果,無包覆的總噪聲級為78 dB,采取5 mm包覆的總噪聲級為72.8 dB,8 mm包覆為70.5 dB,10 mm為69.3 dB,其插入損失計噪聲隔聲量分別為5.2 dB、7.5 dB和8.7 dB。根據前面阻尼帶自身隔聲量預報結果,5、8和10 mm隔聲阻尼帶的插入損失為5.4、7.2和8.3 dB,兩種預報結果相當接近,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驗證了計算方法的正確性。所以采用5 mm以上厚度的阻尼帶包覆,插入損失至少可以獲得5.2 dB以上的隔聲量,并且隨著厚度的增加,隔聲量也增加,因此采取隔聲阻尼帶降低空調通風系統管路噪聲是可行而有效的方法,當然具體管路包覆厚度還需考慮總體重量以及管壁承重量等因素。
3 結束語
由于目前工作主要針對阻尼帶對船舶空調通風系統減振降噪效果開展,對實船總體資源的消耗以及經濟性的分析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在后續的工作中可繼續開展聲學效果與總體資源、經濟性等平衡匹配的分析研究,以期為實船的選型應用提供支撐。
[1] 張貽建.地鐵通風系統消聲技術的探討[J].噪聲與振動控制,2009,4(2):76-79.
[2] 李培銘.船舶空調通風系統空氣噪聲治理方法探討[J].船舶機電設備,2008(5):27-29.
[3] 曹宏濤,陳黎明,曲 飛,等.某型船用離心通風機的降噪處理[J].科技與裝備,2003(3):46-47.
[4] 朱偉明,張 揚.艦船空調通風系統噪聲控制技術研究[J].中國水運,2013,13(1):131-132.
[5] 田華安,薛 敏,劉志忠.空調通風系統消聲器設計及試驗[J].艦船科學技術,2012,34(7):118-121.
[6] 錢偉忠,周振宇.改進艦船空調系統舒適性設計的探討[J].機電設備,2013(4):65-70.
[7] KAZAKIA J Y.A study of active attenuation of broadband active attenuator for cancellation of random noise in ducts[J].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1986,110(3):495-509.
[8] ROURE A.Self-adaptive broadband active sound control system[J].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1985,101(3):429-441.
[9] 馬大猷.噪聲與振動控制工程手冊[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2.
Analysis of Vibration and Noise Reduction of Air Conditioningand Ventilation Pipe of Ship
LI Yan-hua, ZHANG Cheng, TIAN Hua-an
(China Ship Development and Design Center, Wuhan 430064, China)
In order to reduce vibration and noise of air conditioning and ventilation pipe system, the acoustic performance of SID sound insulation damping coating and sound insulation effect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a typical air conditioning and ventilation pipe system is forecasted and analyzed by engineering estimation method and numerical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sertion loss of coating is 5.2dB with thickness of 5 mm in sound insulation damping coating. The effect becomes better when the SID sound insulation damping coating is thicker.
air conditioning and ventilation; pipe sound insulation coating; insertion loss
10.3963/j.issn.1671-7953.2015.01.024
2014-08-17
李艷華(1984-),男,博士,工程師
U664.84
A
1671-7953(2015)01-0093-04
修回日期:2014-09-26
研究方向:船舶振動噪聲控制
E-mail:scorpions2012@163.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