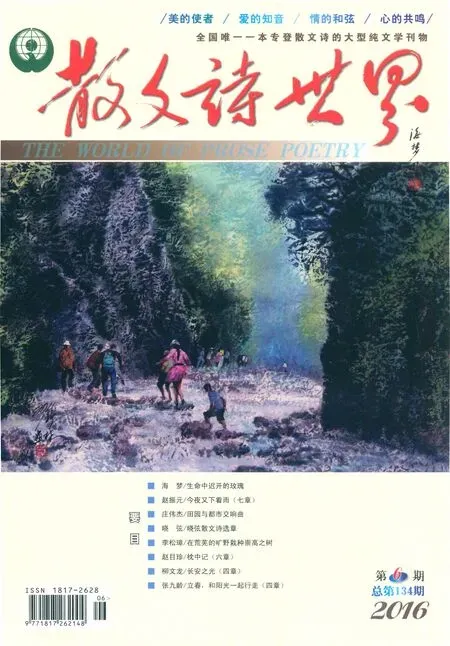我欠故鄉一杯酒(六章)
重慶 譚詞發
?
我欠故鄉一杯酒(六章)
重慶譚詞發
離開故鄉,懷揣一個疼痛的詞語
離開故鄉,我懷揣一個疼痛的詞語——
鄉愁。
是故鄉的石頭,一部分深入大地,一部分櫛風沐雨,我踩踏過,也依靠過。是用來筑橋鋪路、修房建屋的石頭……是一塊絕不會讓人鐵石心腸的石頭。
是故鄉的泥土,保持著大地厚重的品質。我曾把自己想象成莊稼,或草木,生長在樸實的土地上。它也是爺爺奶奶墳前的泥土,父母積勞成疾的源頭;
是故鄉的山野,樹木葳蕤,峰巒起伏。野果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酸澀,甜美。牛羊咀嚼的時光滲透露水和陽光。年少的我經歷過風雨,也經歷過閃電和雷鳴;
是故鄉的小河潺潺地流過,清澈,動聽,像源自某個人的內心。河邊搗衣的女孩歌聲優美,我多次涉水過河,看見自己清晰的倒影;
是故鄉的山路,印著昨天的足跡,笑聲、汗水和嘆息都在路上;
是故鄉的嗩吶,喜慶和悲傷都濃縮在跌宕起伏的調子里;
是裊裊的炊煙,是交錯的犬吠。
是父親額頭的皺紋,是母親兩鬢的白發
一次次將我刺痛。
我欠故鄉一杯酒
故鄉柔軟在內心深處。
我的父老鄉親都是故鄉的王,他們各據三分薄田,視莊稼如命,春種夏長,秋收冬藏;他們修房建屋,養兒育女,對抗病痛,組合成我放不下的故鄉。
他們嗜酒如命,男女老少都是酒的主人,酒是苞谷釀的,飽含汗水和心血。
他們把早晨與黃昏盛裝在杯子里,把喜悅和傷痛盛裝在杯子里,把細小的感動和尋常的幸福盛裝在杯子里。面對酒,他們從不談孤獨和寂寞。
孤獨和寂寞離他們很遠,孤獨和寂寞帶來的傷痛離他們很遠。
對于我的父老鄉親,酒是骨骼里的石頭,是肉體里的山脈,是血液里的支流。
以酒代茶,以酒待客。一杯酒滲透的話題,很長;一杯酒盈滿的日子,很長。有時,他們也將酒杯空著,空著的酒杯盛裝什么?
一杯酒點燃的記憶很美。似醉非醉,很美。似醒非醒,也很美。
離開故鄉,我飲酒時有謹慎,唯恐醉在信箋上,醉在電話中,醉在微信里。有時,我也想舉著天空高深的杯子,飲盡故鄉旖旎的風景。
今生,我注定欠故鄉一杯酒。
我心疼的人揮汗如雨
故鄉的天空在記憶中浩瀚,高遠。
可以寫許多遼闊的詩篇。藍是天空的留白,空出干凈、深邃的句子。是溫暖的藍、純粹的藍,可以繪出無數歲月的錦繡——
飄浮的白云純凈輕柔,插著薄薄的翅膀;
似火的晚霞熱烈多姿,燒紅無限的遐想。
每次仰望,都有清新的喜悅;每次抬頭,都有飛翔的欲望。而我只有一雙隱形的翅膀,被晚風輕輕地托起,童年的歌謠飄向遠方。
遠方在哪里?我的問號,像一朵飄過故鄉的云。
我相信,藍天是故鄉的一本書,富有哲理和內涵,凌空展翅的雄鷹,自由飛翔的小鳥,以及翩翩起舞的蝴蝶,只是時間的插圖。
我是故鄉的一個符號,停頓在村莊的舊時光里。
閃爍的星星是嵌入骨子的書簽,當季節一頁頁翻過,我就長大了,夢幻的童話被郵寄到遠方的遠方。而故鄉的天空依然保持著明凈的底色。當陽光退去,故鄉也有陰郁的日子。
云霧是天空解不開的心結,有一些雨,如泣,如訴。
遼闊的天空下,我心疼的人揮汗如雨。
我只是聽到他們的消息
他們是年輕的標簽,是構成一部小說的人物群體。
每次回鄉,我只是聽到他們的消息。來自廣東,來自上海,來自浙江,來自不同的省市和地區,每一條信息,都是他們遠離故土、顛沛流離的短句。
是工地上揮灑的汗水,是工廠里忙碌的身影,是腳手架上發生的險情……
甚至是一些隱晦的、疼痛的詞語。
他們只是一個遷徙的符號,把濃郁的鄉音播撒在開放的城市,也播撒在偏遠的工地。
他們在風雨中吶喊,在水火中掙扎,把酒當歌,也養兒育女。
他們將春節作為返鄉的號角。
每次回鄉,我只是聽到關于他們的消息。
這讓我想起我的同學,想起他的七個子女;
想起在遠方打工的哥哥;
想起走出去就再也沒有走回來的鄰居。
敬重故土的人有一道隱忍的傷口
鄉村的疼痛從未消停。
敬重故土的人,身上都有一道隱忍的傷口。
鄉村的疼痛是多種癥狀的綜合,貧瘠的土地,破損的老屋,消瘦的炊煙,忐忑的犬吠,以及那些櫛風沐雨的足跡,都有痛感。
歷史遺留的,現實孕育的,意識孳生的……
那些固有的、傳播的、漫延的痛,
是陽光下的頑疾,是風雨中的雜癥,是裂變的傷痕。
那個立志治病救人的人,他要俯身把脈問診,找出鄉村疼痛的癥結;他要揮動手中的手術刀,解剖真相,刮骨療傷;他要讓鄉村守候健康,保持安寧。
可是,刀片劃過如閃電,與病源間隔千層云。
他俯身看到的也不是真相。真相被時間掩蓋,被語言掩蓋,被真相掩蓋。
那些云里霧里的痛,那些不可救藥的痛,那些時間擱淺的痛……
誰能真正治愈?
寫出一撮黃土的寂靜與安寧
一個佝樓的身影,一個背著籮筐在鄉村小路上前行的身影。
他行走,像緩慢移動的山丘,支撐著陽光和風雨。他敬重腳下的土地,每一步都腳踏實地。他看見自己的足跡清晰地印在土路上,汗水一滴一滴浸入泥土中。
他移動的身影像一張弓。
他使盡渾身力氣,那支虛設的箭射向哪里?
他是鄉村卑微的剪影,背負一個時代的重任。他是辛勤的畫家,在季節的宣紙上,繪出輪廓分明的生活:是莊稼?是房屋?是上學的子女?
是一首可拆分的詩,每一個章節都是用青春書寫的佳句。
只要用心閱讀,每一句都有滲透汗水的優美,每一句都有飽含心血的韻律。
這讓我想起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鄉親。
他們把一首詩寫在晨光中,寫在暮色里,周而復始,年復一年,直到
寫出皺紋的形狀,寫出白發的質地,寫出歲月的滄桑。最后,他們用靈魂寫出
一撮黃土的寂靜與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