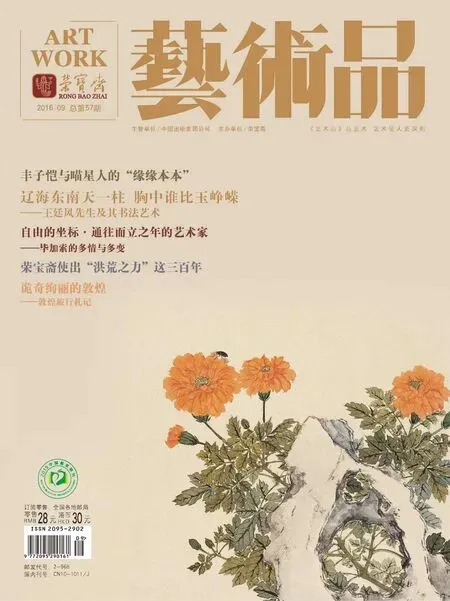自由的坐標?通往而立之年的藝術家—畢加索的多情與多變
自由的坐標?通往而立之年的藝術家—畢加索的多情與多變
文/龔之允
生命短暫而藝術長存。藝術有著超越時空的不朽魅力,是人類生命的一種延伸,既是人們通向理想的媒介,也是社會與個體現狀的載體。
偉大的人物總是能在庸碌之世為人們帶來一絲希望之光,仿佛生命的存在與永恒并不是一種顛倒癡幻。然而偉大的歷史創造者—英雄—總是被常人冠以“悲劇”的色彩,因為人們總希望為自身的平庸制造借口:英雄的成功必然需要經過艱苦卓絕的磨練,必須要有一番痛徹心骨的犧牲。在西方和東方偉大的歷史學家都因為其“天才”而飽受身體缺陷的折磨,如荷馬、左丘和司馬遷。似乎失敗者更受同情和傳唱,如屈原、項羽和拿破侖。
在當下的世界,特別是在被當代藝術的喧囂煩擾的中國,很多人心中名垂青史的藝術家似乎都應該如凡?高那樣,活著的時候籍籍無名、不名一錢,死后才被后人推崇備至,比肩圣人;似乎很早就德藝雙馨的藝術家都只是一時喧囂的弄潮兒。其實仔細研究藝術史就會豁然釋疑,凡?高這樣的備受磨難的藝術大師畢竟是少數派。

畢加索 亞維農的少女 244cm×234cm布面油畫 1907年 美國紐約現代藝術館藏
畢加索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雖然在他之前有凡?高、塞尚、高更,在他之后有安迪?沃霍,但空前絕后的是,畢加索的確無愧為人類藝術徹底走向現代主義的推動者。他的藝術實踐比“后印象派”三大家更激進,徹底推翻了“文藝復興”以來歐洲藝術的原則:單點透視、敘事性和美感。他在“藍色時期”經歷過一段短暫的悲傷和困苦,之后便成為藝術的話題制造者,不但引無數的文人墨客競折腰,而且備受贊助人和藏家的提攜。世界各大美術館都以收藏畢加索的作品為榮,而在市場上畢加索的畫作競拍也屢創新高。那么贏得生前身后名的畢加索是在什么時候奠定其藝術先鋒地位的呢?讓筆者驚異的是,畢加索最具標志性和顛覆性的“立體主義”形成的時期,正是這位藝術家步入而立之年之際。如果說凡?高對自由的選擇是“孤獨的執著”,那么畢加索的抉擇則是“多情與多變”。

畢加索 馬戲團之家 212.8cm×229.6cm 布面油畫 約1905年 美國華盛頓國立畫廊藏樹
一路走來的天才
畢加索出生在藝術世家,父親曾經是藝術博物館的管理員(curator)后來又在一所藝術學院擔任教師。畢加索自7歲起就開始接受父親的系統繪畫訓練。和凡?高完全不同的是,畢加索自小就天賦異稟,他在藝術學校的成績名列前茅無可挑剔。據說他的父親在仔細觀察畢加索的筆法之后,驚異地丟掉了自己的調色板和畫筆,并發誓放棄繪畫,因為兒子作為畫家遠比他出色,他已經沒有繪畫的理由了。①

畢加索 自畫像 81cm×60cm 布面油畫 1901年 法國畢加索博物館藏
畢加索出生于1881年,“世紀之交”(fin de siècle),此時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西方文明已經完成了對世界的瓜分,這也使得西方思想界的視角由擴散式的對外觀察轉向對自己內心的審視。文藝界則由過去的“浪漫主義”“ 現實主義”過渡到“象征主義”,注重對人性苦難的挖掘。“世紀之交”這樣的時代精神和公共認知與西方基督教“末日審判”的意識也息息相關。②十六世紀初的弗洛倫薩就出現過因末世恐慌帶來的文藝復興毀壞運動,美第奇家族被放逐,波提切利不惜自毀畫作以應時局。二十世紀的藝術世界也同樣出現了這樣的恐慌,這種對生命和文明不確定性的焦慮較好地體現在了畢加索早年的創作中。
1900年,19歲的畢加索的畫作代表西班牙參加了在巴黎的世界博覽會,不久巴黎的兩家畫廊就開始代理畢加索的畫作;1901年5月,20歲的畢加索就在巴黎舉行了個展;5年后美國的藏家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把畢加索捧到了新藝術大師的高度,和她旗下的另一位大師“野獸派”開創者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相提并論。③馬蒂斯要比畢加索大12歲,因此畢加索儼然已經是當時新藝術的王者。1906年,畢加索所作的《格特魯德?斯坦因畫像》已經呈現出“立體主義”的端倪了。雖然這幅畫與之前的“藍色時期”和“粉色時期”一樣還保留了一些寫實技法,并且人物的姿態還帶有一絲“古典主義”意味,左右眼睛的不同也蘊含了中世紀基督畫像的那種神秘主義色彩,但是畢加索顯然已經不滿足于對整個歐洲繪畫的探索了。在“藍色時期”,他探索了宗教繪畫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慈悲,嘗試了格列科(El Greco)的那種扭曲的悲情,還運用了傳統象征意味濃厚的手勢來表現“世紀末”的一種集體和個體的危機感。到了“粉色時期”,他開始嘗試把法國式的柔和、情欲和色彩融入到創作中,從普桑、洛可可到安格爾。④他學習的對象由于基數龐大,以至于無法讓圖像學家把他某一幅作品的模仿對象清晰地做一一對應。畢加索毫不掩飾地夸耀道:“藝佳者借,藝絕者竊。”竊藝者無聲無息便能博采眾長,而借藝者則有拾人牙慧之嫌。當歐洲圖像史不再能夠滿足畢加索的時候,很自然地他便會跨越歐洲藝術體系,把竊技的目標投向“原始藝術”。畢加索作為模仿大師對一切藝術都有濃厚的學習興趣,不可謂不多情;但是他又不拘泥于一種框架,往往在吸收大量的繪畫元素后便天馬行空速成一系,不可謂不多變。“藍色時期”持續了近5年,“粉色時期”則不到兩年。1908年到1914年的6年間,“立體主義”的變化也叱咤風雷般地變化著,不僅挑戰了繪畫,而且還顛覆了語言指示和物質特性等概念。如果從后來的“結構主義”觀念回顧那6年間的“立體主義”,畢加索在30歲左右的藝術創作無疑是

畢加索 老吉他手122.9cm×82.6cm 木板油畫1903—1904年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
注釋:
① Timothy Hilton, 1975, Picasso, Thames & Hudson, p. 9. 蒂莫西?希爾頓《畢加索》,泰晤士和哈德遜出版社1975年,第9頁。
②Shearer West, 1993, Fin de siecle: Art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Overlook Press. 希勒?韋斯特《世紀末:在動蕩歲月中的藝術與社會》,俯瞰出版社1993年。
③Christopher Green,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Picasso’s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 克里斯托弗?格林《畢加索的亞維農少女》,劍橋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頁。
④Timothy Hilton, 1975, Picasso, Thames & Hudson, p. 62. 蒂莫西?希爾頓《畢加索》,泰晤士和哈德遜出版社1975年,第62頁。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未能給予畢加索創作于1902到1907年之間的代表作以足夠的重視。簡而言之,我過于急躁地跳到了“立體主義”時期。由于未能給予這一較早的時間段以足夠的關注,我想我忽略了畢加索作為藝術家的本質特征的一條線索。我感受到了他天才的本質,我一再談及,但是我未能很好地把它表述出來。也許我能彌補這一疏漏。⑥一種用視覺手段對人類認識構架的洗牌式定義。
關鍵時刻
英國著名藝術批評家約翰?伯杰(John Berger)⑤的《畢加索的成與敗》是一部備受關注的寫畢加索的專著,因為伯杰基于對畢加索的崇敬而對藝術家的一些不足提出了批評。該書初版于1965年,當時畢加索還健在,其聲望沒有一位在世的藝術家能與之比肩,其泰斗的地位也無人可以撼動,畢氏的生平成就儼然已被神化。而伯杰的著作卻把畢加索從神格拉回到了人格,于是乎對伯杰的口誅筆伐也此起彼伏。關于這本書的學術價值本文在此不作評述,筆者覺得值得關注的地方卻在于伯杰在1989年的該書第二版序言中作的自我批評:

畢加索 生命196cm×129cm 布面油畫 1903年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這位客觀冷靜的批評家也意識到了畢加索藝術成熟的關鍵時期并不是“立體主義”階段,而是在此之前的嘗試與醞釀。1902年到1907年,畢加索的創作經過了”藍色時期”“ 粉色時期”再到《亞維農的少女》,畢加索最終脫離了19世紀末的“印象派”“ 表現主義”和“象征主義”的濫觴,開啟了旗幟鮮明的反傳統藝術規范的“現代主義”。1907年,畢加索年方26歲,就在之后的那一年,“立體主義”(Cubism)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畢加索有很多詩人朋友,他被稱為“詩人隊伍中的畫家”,早年他畫室的門上總掛著“詩人集會”(Au rendez-vous des poètes)的字樣。⑦他主要的詩人朋友有馬克思?雅各布(Max Jacob)、安德烈?薩蒙(Andre Salmon)、阿伯利奈兒(Guillaume Apollinaire),還有先鋒編劇科克托(Jean Cocteau)后來的“超現實主義”教父布雷東(Andre Breton)。這些文人朋友不但開拓了畢加索的視野,并且給他帶來了更多的情感。阿伯利奈兒是其中最富先鋒意識的詩人,他被稱為“畫家隊伍中的詩人”。⑧他對畢加索的評論就充分展現了他對畢加索的認識。1905年他就指出畢加索的悲天憫人讓他在處理繪畫時粗野冷酷,這位西班牙畫家的藝術內容更接近拉丁人而形式上卻如阿拉伯人。⑨1913年他又評價道,畢加索充分展示了對所有藝術的模仿能力,對物體的刻畫有著無窮的欲望,當過去的解剖學再也無法滿足畢加索情感探索的時候,他勢必要重新發明解剖學、重新定位造型、重新定義藝術這一概念。⑩
阿伯利奈兒的“視覺化詩文”和“立體主義”一樣重新定義了西方詩歌的概念。正是他在向觀眾解釋畢加索參與設計的戲劇的時候發明了“超現實”這一詞語。而他也經常以身份平等的方式和畢加索一道出現在畢加索的畫作中。創作于1905年的《馬戲團之家》是畢加索“粉色時期”的完結作品,畫作中他把自己畫在最左側,而他右邊的形同皇帝的小丑就是阿伯利奈兒。畫面上,畢加索身穿格子式的藍衣服,形體瘦長,與穿紅色衣服比較胖的阿伯利奈兒形成了一組對比。他背對觀眾,左手的姿勢有位怪異,甚至帶有侵略性。畢加索仿佛在一種矛盾中:一方面背對傳統與舊藝術訣別,另一方面卻在暗示傳統藝術要抓緊他的左手,不然他就會親自終結它。那身格子衣服在那一時期的創作中反復出現,可見是備受藝術家青睞的一種圖示。當畢加索把具象的事物越發“格子化”的時候,“立體主義”也就筆直地向傳統藝術發動猛烈的進攻了!
“筆直的侵略者”與革命的旗幟
西班牙的畢加索以他者的身份出現在法國,然而他除了短暫地停留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外,幾乎安于現狀,常居法國,歷經兩次世界大戰。雖然納粹曾阻止他展覽的權利,但是整體而言,戰爭并沒有影響到他的生計。畢加索被認為是一位高度獨立的藝術家,極少參與集體式的或運動式的先鋒藝術活動,“立體主義”是唯一一次真正投入團體創造的一個階段。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是畢加索告別和藝術戰友們并肩開拓“立體主義”的轉折

畢加索 執扇少女 布面油畫1905年 美國華盛頓國立畫廊藏
⑤有學者翻譯為伯格,那是錯誤的音譯,伯杰不僅更接近英文原本的發音,也符合業界新華社世界人名翻譯的規范。
⑥John Berger, 1992,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 London:Granta Books p. XV. 約翰?伯杰《畢加索的成與敗》,格蘭塔書業1992年,第XV頁。
⑦Mary Ann Caws, 2005, Pablo Picasso, Reaction Books, p. 41.瑪麗?安?考斯《巴勃羅?畢加索》,反應書業2005年,第41頁。
⑧Francis Steegmuller, 1963, Apollinaire: Poet among the painters,Rupert Hart-Davis. 弗朗西斯?施特格馬勒《阿伯利奈兒:畫家中的詩人》,魯伯特?哈特-戴維斯1963年。
⑨Apollinaire on art: essays and reviews 1902 -1918, 2001, ed by Leroy c. Breunig, MFA Publications, p. 16. 《阿伯利奈兒談藝術:文章和回顧 1902-1918》,勒魯瓦?C?布羅伊尼希編輯,麻省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頁。
⑩同⑨,p. 279. 第279頁。

馬蒂斯 生活的歡樂 176.5cm×240.7cm 布面油畫1905—1906年 美國費城巴恩斯基金會藏
伯杰在評論畢加索時總是用“筆直的侵略者”(Vertical Invader)這樣的詞語;把畢加索比做傳統藝術的“侵略者”很容易理解,然而“筆直的”這樣的形容詞卻很費解。從藝術形式來說,畢加索整體上使用了豎線條來展示藝術的“侵略性”。與此同時從色彩上來說,為了融匯法式藝術(從“楓丹白露派”“ 新古典主義”“ 現實主義”“ 印象派”到“后印象派”和“象征主義”),畢加索沒有采用西班牙國旗的主色調而是使用了法國大革命的“藍白紅”。藍白色和豎線條恰好也是代表西班牙文藝復興的格列克(El Greco)的掠影浮光。盡管格列克對于西班牙來說也是一位來自希臘的“筆直的侵略者”。
眾所周知《亞維農的少女》是對馬蒂斯的《生活的歡樂》一種反相對應。法式的馬蒂斯用濃烈的暖色表現生命的喜悅;而“西班牙”的畢加索則針鋒相對地使用冷色調來表達生命的欺瞞。馬蒂斯使用曲線勾勒人體表達一種永恒的和諧;而畢加索則使用折線鋒芒畢露地表現一種反文明的支離破碎。馬蒂斯的人物以躺著為主,并且融入到了大的自然場景中;而畢加索的人物全部筆直,不僅把畫面占滿,甚至有躍出畫布的一種震懾感。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國旗是藍底白十字中間是帶有紅色王冠的象征王權的旗幟,西班牙的國旗就遵循著這種中世紀以來的紋章旗幟學傳統使用橫向的設計。而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為了顯示區別以往的封建專制象征,而使用了縱向的顏色排布。縱橫兩種設計分別代表了歐洲各國不同的政治體系。如俄羅斯的國旗就沿用了荷蘭王室的樣式。因此畢加索的垂直線條代表著一種激進的歐洲視覺文化,這一點伯杰出乎意料地沒有直接點明。
垂直線條的侵略象征意味在畢加索1905年創作的《執扇少女》中已初見端倪。在創作的草圖中,那位少女由于把扇子平放于腿上,顯得典雅恬淡;而在最后的作品中畢加索卻讓少女的雙臂張開,在垂直面上營造出一種強勢的氣氛。美國現代藝術史泰斗梅耶?沙皮羅指出這表現了藝術家對視野和圖像的強烈控制,其內心情感已經與之前純粹的波西米亞流浪風格出現了質的轉變:因為一年后畢加索就被斯坦因捧為新藝術的領軍者。28歲之后的畢加索再也沒有因為生活而窮促。

德拉克洛瓦 自由領導人民 260cm×325cm 1830年 法國盧浮宮藏
1911年后
“立體主義”在發展時期有著劇烈的風格變化,1911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畢加索在布滿平面線條的畫面上加上了文字,緊接著他便不再滿足于畫布上模糊物體、文字、圖像、意義之間的關系,直接使用了現成品(Readymade,如麻繩、報紙、布帛、沙子等)對藝術門類做了一次顛覆。于是拼貼(collage)出現了,而繪畫被徹底顛覆了。
有趣的是,當這些顛覆性的工作完成之后,畢加索被“超現實主義”團體奉為開拓者,然而他卻回歸到了繪畫上。雖然他還在嘗試陶瓷、泥塑、拼貼,甚至和攝影家合作拍攝了《神秘的畢加索》(Le mystère Picasso, 1956),但是一切卻再也沒有跳出他1911年發明制定的創作原則。

畢加索 帶有藤椅條的靜物29cm×37cm 布面油畫加布貼和麻繩1912年法國畢加索美術館藏

畢加索 苦艾酒杯 21.6cm×16.4cm×8.5cm 彩繪銅塑和苦艾酒勺1914年美國紐約現代藝術館藏
在通往而立之年的畢加索是多情與多變的,他不滿足繪畫又立足于繪畫,他把繪畫作為宣泄情感和創造力的基點。他幾乎學習了一切古典大師的構圖、造型和色彩的原則,信馬由韁揮灑自如地變化著。他身邊的朋友來了一批又換了一批,他的情人們也呈“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架勢。在撲朔迷離的現代社會,他的多情與多變使他藝途愈隆。當然他始終保持著個體的獨立性,與“共同主義”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其波西米亞的流浪精神只有在“立體主義”創作時期有過短暫的停歇。畢加索在而立之年作出了一種選擇,雖然他不像凡?高那樣身處逆境,但是在思想上的斗爭并沒有因此而削弱。
試想已經十分安逸的畢加索又為什么要去冒險作死式地畫“立體主義”呢?之前“象征主義”式的繪畫已經足夠他成為一代寵兒了。對于畢加索而言大師是一種無謂的名號,重要的是對藝術的各種嘗試,對定勢的理性思維的顛覆:
我曾數月持續在加泰羅尼午餐,在這數月中我一直盯著一木板架看,除了心里說這是一個木板架,我心無旁騖。有一天我決定畫這個木板架。第二天我再去用餐時卻發現木板架沒有了。我肯定由于太專注于畫它,卻忘了我已把它拿走這件事。
這種非理性的執著和對描繪物的強烈的全面觀察欲望,正是畢加索多情與多變的精神來源。
伯杰說:“我們都知道藝術并不是真理。藝術是讓我們意識到真理的謊言”。
在發明“謊言”的道路上,畢加索更需要多情與多變,因為歸根到底,這是一條孤獨的道路。
(本文作者為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大學藝術史系教師)
責編/王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