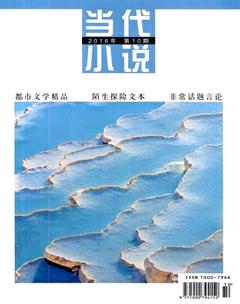五指并攏
詹政偉
接到小毛電話時,我在辦公室接待一個來訪者,來訪者正向我訴說他的悲哀:年老體弱,行走不便,想和老伴住到城里去,兒子卻說城里太擁擠,有霧霾,說還是住在鄉(xiāng)下好……兒子不是一般的人,擔任著一官半職,老是借口忙,連個人影子都見不著,老是電話來,電話去的……
我耐心地聽著,并在腦中思量著該怎么把他的不孝兒叫過來,好好地教育一番。
這時,手機響了。小毛的聲音在電話里顫抖,英濤啊,湯雄出事了。
我一愣,湯雄出什么事?經(jīng)濟上的?這年月,凡是有點職務(wù)的,出事大半都是栽在經(jīng)濟問題上。但我也有些猶豫,因為湯雄一直呆在一個清水衙門,干的也是務(wù)虛活,離經(jīng)濟有段距離。
湯雄人沒了,聽說死在河里……是喝了酒以后
我的血呼啦一下涌到了頭頂。喝酒怎么會到河里?我愣住了。
小毛繼續(xù)嘀咕,不知道崢嶸清楚不清楚,我也是聽說的,不詳細,要不,你問問他。
我“哦哦哦”地答應(yīng)著,隨手撥崢嶸的電話,撥到一半,看到來訪者——七十多歲的馬是之大爺,仄起耳朵,聽我和小毛的對話。
我的臉皮有些燥,便對馬是之說,馬大爺,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情我會處理的。
馬大爺不大情愿地站起來。搓著手皮說,三天給我答復(fù)。行么?
我點點頭。
馬大爺臨走,插嘴說,人總歸要死的,要想開點。
我沒有理他,這個馬老頭老是瘋瘋癲癲的。我都已經(jīng)習慣了。我的心思顯然已不在他那里了,我撥崢嶸電話。
崢嶸正忙,電話里聲音很嘈雜,我小聲說,聽說湯雄沒了,真的還是假的?
崢嶸嘶啞著喉嚨說,我也聽說了。
和哪些人?
不知道。我也在問。等下給你回復(fù)。
放下電話,寒意一下子升上來,像霧,彌漫了全身。
認識湯雄是在牌桌上,我業(yè)余喜歡打紅五,紙牌中的一種游戲,玩的也是衛(wèi)生牌,沒有任何彩頭,一同玩的,要么是同好,要么是熟悉的人。對于真正沉溺于牌桌的人來講,我們的打牌,似乎有點浪費時間。
但誰叫我們有那么多的空余時間呢?!
那天,是在小毛家的車庫里,小毛把車庫布置得像棋牌室,于是有很多的時候,我們都在那里開戰(zhàn)。我和小毛搭檔,牛宏英和湯雄搭檔。小毛是個喜歡交朋友的人,打牌地點又放在他那里,于是他常常充當秘書長的角色,召集人員,提供茶水,便成了他的慣常。
牛宏英也是在小毛那里碰到的。人認識近二十年了,只是不常打交道,這認識也就成了一種虛空。但一旦打過幾場牌,似乎便成了很熟悉的人。
牛宏英是個胖嘟嘟的女人,五十剛剛出頭,卻擁有一頭黑頭發(fā),長發(fā)披肩,她眼神活泛,但很少與你交流,慵懶和噦嗦是其常態(tài),以前手里老是拎著一堆待打的毛線,一有空,就窸窸窣窣打個不停,坐著時,身邊會突然多出一條毛茸茸的尾巴來。與她的長發(fā)相映成趣。后來她就喜歡抱一條棕色的小狗,時不時地用嘴巴去親親它,那樣子,不像一個過五十的女人,而是一個賣萌的小姑娘。她還特別愛笑,笑點特別低,莫名其妙的東西,都能引來她的狂笑,一笑,那大嘴巴張開來,就有河馬的感覺了。
牛宏英不喜歡人家叫她老牛,一叫,就愛大驚小怪地嚷。都什么年代了?還這種老土的叫法!我有那么老嘛,來,叫我牛姐。于是,大家都叫她牛姐,真名倒是讓人忘了。
牛宏英喜歡熱鬧,雙休日,她是喜歡搞活動的,不管大小,都是要碰一碰面的。
小毛以為我不認識湯雄,就介紹說,湯副書記,市直機關(guān)黨工委的。
牛宏英叫起來,小毛,你以為周英濤不認識啊,湯雄還是我們周主席的會員呢!
湯雄于是呵呵呵地樂,我認識周主席,周主席不認識我,官大一級壓死人嘛。
我仔細地看一眼湯雄,還真不認識,于是我笑笑,你入會時誰介紹的?湯雄說是市博物館的邱曉鳴。我樂了,我們協(xié)會有近200號人,我哪里認得全?再說,是邱副主席介紹的,我沒有理由不讓你入會,我這個主席是兼職的,邱副主席倒是專職的。
這個會員,一般人想入也入不了。牛宏英嘿嘿嘿地叫起來。
這倒是。湯雄入的是收藏家協(xié)會。如果沒有收藏品,也沒有興趣,那是不好意思加入進來的。
湯雄說,我小學3年級就開始搞收藏,收藏各式各樣的糖紙。是符合要求才進來的。
這樣,我和湯雄算是正式認識了。
湯雄人高,足有1米80吧,長胳膊長腿的,又黑又瘦,看上去,就像一只剛出水的八爪章魚。
湯雄部隊出身,當了近20年的兵,打牌卻膽子小,束手束腳的,一點都放不開,我和小毛都是牌桌上的老運動員了,相當有默契,于是湯雄和牛宏英就輸?shù)靡凰俊?/p>
一輸,愛贏的牛宏英就跳得八丈高,手指一直戳到了湯雄的鼻子尖上,你搞什么搞?有大牌為什么不出?
湯雄態(tài)度奇好,他囁嚅著說,我是想出的,看你緊張的樣子,我以為你想先出,所以就讓你了。打牌是看牌,你盯著我臉看什么?能看出什么花來?
我“噗哧”一聲笑了,牛姐的臉很好看嘛,怎么看都像一朵花。
化干戈為玉帛。于是繼續(xù)打,他們一如既往地輸。
牛宏英忍不住了,開始埋怨。先前倒是沒見過牛宏英發(fā)脾氣,現(xiàn)在領(lǐng)教了,卻叫人大開眼界,牛宏英像個敲木魚的小和尚,有口無心地敲著木魚,湯雄聽著也不當回事,該出錯牌還是出錯牌,出大錯的時候,牛宏英將手中的牌往桌上一砸,你這樣亂攪,不玩了!
湯雄卻一臉嚴肅地將手中的牌死死地摁住,就像有誰要奪他牌似的,他粗黑的眉毛上揚,一本正經(jīng)地沖著牛宏英說,你把牌撿起來,你這樣干什么?
牛宏英咬牙切齒地說,你個榆木腦袋,不玩了,你聽不懂嘛?!
湯雄一頭霧水,為什么不玩了?不是玩得好好的?輸贏是正常的嘛,總歸有一方要輸?shù)摹?/p>
牛宏英唾沫四濺,你的意思,我們就該輸?
我不是這個意思。湯雄辯解。
你不是這個意思,干嘛亂出牌?牛宏英吼道。
小毛看他們起爭執(zhí)了,連忙做和事佬,牌是紙做,輸過再來。
這個下午的一場牌局,在牛宏英和湯雄無休止的吵嘴聲中落幕。牛宏英輸?shù)脷夂诹四槪餍涠ァ蹍s熱情地邀約,周主席,下個星期,我們繼續(xù)操練!要向你們學習!接著,又給牛宏英打電話,你就等在小區(qū)大門口好了,我出來接你!然后就飛快地跑出了車庫。身手敏捷。
崢嶸的電話來了,他語速飛快地說,湯雄真的沒了,就是昨天夜里,在北西河里……據(jù)說和一班人一起喝的酒……哎,去見毛老人家了,不知道會給他個什么官當當。
這個崢嶸,這個時候,還有心思說笑話,我的心一沉,小毛估算得沒錯,在等崢嶸電話的過程中,小毛又來電話了,說他打牛宏英電話,通是通的,卻無人接聽。莫不是昨夜的酒席她也參與了?
我說,有可能。
因為有很多的時日。我們大家都看見牛宏英和湯雄有說有笑地在一起,看上去比較親密。
現(xiàn)在情況從崢嶸那里得到了證實,我沒有理由不對包括牛宏英在內(nèi)的人關(guān)注。
我對小毛說,有些事,我們沒有必要去參與,雖然我們和他們都是比較處得來的朋友,但也僅僅局限于偶爾喝個酒,打個牌、釣次魚、打場乒乓……細里細的東西,我們是完全不清楚的。
小毛好像輕松了一些,我也理解他的情緒波動,畢竟有段時間,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見上一面,打上一回牌。而且地點往往就是在小毛家的車庫里。
這個上午,我接了N個電話,都是關(guān)于湯雄事件的。是的,有好多人都知道,我有許多的雙休日是和湯雄、牛宏英他們在一起的,他們迫切想弄清楚,昨夜的那場酒,我是否也參與了?我斷然否決。
昨天下午3點左右。我確實接到了一個邀約我喝酒的電話,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在鄉(xiāng)鎮(zhèn)法律事務(wù)所工作的費超打來的。費超說,晚上有個敬重你的人要見你。費超安排酒席,基本上不是談收藏,就是推薦收藏愛好者給我,說是為收藏事業(yè)添磚加瓦。我樂意地答應(yīng)了。但下班回家路上,碰到一熟人,笑問,今天平安夜,上哪兒瀟灑去?
我猛地記起這天居然是圣誕夜。我猶豫起來,因為我給自己定了一個規(guī)矩。節(jié)假日盡量不參與可去可不去的酒席,要陪著老婆。我不能出爾反爾。于是我給費超打電話,說是臨時碰到事了,不能來赴宴了。
費超氣得直罵我,說就等你這尊神了,神卻不來,你讓我等情何以堪?我笑答,神不來,你們可以多吃一點。如果去參加了那場酒宴,我不知道現(xiàn)在會怎么樣。
等到中午的時候,湯雄事件就發(fā)酵了。
無數(shù)的電話告訴我,沒人知道湯雄那天喝了多少酒,就是一同和他一起喝酒的人也不知道。因為他在包廂里喝酒的過程中,跑到外面去敬酒了。在包廂里他喝得并不多,他們總共七個人,4男3女,女的都沒喝酒,4個男的平分了兩瓶卡斯特紅酒。這點酒,對酒量極好的湯雄來講,簡直是小菜一碟。酒量極好的湯雄喝酒后,走到河里去了,然后溺水身亡。
一齊參與喝酒的,有我認識的,也有我不認識的。3個女的,我都認識,她們依次是牛宏英、金玲英、吳中瓊。三人平時比較要好,是合得來的小姐妹,是并聯(lián)電阻,經(jīng)常性串在一起的。她們都是公務(wù)人員,金擔任某銀行的行長,而吳是財政局的副局長。男的,一個是吳的下屬老錢,一個是開發(fā)區(qū)的中層干部丁臨芒,另一個是駕駛員老柯。再有,就是湯雄。
酒席的組織者是金玲英。然后由牛宏英一一通知。
因為是平安夜,所以有了聚會的理由,而那段時間,市里專門出臺了文件,規(guī)定星期一到星斯五公務(wù)人員不能在酒店喝酒。平安夜恰恰是星期三,所以去酒店的人都開了車。丁臨芒是老柯送過來的,送來后,老柯想走。丁臨芒說,人不多,一起吃一點吧。老柯想了想,默認了。一進包廂,湯雄提議男的喝酒,女的不喝,等會兒送男同胞。老柯想拒絕,湯雄說,你車停這里吧,明天來開,反正我的車也停在這里。
酒喝到一半的時候,湯雄就端著酒杯,跑別的包廂敬酒去了,他呆過的部門不少,熟悉的人很多。他脫下的皮夾克掛在他坐過的椅背上。
估計誰也沒有想到,湯雄出去了,就再也沒有回來。
說老實話,我對湯雄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人高大,卻長一雙鼠目,還喜歡翹著蘭花指,總透著那么一股女性味,有點娘。這實在是有點匪夷所思的,你想想,一個大男人,在軍營呆過多年,帶過隊,訓過兵,怎么會是這副樣子?給人的感覺,好像他那副團是開了后門才得到的。開會,也總是習慣性地坐在會議圓桌大約10點鐘的方向,因為這個位置既不顯眼,也不容易被人提問。很多時候,他是面無表情的,所以面目也老是模糊不清,
但和他喝過幾回酒后,我幡然醒悟,湯雄能在部隊混出名堂來,那一定有他的獨門秘訣。酒席臺上的湯雄眉飛色舞,妙語連珠,一反平日的唯唯諾諾。他酒量大,喝什么樣的酒都是一口清。當然,對于能喝的人,我也不當回事,職場這么些年下來,什么樣的酒神、酒仙沒見過,但湯雄卻讓我刮目相看。
湯雄酒微醺的時候,就愛沖著在座的人喊,喂,把你們的手伸出來,讓我瞧瞧,給你們檢查一下,看到底有沒有病。
別人以為他吹牛,不想理睬他,對于酒鬼來講,最好的辦法是不理睬他。
湯雄卻細瞇著眼,一個一個地瞧過去,突然出其不意地逮住身邊人的一只手,狠狠地拉過來,拉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他就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捏起來,邊捏邊問,疼不疼?疼不疼?
被捏的人叫起來,你捏得重了,當然疼;捏得輕了。當然不疼。
湯雄坐直了身子,一本正經(jīng)地說,不是和你鬧,你如果真的疼,就說一聲,我可以判斷你問題出在哪里。
記得那次逮住的是小毛的手,湯雄愈是認真,小毛愈是不以為然,捏到他的小手指時,小毛疼得跳了起來,啊唷,疼死我了!
湯雄發(fā)現(xiàn)奇跡似的問,真的疼?
小毛惑然地看著他。
湯雄又一次捏,這回小毛疼得眼淚都出來了。
湯雄翹著蘭花指說。小毛,你得去查查你的小腸,說不定有點小問題。
小毛嘴硬,我能吃能喝,腸胃一直好好的,估計連樹根也能消化。
湯雄說,我建議你去查一下,沒問題最好,但你的小澤穴疼得厲害,估計不會無緣無故地疼。小毛讓他說心虛了,艦著臉坐在那兒半晌作聲不得。
湯雄笑了,查一下嘛。
接著,湯雄又逮住了另外一只手,是戚老師的,他把他的無名指捏痛了,湯雄說,戚老師,你是不是頭痛?要不就是喉嚨痛?
戚老師叫起來,啊呀,我真的有點頭痛,有好幾天了,一直隱隱約約的。
戚老師的驚嘆,終于吸引了在座的人,他們紛紛主動向湯雄伸出了手,哎,湯書記,給我捏一捏,給我捏一捏。
小毛偷偷溜了,他跑醫(yī)院去了,檢查結(jié)果出來,他跟老婆打電話,哎,那個湯雄,有點名堂,醫(yī)生說我小腸那里有炎癥。
湯雄捋一捋梳得光亮的頭發(fā),解釋說,根據(jù)中醫(yī)經(jīng)絡(luò)學說,人的五指尖各有經(jīng)絡(luò),而且分別與內(nèi)臟有關(guān)系。指尖捏上去有異痛,相對應(yīng)的內(nèi)臟部位就會出現(xiàn)問題。
眾人不明白湯雄為何還懂這一套。湯雄抿著嘴樂,我喜歡看中醫(yī)書,看著看著,就會一點點了。
呵呵,你們知道我為什么喜歡手指,五個手指并起來,就是一扇門,握起來,就是一個拳頭,要是各自為政,那力量就弱小了……呵呵,這也是一門學問,高深著哪!湯雄顯得深有體會地說。
還有一回,是我請客,叫的基本上都是收藏圈的那一撥人,順便把崢嶸、小毛、牛宏英和湯雄叫上了,那時候好像是快臨近春節(jié)了,不知怎么的就說到了春聯(lián)的事,因為座中多的是弄文字的高手,我提議每個人都弄副對聯(lián)出來。
于是依照座次,一個一個輪過去,開始幾個人作的照例是中規(guī)中矩的,那年好像是豬年,于是一片豬聲,狗守太平歲,豬牽富裕年;春新豬似象,世盛國騰龍;看豬大似象,視漏貴如金……
湯雄喝過一瓶多6年陳的紹興花雕后,鼠目更加寸光,他慢吞吞地說,對聯(lián)一定要對得有意思,沒有意思,再工仗也沒多大勁。
寫文章的人。多半都比較自尊,看湯雄一副指點江山的樣子,有些不屑,崢嶸更是冷眼相對,他起哄說,你湯書記也來副對聯(lián),叫我們見識見識,學習學習。
我原以為湯雄會退讓的,哪想他摸摸頭皮,說,那我獻個丑。他說,今天我們大家相聚一堂,就像提前過年,肯定很開心,那我就以此為題,給大家來副對聯(lián):吃紅燒大肉,抽外國香煙。橫批是:過年得神。
崢嶸哈哈大笑。當即奚落,湯書記,你這不是對聯(lián),是順口溜,既不工整,又不對仗,是土八路的干活,怎么就弄出這等玩藝兒來?
湯雄一點惱怒的表情都沒有露出來,他呷一口酒,笑瞇瞇地說,想當年,我看過電影《少林寺》后,也胡謅過一副,我給大家念念,“顛顛倒倒乾坤,歪歪斜斜棍棒。”還有,我一個畫家朋友年紀輕輕就過世了,我去參加他的追悼會,也弄了一副,“偶來人間三十年畫神畫鬼。回去山中八千里寫天寫地。”
你這種所謂的對聯(lián),除了字數(shù)對,其余都不對。牛宏英也大叫小嚷起來,照你這么弄,我也弄得出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橫批是:一派胡言。牛宏英念完,掩住大嘴,嘎嘎嘎地笑,后來,笑倒在桌子上,還是笑。
湯雄又呷一口酒,說,我這是下酒菜,圖的是開心,不必計較。我又不是靠這個吃飯的,又何必較真呢?你們是行家,我說了不算,一孔之見。完全不必在意。
見湯雄這樣說,本來摩拳擦掌,準備與他好好理論一番的人。也就偃旗息鼓了。
我卻一下子對湯雄好感起來,好感在于此人有分寸感,也內(nèi)斂,且肚中有點貨,不是一個草包。
對湯雄有好感,卻有距離感,除了打打牌,喝喝酒,偶爾也說說收藏,但他好像不愿意往那方面談,所以基本上沒什么交談,最主要的還在于,我們在一起時,有一個人物是始終在場的,那就是牛宏英。
我承認我是個有點潔癖的人,這個潔癖源自于我對傳統(tǒng)美德的尊重,看到形形色色的男女關(guān)系,我總會保持相對的警惕,還有,我老婆對我比較嚴格,她老是在我耳邊給我敲警鐘。
湯雄和牛宏英甫一出場,我就在心里打了一個疑問號,他倆到底是什么關(guān)系呢?在這里有必要說一下牛宏英的背景,據(jù)說牛宏英離異了,但到底有沒有和丈夫扯離婚證,誰也不清楚,但有一個事實,他們常年分居,互不搭界。有好多年了,牛宏英一直是獨出獨進。湯雄卻是有家室的,他和牛宏英保持密切的關(guān)系,肯定會吸引眾多人的眼睛,當然,也會有無數(shù)的猜測冒出來。好在只要家里人不鬧將起來,別人是不會理會的。這年月,你能弄清楚什么?
我每次看到他們猶如夫妻一般進進出出,總會感覺別扭。但有時候我也會對自己說,千萬不要想歪了,畢竟牛宏英生活不易,湯雄作為朋友關(guān)照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干嘛把別人想得那么壞?畢竟他們都是有一官半職的人,有頭有臉,不會不顧忌一些東西,特別是他們兩個在眾人面前落落大方的樣子,我就釋然了,所以碰到湯雄把牛宏英車來車去,一同去接牛宏英在外地上班的女兒回家,送牛宏英一些水果干貨什么的,我在心里認可了,也正因為認可了,所以彼此也愿意作些來往。
牛宏英和我們大家都很客氣,也很熱情,碰到一起玩樂,她總是沖在前面,但在湯雄面前,她卻一直頤指氣使的,湯雄就像是她的小跟班似的。我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疑惑,湯雄欠了牛宏英什么,所以要巴巴結(jié)結(jié)的?這也未免太委屈自己了!換位思考,覺得要叫自己也這樣,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同時也想,牛宏英脾氣這么臭,怪不得她老公要與她分手,她有時候做得的確有些過分。
我的印象里,湯雄很少提老婆,提起,也是蜻蜓點水,一拂而過,我們知道的是,他想讓老婆隨軍,老丈人卻不肯,說不想讓女兒帶著外孫女跟他到安徽的山溝溝里吃苦,又說怕耽擱外孫女的學習成績,湯雄作了無數(shù)的思想工作,也沒有效果。老婆帶著女兒長年居住在娘家,他有時候探親回家,回的總是丈人的家。女兒,他也很少提,只有在別人問及他時,他才會慢悠悠地掏出手機,給我們看他女兒的照片。我也看過的,但大多數(shù)都是他女兒和他老婆的合影,偶然的幾張三人合影,女兒也基本上將頭偏向媽媽那里。于是他的身邊常常留著一些空白……
牛宏英終于給我打了電話,她一開口就說,周主席,我這個事你大概都知道了吧。
我捂緊耳朵,悄悄地說,知道一點點。
她卻哭開了,我冤啊,陪湯雄喝了一頓酒,卻要我和陪酒的人每人掏12萬塊錢,這沒有道理啊。
怎么回事?我雖然也耳聞了一些,但還是很想從牛宏英那里知道一點什么。我的好奇心在于,我有些不大相信湯雄是灑醉失足跌下河堤,然后溺水而亡,因為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酒量委實太好了。
牛宏英語氣沉重地說,湯雄在我們那個包廂,酒喝到一半就出去了,我們以為他很快就會回來的,但一直到我們吃完,想離開時,還不見他人影。丁臨芒和他打電話,問他留在椅背上的皮夾克怎么辦?湯雄說。讓老錢幫我?guī)е桑魈煳业剿k公室取。再問他回不回包廂?他說還要敬酒,不回了。后來我們就回家了,回家了,我還給他打了個電話,問他在哪里,可他沒有回。到凌晨3點,公安就把我叫去做筆錄,說是湯雄死了,他的手機上最后留存的幾個號碼中。有我的號碼,我嚇死了……牛宏英抽泣起來。
湯雄到底要干什么啊,他老婆打他電話也不接,他那時候人在哪里,我們壓根兒不知道。湯雄人一死,他老婆像個瘋子一樣,到湯雄的單位里去鬧,說以后還要到我們參與喝酒的人的單位里鬧。她的話說得太難聽了,說牛宏英叫了一群離婚的、家庭關(guān)系不和睦的人一起喝酒。在平安夜喝花酒……
……說我和她老公湯雄有關(guān)系,因為湯雄騙她說,晚上是和單位里的人在一起,就吃個工作便飯。
從湯雄和牛宏英的密切程度里。我就清楚他和老婆的關(guān)系肯定一般般,據(jù)說她在一家學校里當校工,一個月2000來元錢。她到湯雄的單位鬧,主要是關(guān)于錢的問題。她大喊大嚷:一家的頂梁柱沒了,上有老。下有小,你讓我怎么辦?
周主席,我冤啊,一輛小車開到北西河里去了,我是為湯雄作貢獻。湯雄有毛病啊,他自己要死,還拉著我們作墊背,算什么名堂?!……
我安慰她,牛姐,要說倒楣,最倒楣的當然是湯雄。他五十還沒到,就沒了,他又是農(nóng)村出來的,父母年事已高,還有女兒,剛剛考上研究生,他老婆又沒正式工作。一家都指望著他……再說,畢竟都是朋友。嗨。碰到了這種事,只有正確面對。
牛宏英哦哦哦地答應(yīng)著。但她顯然心不在焉。我也不想賠啊,我一個拿死工資的人,12萬,容易么?可人家逼著……一言難盡。
我理解她的苦衷。湯雄事件一出。聽說市里主要領(lǐng)導很惱火,湯雄所在部門,雖說是個清水衙門,但到底還是個重要部門,鬧將起來,成何體統(tǒng)?參與喝酒的人,大多是各機關(guān)部門的,傳出去,對誰都不利,于是責令調(diào)查的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打這個板子其實還是容易的,一句,“你們還要不要頭上的這頂帽子?”又一句,“你們都是公務(wù)人員,在明令禁止下,還敢喝酒,你們不想要這飯碗了?”傳的人有鼻子有眼的,原話也經(jīng)由微信散發(fā)。在一個網(wǎng)絡(luò)時代,你能阻止信息的傳播么?
……我最氣憤的是,所有的人都認為我和湯雄有男女關(guān)系,真是見鬼了,他湯雄臉上生出花來了?我牛宏英檔次低到這個程度了?牛宏英氣急敗壞地嚷。
我不敢過多追問牛宏英,雖然我是那么的想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沒有比探究事情真相更刺激我了。
我所知道的關(guān)于牛宏英的幾個細節(jié)是:她半夜遭警察盤問,做筆錄,抖若篩糠,后來,連說話也語無倫次了,導致胃痙攣,被警察連夜送進醫(yī)院;
牛宏英的手機長時間無人接聽,一直在事情發(fā)生后的第三天,她才開始接聽電話:
老柯拒絕賠錢,他急得跳腳,他媽的,你們都是公務(wù)員,我一合同工,拿什么賠?還有,我本來就不參加聚餐的,是丁臨芒硬拉著我的。牛宏英氣不過,吐了他一口唾沫,直接吐在他面門上。老柯破口大罵,都是你這只狐貍精惹出來的麻煩。牛宏英氣得拿手機砸他……砸也沒用,老柯就是不賠,本來是每人賠10萬元。老柯的抵制,讓他們每人又多賠了兩萬元
和崢嶸一同去參加一個會議,我搭他的車前往,在車上,他忍不住說,英濤,你可能不知道,我差一點點也去參加湯雄他們那個聚會了。牛宏英打電話過來約我了。我單位里正好來了一批客人。好險。不然也要無緣無故拿出12萬元錢了!
我心中一動,因為小毛當初打電話來,讓我問問崢嶸情況,其實也是估計他一同參與了。
我說,你是吉星高照啊,被卷進這種旋渦里,對你總歸不利。
崢嶸慶幸地騰出一手,拍拍自己的額頭,我要去,就慘啦,說到底,我和湯雄并不熟悉,還是牛宏英牽線搭橋,我們才一同打牌,喝酒的,打牌基本上就在小毛的車庫里,喝酒,你們幾個基本也都在場的。
是的,崢嶸這么一說,我想起了屈指可數(shù)的幾次聚會,我們幾個都是在場的,說到底,還是牌友的聚會。
人有時候就是這樣,本來沒啥關(guān)聯(lián)度的,偶爾的相會,以后的再相會,你來我往的,好像成了熟稔無比的人。等到真的想記起某人來,留在腦子里的全是他或她的音容笑貌,盡管生動無比,卻都是淺表的、模糊的。
我也有點后怕地說,如果你答應(yīng)去了,牛宏英說不定還會邀約我的。因為誰都知道,我和崢嶸是非常默契的打紅五搭檔,可以說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好多時候,好多場合,我們會一起出現(xiàn)。當然,別人以為我們是因為打牌才走在一起,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關(guān)系密切。主要的原因還是,我是一個搞收藏的,而他是一個喜歡欣賞收藏品的。我搞收藏近30年了,他欣賞了30年的藏品,當然,最主要的,他還是一個風趣幽默的人,喜歡插科打諢,我每每收到佳品,他總是會一二三四地挑出許多毛病,我一說他,他就跳,說,知識就像內(nèi)褲,看不見,但很重要。還有一次,他說,老婆煩他老不回家,問他是不是外邊有人了?他一本正經(jīng)說,還沒來得及拈花惹草,毛就被人拔光了……還有一次,他說,養(yǎng)魚挺麻煩的,每周要換一次水。我經(jīng)常忘記,只好每周換一次魚……我似乎沒有理由不喜歡這個油嘴滑舌的家伙。
有人說。湯雄死,是因為牛宏英逼婚?!崢嶸不解地問,哎,你怎么看?
我說,也有可能,牛宏英不小了,女人到了這個年齡,特別有恐懼感,所以想抓住點什么。但隨即,我又疑惑,不可能啊,牛宏英那么多年都熬下來了,還在乎一個名分?
崢嶸分析說,或許是湯雄有過承諾的,而且是有期限的,期限到了,所以牛宏英要逼……牛宏英這個人,有冷熱病。對湯雄好的時候,恨不得把一顆心都捧給他,什么事都跟他講,湯雄那次生病開膽結(jié)石,牛宏英三天二頭往醫(yī)院跑。不知道的還以為她是他的老婆;碰到不高興的事,恨不得對湯雄拳打腳踢,常常有沖上去。要把他咬下一塊肉來的沖動……當然,這些也僅僅是猜測,許多細微的事情,誰說得清呢?
在會場上,這個會好像是市民政局的一個年終總結(jié)會,我碰到了小朱,小朱的老公是市公安局的一個副局長,又說起了湯雄事件,她神秘兮兮地說,排除了他殺,是溺水身亡。
然后,我又碰到了攝影家中東,中東是最后見到湯雄活人的幾個人之一,那天,他也在那家酒店應(yīng)酬。接受了湯雄的敬酒。我問,中東,那天湯雄到底喝了多少酒?
中東推推眼鏡,顯得非常肯定地說,他在自己那個包廂喝了多少我不知道,但在我們的包廂,他喝的也不多,喝倒是喝的白酒,因為我們喝白酒嘛。我發(fā)現(xiàn)了一點,他那天很不高興,喝的多半是悶酒,因為他在敬我們酒時,一下子把自己杯里的酒喝干了,而我們杯里的酒。他看都不看一眼。你也知道,酒喝得高興的時候,多半會讓自己少喝一點,而讓別人多喝一點,起碼不讓別人少喝。湯雄那天,狀態(tài)不對。后來,他就轉(zhuǎn)到別的包廂去了。唉,怎么會發(fā)生這種事,不可思議,他又不是沒經(jīng)歷過風浪的人……
那段時間里,沒有誰不提湯雄,湯雄是這個城市里最炙手可熱的新聞。
……周主席,聽說你一直在關(guān)注我,我和你解釋一下,我冤啊,我真的不想死,我女兒很優(yōu)秀的,是清華大學啊,她才上研一,我一走,她怎么辦?無依無靠了,我家里還有老爹老娘,爹八十一,娘七十七。我有三個姐姐,都在鄉(xiāng)下,混得都不好,日子過得很艱難。我老婆也沒個正當工作,別看我整天笑呵呵的,我壓力大啊。可沒人知道我的壓力,他們都認為我位置好,朋友多,很來事。可我心里悶啊!
牛宏英,你知道的,我存心想幫她一把的;金玲英,離婚了,小孩還在讀研二,我也要幫襯一把,誰叫她是牛宏英最要好的小姐妹;吳中瓊。跟老公的關(guān)系一直搖搖擺擺,但她是銀行行長,多的是經(jīng)濟這方面的路子……我喜歡和女人在一起。和她們在一起。我有成就感,人也會放松。我從軍幾十年,很少和女人打交道的,一直到轉(zhuǎn)業(yè),才開始與除老婆以外的女人打交道……和她們在一起,也是惺惺惜惺惺,嘿嘿,一切都是冷暖自知啊……你也知道,像我這種年齡,上不去了,我得掙點錢,為以后的自己著想……高大典,你知道的,方微,你也是知道的,我把自己的錢,還有金玲英、吳中瓊、丁臨芒,還有好多好多我的親戚朋友,他們的親戚朋友的錢,都投在他們那里,但他們一個跳樓了,一個吃官司了……這么多的錢都打了水漂,你讓我怎么辦?……
……喝酒就喝酒唄。提那些不痛快的事干什么?又不是我一個人的責任。你們都不愿意出面,讓我出面,說我崗位好,便于協(xié)調(diào),人緣好,可以溝通,錢都賠進去了,你們一個比一個兇,他們只知道抱怨,一個人也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我也知道,這世道就是這么黑暗,滿目瘡痍……
黎春華,哦,是我老婆,不是我說你,你老是盯著我和牛宏英干什么?你就知道褲襠里那點破事,那點破事,在現(xiàn)在這個年代,算是事么?我和牛宏英走得近,那是因為我們有合作關(guān)系,她有人脈……你啊,頭發(fā)長,見識短,你不相信了我一輩子,我不和你噦嗦了,等到我把錢賺回來,你就知道你老公干的是正經(jīng)事……
……我真的不想死,怎么跌到水里去的?我不知道啊。到了水里,我也不怕,我就是想嚇唬嚇唬他們,讓他們知道,我也是沒有辦法,那么多的錢,你讓我哪里去籌……
我看見一條碩大的魚張著嘴巴向我傾訴,這是一條渾身金光閃閃的大鯉魚,它的每一片鱗片都有金元寶那么大,它幽幽地說,我生活在水里,所以你們看不到我的眼淚!
我奇怪死了,我說湯雄,你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你變成這個樣子,說的卻是人話,叫我怎么相信?!
“嘩啦”一下,湯雄一下子把全身的鱗片都脫光了,你們總是不相信,不相信,你們以為我把錢都私吞了?周主席,老實對你講,連你這樣的人,也不相信我,那我真的只有去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他騰騰騰地沖向前。前面出現(xiàn)一座巨大的雕塑,哦,我看清楚了,那是公園里的一座名人雕像,他把頭撞在基座上,他的頭一下子爆開了,鮮血淋漓。我嚇得魂不附體,尖叫起來。
尖叫過后,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做了一個夢,我感到匪夷所思,居然夢里也出現(xiàn)了湯雄,由此可見,這些天,我關(guān)注湯雄到了一個什么樣的程度。我的關(guān)注,就在于想弄明白湯雄究竟為何而死。
想到夢境中湯雄說的,我將信將疑……
因為他和我說的方微和高大典,我都是知道的。因為這兩個人,都是這個城市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們一個非法集資,一個也是非法集資。
但叫我疑惑的是,高大典和方微的事,都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特別是跳樓的高大典,都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可以說是灰飛煙滅了,難道和湯雄也有關(guān)聯(lián)?要知道,那時候,湯雄還在部隊服役呢!
小毛在湯雄溺水身亡后的第十天,終于熬不住,打了我的電話,手癢了,怎么樣,來我車庫打牌吧?
我說都叫了誰?小毛說,你一個,我一個,還有苗老師夫妻。我說好,吃過晚飯,趕過去,發(fā)現(xiàn)小毛把車庫粉刷過了,空調(diào)、桌子,凳子,也全換了,搞得煥然一新,我詫異,問,怎么啦?
小毛紅了紅臉,他有點口吃地說,湯雄以前老是在這里出現(xiàn),他是生死的,有點不吉利,我們以后都要在這里打牌的,所以……
苗老師夫妻都是教初中英語的,牌也打得好,這天,卻打得有些潦草,因為好幾次,他和她都忍不住地提到了湯雄,這個湯雄,還有牛宏英,到底怎么樣?
小毛噓了一聲,打牌,打牌,我們不說這個。
苗老師的老婆姚老師感嘆道。這人哪,薄若脆瓷哪,想一個多月前,我們還在一起喝酒哪。是的,我記起來了,那天是湯雄請客,請的是他打乒乓的一批乒友。苗老師在湯雄的鼓動下,第一次喝了白酒。喝完后,苗老師還笑嘻嘻地說,其實白酒慢慢喝,也不難喝。
湯雄當即叫好,說,苗老師,你是有基礎(chǔ)的,你夫人在你身邊,你還這樣說,那說明你是有潛力的。
小毛又一次打斷,姚老師,不說湯雄,一說湯雄,我就心慌。
我理解小毛慌什么,他向來安分守己的,突然就有了一個波折,他暈了。
晚上我們基本上打一局牌,無論早晚,為的是不影響第二天正常上班。那天,牌局一邊倒,我和小毛輸?shù)靡凰俊N颐靼祝€是受了湯雄的影響,我們無法做到心如止境,把心智全都用在牌局上。
散場后,我開著車往家走,走到半路,我突然心血來潮,來到了湯雄溺水身亡的地方。那個酒店在一個公園的邊上,這個公園和歷史上的一位名人關(guān)聯(lián)度很大,此刻,公園里還豎著他的雕像。我在接聽別人電話時就發(fā)生過疑惑,據(jù)說當時的監(jiān)控探頭顯示,湯雄一直在公園門口晃來晃去,邊晃邊打著電話。值班室里的保安出來,和他說著什么話。后來,湯雄就跑到里邊去了。在文化局和小朱聊天時,小朱也說,我老公他們公安去問過保安,保安問他干什么?他說我小便可以嗎?保安說,小便當然可以,因為公園的,里面有廁所,但讓保安迷惑的是,他不是在酒店里喝酒么,酒店里多的是衛(wèi)生間,他又何必舍近求遠,而且,那么冷的天,西北風呼嘯著,他居然連外套都不穿。就穿著羊毛衫在凜冽的北風中走來走去打電話
我下車,往公園里走,保安照例攔我,問我干什么?我說我方便一下。
保安嘀咕,小心不要去河邊,小心跌下去,不要像那個湯雄。
我進到公園里,名人雕像在黑暗中挺立著。
我慢慢地沿著河邊走著,這時候,我看到一條枯草黃色的狗不緊不慢地跟著我。這是江南鄉(xiāng)間經(jīng)常可以看到的那種看門狗。但它顯然不是,它的身上沾著不少的泥巴,在昏黃的燈光里,它乞求般地朝我搖著尾巴。我停下,它也停下,我走,它也走。我走到河邊,佇立在那兒時,它居然悄悄地拖住了我的褲腿,嘴里發(fā)出嗚嗚嗚的叫聲,我受驚似的下意識一腳,那狗好像被踢痛了嗷嗷叫著跑開了。但不一會兒,它又悄悄地跟過來了,只是離我稍遠些,怔怔地看著我,眼里露著哀傷的光,有時候,還屈起前腿,好像在跟我打揖似的……
我不理睬它,它就是一條流浪狗,餓得有氣無力,它指望每一個來公園的人,都可以給它一點施舍。我的口袋里空蕩蕩的,什么吃的也沒有,我愛莫能助。何況,我的心思全在湯雄身上。湯雄,你就是在這兒落水的么?
河邊都用石欄圍著,我試了試,要掉下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湯雄到底是在哪兒落的水,我也不知道。黑夜里的河水奔流著,聽不到聲音,但我分明感覺到它的暗流在水下洶涌。
我記起有一年春節(jié)。我到浙南的一個叫古偃畫鄉(xiāng)游玩,在清澈的江邊,突然碰到有人往江里跳,那時候游人如織,有人高喊,有人自殺了,有人自殺了。不少的人竦然一驚,接著,有好幾個人同時跳下了江,合力把那個跳江的人救了上來,那人卻掙扎著反抗,連連說,你們干什么,你們干什么,我不是自殺,我是在搞行為藝術(shù)……
眾人傻了眼。
跳江者委屈地推開救他的人,又一次跳下了江,邊上真的有人舉著攝像機在拍攝……我站了一會兒,聽見一只夜鳥突然在樹林間呀呀亂叫起來,像是受了驚嚇。我全身一哆嗦……
牛宏英有一天給我打電話,她爽朗的笑聲從空中傳過來,周主席,好長時間沒看到你,領(lǐng)導你在忙什么呢?
我說瞎忙。
打牌有空么?有空我打小毛電話。讓他再叫一個。
我那天正好有事,便推辭了。
放下電話,我愣了一下,想牛宏英又活泛起來,她是不是從湯雄事件里走出來了?這時候牛宏英那寬咧的大嘴巴一下又一下親著棕色小狗的情景又在眼前晃動了,照例又聽到她帶點沙啞的嗓音在喊,湯雄,我的手指,你給捏捏、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又不舒服了?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