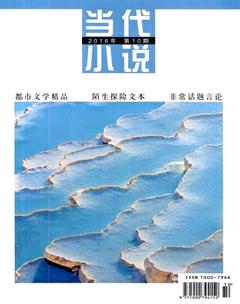蘇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
吳祖麗
蘇先生習慣在天色將暮未暮之時,下樓散會兒步。
蘇先生,全名蘇志文,目前的身份:病人。在那之前,他是部長。不是部長,可以是教師,或者書法家。自認為努力一下也可以做個小說家,他對卡佛、福克納、卡爾維諾等所謂教科書式的經典作品素有研究。但是現在,以上種種。他也只愿意在散步的時候胡思亂想一下。
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時段出門,是因為碰見熟人的概率較小。說散步純粹是自我安慰,作為一個二流大學中文系出身的人,他大致還能記得散步的詞語解釋是指隨意閑行。就他這樣能叫隨意閑行嗎,左腳顫顫巍巍地好不容易邁出去,右腿卻始終不肯合作,在原地磨蹭了幾秒鐘,像等待裁判手里的發令槍似的,終于用盡全身的力量和意念,牽線木偶一樣被指揮著微微劃個圈再拎過去。腦門上已經沁出汗來,不知道是緊張還是用力過度。右手臂僵硬而丑陋地掛在腰那兒,手指痙攣屈曲,伸不直握不緊。生活跟他開了一個詭異的玩笑,他終于明白什么叫天翻地覆,什么叫悲痛欲絕,什么叫欲哭無淚。說到這兒,你大概已經猜出來了,蘇志文是個腦中風患者,腦中風的后遺癥是:右側肢體癱瘓,右臉麻木。他五官中最好看的是鼻子,高挺的鼻梁一筆勾勒出希臘式的清冽側顏,曾令多少女人神魂顛倒,遺憾的是,現在連它也背叛了初衷,不可避免地向左側歪斜。就這樣的現狀,還是蘇志文經過兩年艱苦卓絕的求醫和康復鍛煉的結果。客觀地說,臉還是那張臉,人也還是那個人,甚至連體重都與兩年前不相上下。但是全然不對,整個人崩坍了。就像一個擁有絕世武功的高手,一朝被廢,渾身彌漫著的,是那種抽筋剝骨的疼痛,那種茍且偷生的羞恥。那種不得不繳械投降的絕望和萎靡。
正是源于這種潛在的絕望和萎靡,令他怕接電話,怕跟人打招呼,怕別人憐憫的目光,尤其憎惡自己因口齒不清而無比漫長的語言表達。蘇志文刻意地想要避開原來的熟人,特別是原來圈子里的人。蘇志文原來圈子里的人都是一群衣冠楚楚、昂首闊步的人,或多或少、或輕或重地主宰和影響著這個城市的方方面面,男的一律身著正裝襯衫,深色西褲,女的一律身著考究上鏡的職業套裙,即使最冷的冬天也在大衣里面襯著輕柔的薄呢西裝,時刻準備上臺講話和出席重要宴請,每天提拎精神準備應對鏡頭話筒和閃光燈。不管如何小心,碰上的幾率總是存在的,偶爾他們中的一兩個,下班遲了點,匆匆趕去下一個場合,某個四星五星級酒店,或者某個單位的內部食堂。因為離得近索性步行而去,眼看著就要狹路相逢了,蘇志文不得不異常敏捷地把自己挪到某堵墻后面,或者借助一棵梧桐樹的粗壯樹干,遮擋彼此的視線,避免不得不寒暄問候幾句而引發的難言尷尬。
蘇志文一向是個追求完美的人,這種追求沒有因為生病而被克服。他不喜歡散步,可是每一個醫生都不容置疑地正告他,惟一的康復途徑就是堅持鍛煉。對病人來說,醫生都是判官,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以及生死予奪權。況且他在一百多平米的籠子里跟自己戰斗了一天了,好吧,就出來散步吧。他慢慢有了經驗,挑那些人少僻靜的地方走。他不習慣自己以這樣一副拄著拐杖的畸零形象,落人那些熟人的眼睛。是的,他恨透了這根拐杖,這種恨,就像他離不開它一樣強烈。每回出門前,他都躊躕上一陣子,猶豫要不要帶上門后的紫竹拐杖。下意識里,拄上這根拐杖,好像殘疾人士的標簽就貼在后腦勺上,撕也撕不掉了。反過來一想,不拄這根拐杖,難道別人就看不出他是個腦中風患者?這么一想,更加泄氣。思想斗爭個兩三回,不過是自己給自己找不痛快,末了還是拄著拐杖下了樓。這根深棕色的紫竹拐杖還是那年蘇志文去黃山時買的,真是鬼使神差的,買回來也沒送誰,被李月琴收在儲藏室里。他在省城住了五個多月醫院回到家,一眼就看到擱在客廳玄關處的拐杖。就在這個時候,李月琴回頭看了他一眼,頗有些深意。蘇志文正趴在小舅子的背上,目光交錯的剎那,她知道他看到了,她是故意的,蘇志文竟分辨出她眼里一閃而過的快意。
蘇志文沒有想到,他人生的坍塌。反倒成就了李月琴。
一年前,兒子考入蘇城的重點高中。蘇志文接到了組織部門的免職通知,這個決定延挨了大半年,眼看蘇志文不可能完全康復重返崗位。也算仁至義盡了。李月琴大約從蘇志文仕途的終結里悟出某種人生哲理。決定去蘇城陪讀。沒有商量,她就拿出家里所有的積蓄,在蘇城開了個美容會所,居然漸漸做得風生水起。
直到這個時候,蘇志文才發現原來自己真的不那么了解她。這些年,隨著仕途的不斷上升,他身邊來來往往地有過不少女人,她哭過鬧過,末了,還是默認了。他一直以為她軟弱,沒有社會經驗,甚至沒有多少生存能力。這一年,她大部分時間都在蘇城,為著他們之間殘存的義務和責任,她平均每周回來一次,采購生活用品,陪他去醫院。不知不覺中,這個女人成功地完成了婚姻中的角色轉換。蘇志文想到這個,總會驚出一身冷汗。
兩年前的一個清晨,蘇志文站在洗臉池前刷牙,忽然感到強烈的頭暈惡心,吐得一塌糊涂。等在樓下的駕駛員一分鐘也沒耽擱,很快把他送到醫院。那時意識尚算清醒,他競記得打個電話給副職,我不太舒服,八點鐘的會由你代為主持。然后就陷入了昏迷,先天性腦血管畸形引發腦出血。醫院十分慎重,立刻組織轉院到省城。術后的一兩周,康復情況頗為樂觀,他對自己的身體向來自信。一個人的自信,不是無緣無故的。這些年,他從一個高中語文教師,到機關文秘,到文廣新局副局長、局長,四十歲不到,儼然已坐穩宣傳部長的位置,他成了很多人艷羨的政治新秀。仕途的歷練,權力的予奪,甚至其中不為人知而又微妙無比的跌宕起伏,一點一點把他全力塑造成一個說一不二、目標明確、意志堅定的人。絡繹不絕探望的親友同學同事,甚至主治醫生也在盡力烘托某種樂觀的情緒。省城的三個大學女同學,一日三餐輪流送飯和陪護,加上他美麗的妻子,病房里竟然鶯鶯燕燕起來。三個中的一個在校時就一直仰慕他,另外兩個相繼與他有過親密關系。蘇志文困在病床上,看著她們圍著他忙來忙去,恨不能替他分擔病痛的親切模樣。他不動聲色地享受著她們的美麗、溫暖和撫慰。某一個瞬間,對那三個女同學竟有了綺麗的聯想,不由得暗暗紅了臉。蘇志文不確定李月琴有沒有看出什么端倪,她似乎很樂意接受三個女人的幫助,非但沒有吃醋,反而有些自豪。蘇志文不免胡思亂想,看來權力不僅是男人的春藥,更是男人馴服身邊女人的魔杖,只要用得恰當。無不化腐朽為神奇啊。
誰能想到呢,緊接著病情急轉直下,醫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書。新的出血點位置敏感,不適宜二次手術,專家會診的結果是保守治療。好不容易過了危險期,他出現了偏癱和失語癥狀,住了五個月的院。他僅能斟詞酌句地說幾個單字。
就是這種情況下,蘇志文也沒有喪失信心,他無比積極地配合治療,因為太積極了,出現運動過度引發的抽搐,被醫生嚴厲地叫停。他是太著急了,他知道那個位置不會一直空著等他,他這一病,給了多少人機會和希望。幾位重要領導相繼上門看望,拍著他的肩膀說了許多鼓勵而溫暖的話語。蘇志文卻分明感覺,他們俯視他的目光像在看一個瀕死的人。有一次,某位重要領導和秘書走后,李月琴哀怨地說,平時天天在外喝酒,偏偏那晚推了飯局,在家喝稀飯。言下之意,如果是在外參與公務接待,跟組織上還有條件可談。蘇志文沒有說話,極為罕見地有一點夫妻同心之感,他自己也千百次設想,哪怕倒在公務接待的現場,也有幾分悲壯色彩。現在這樣算什么呢,先天性腦血管畸形。
除了每天一次或者隔天一次(遇雨雪天氣中斷)的放風式散步,蘇志文基本上都是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家里。看看電視,看看書,機械地做寂寞無聊的行走康復鍛煉。在家里不用拐杖,處處諳熟于心:書房橫走是九步,豎走是十步。客廳繞一圈需走三十一步。從臥室到衛生間是十八步……間或,遵醫囑做一套上下肢的關節康復運動操。他不知道做這些有什么效果,好像有時候感覺好些,有時候感覺差些,并沒有明顯好轉。晚上,用熱水泡手泡腳,水溫總是對得太高,手腳泡得通紅,就差那么一點就要燙傷了,還是性子太急。
看書,也是為了刺激大腦和鍛煉語言表達,除了看還要讀。他選的第一本書和惟一一本書,就是斯坦利·艾林全集中的《本店招牌菜》,還是在大學時買的。花去他一周的伙食費。蘇志文是斯坦利·艾林的忠實粉絲,追讀過他所有的謀殺小說。但是,跟其他粉絲不同的是,蘇志文最喜歡的并非作者的成名作《本店招牌菜》,而是詭異驚悚中帶點輕松家常風格的《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艾伯比先生是個有意思的人,喜歡井然有序的生活,追求細節完美,并且目標明確。十八年后重讀,蘇志文更為傾倒。甚至,他發現自己與艾伯比先生具有某種神秘的關聯。蘇志文也迷戀井然有序的生活,不能忍受任何破壞,不能忍受因為疏于打理而臟亂的臥室,床頭柜上桌上飄窗上到處扔著靠枕、衣物、紙巾、遙控器,以及各種藥瓶和藥瓶里的說明書,等等。蘇志文追求完美,他喜歡訂制西服,帶低調袖扣的襯衫,一塵不染的皮鞋,然后在落地玻璃窗里,頗為自戀地瞥見自己高大修長的身影,心情愉悅地對鏡中人很知己地點點頭。蘇志文從離開教育系統那天起,就一直目標堅定地行進在路上,他年輕,他有涵養,他善于表達,總是能在各種場合恰到好處地彰顯閱歷和學養。當然。現在已經成為過去式了。
《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這篇連標點符號在內一共一萬兩千八百二十五個字的短篇小說,被蘇志文朗讀了無數遍,從開始的磕磕絆絆,到最終的嫻熟生動。直至倒背如流……
蘇志文第一次走進小區對過的足療店時。頗有些躊躕。他以前出差,跟同事朋友同學出入過許多高檔足藝中心,但是從未領教過這樣的小店。店面很小,門口的牌子上寫著:足浴、按摩、推拿、針灸、拔罐等等。一處臨時搭建的披廈。借了一幢居民樓的外墻,進去之后倒還可以,一個外間兩個小隔間。店里沒有顧客,只有兩個中年女人在看電視劇。見他進來,皮膚白些的那個站起來招呼他,師傅,泡腳啊。蘇志文心下凜然,木然地點了點頭。他看著迎面的一扇玻璃推拉門里映出的自己,一件藍不藍灰不灰的夾克衫,一雙老北京布鞋,一副踉踉蹌蹌的步態,一張萎靡不振的臉,人家不稱呼你師傅稱呼你什么呢。
她帶他進了對面的隔間,兩張床上都是白布單白毛巾,倒也干干凈凈的。皮膚白的很熱情,自我介紹叫朱蓮。又聒噪說,師傅是第一次來吧,做得輕啊重的,你說一聲。蘇志文含糊地說,正好,正好。朱蓮又推薦他做個全身按摩,還說長期堅持,對他這種中風后遺癥的康復效果特別好。蘇志文問,全身按摩多少錢。朱蓮說,不貴,八十塊。蘇志文說,八十還便宜啊,我不如去醫院了,醫院還能報銷。朱蓮有點不悅,師傅,醫院能有我們服務好啊,再說了,去醫院多麻煩,又是掛號又是排隊的。我們這兒,腳一抬就來了。
第二次去的時候,朱蓮不在,另外一個叫唐姐的女人嗑著瓜子看電視劇。蘇志文笑著說,怎么我每次來都沒有顧客的。唐姐說這個點不是上客時間。她看蘇志文四處張望,就告訴他,朱蓮今天不在店里。唐姐比朱蓮手勁大,按得他全身的汗都出來了。蘇志文一動不動地趴在那兒,幻想身體里的血管在四處奔流。他腳一著地,就能跨回到兩年前。
來,翻一下身。唐姐邊說邊手下帶了勁。
你們老板是誰?
我和朱蓮合伙的,老板是我們,伙計也是我們。
生意怎樣啊?
小本生意,糊個嘴。
蘇志文打量著這個叫唐姐的女人,皮膚有點黑,歲數看上去不小了,但眉眼倒很好看,有點風情的樣子。蘇志文看她有些面熟,似乎像記憶里的某一個人,他想不起來。他現在終于明白什么叫大腦短路了,真是精辟啊,他每天都處在短路的焦慮中。他大腦中的接收天線出了問題,不是短路,就是接觸不良。總之是比別人慢上兩三拍,別人說的話,他總是很吃力地接收一下,才能反應過來。等他反應過來,人家已經說到下一句了。
唐姐在他右側身體上多花了點時間,帶著那么點體貼的意思了。他記得以前看過一份報告,其中提到這一類設施簡陋的足療店里的女技師,其實就是兼職的暗娼。朱蓮,唐姐,可能嗎?都像,又都不像。他睜開眼睛瞄了一下,她的臉正對著他,近得怕人,睫毛低垂。鼻尖上幾粒細細的汗珠。他不適地閉上眼睛,感覺她輕微地移動著,她的手擱到了他的左側大腿,隔著條極薄的淡藍棉布單子,她先是上下撫摸了一遍,接著是極富節奏的揉捏捶打,左腿有了新鮮健康的刺激,熱熱的溫度彌漫開來,幾乎令他感動落淚。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一瞬間,身體非常荒唐地起了反應。蘇志文鎮靜地躺著,一、二、三、四、五、六、七,默數到七的時候,那里冷卻下來。從來不會超過七。她的手帶動著他翻了個身,淡藍棉布單子蓋到后背。他并手并腳朝下趴著,臉貼著按摩床洞,白色帶暗紋的地磚上一只脫離組織的螞蟻,正張皇失措地轉來轉去。蘇志文無聊地看著那只螞蟻,幾乎可以想像它恐懼害怕的表情。
做完按摩,他又躺了一會兒。墻上的電視機還在沒完沒了地播著那部韓劇,唐姐漫不經心地看著電視劇跟他聊天。他告訴她自己是個公務員,現在病休在家,老婆去蘇城陪讀了。她很驚奇,你老婆扔下你一個人?他有點為她辯護,她找了個鐘點工,一天三頓飯兼打掃洗衣服。他說著,不停低頭去看地磚,螞蟻不見了,白色地磚上什么也沒有。他告訴她這個叫小桃的鐘點工做飯如何難吃,如何不愛干凈。她循循善誘地問,小桃是不是長得很漂亮?他很配合地說,是還可以。唐姐就很大聲地笑。小桃的身影在她的笑聲里浮現出來:她第一次上門,烏黑的頭發束成馬尾巴。穿著件松松垮垮的煙灰色長毛衣,襯著一件黑白格子襯衫。她看他的眼神里帶著點兒驚奇,年輕得像個女大學生。他知道她其實沒有看上去那么年輕,三十出頭,有個讀一年級的女兒,丈夫在外打工……
那之后,他隔了許久才又去足療店。她們兩個都在,朱蓮就很自然地招呼他。他正躺著做腳,外面進來一個人,嚷著頸椎不好要刮個痧。蘇志文認出是從前常去的美濤美發的小老板。現在他不去那種地方,锃亮的地板,到處都是明晃晃的鏡子,各種洗發水護發素染發劑焗油膏精華素,前幾號發型師都要預約,消費的不是人民幣而是貴賓卡。現在好像沒必要了,就在樓下老李的鋪子里解決了。蘇志文閉著眼睛假寐,好像所有美發店的老板都饒舌,因為整日跟女人打交道的原故。人也顯得有些女氣,個子不高,發型總是很夸張,四周剃得看得見頭皮,頂上留一撮,像公雞頭上的冠。他們還特別通,這個城市里的政商顯貴,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一張宏大的網,他們就像俯瞰其上又游刃其中的網管。他們收集信息,同時不加分辨地傳遞信息,隱秘的緋聞,盤根錯節的關系,捕風捉影的消息。從來不需要對誰負責,也沒有誰向他們負責。水滴石穿,日積月累,呈現在你面前的這個群體,往往特別會說話,特別能混事,特別容易做朋友。
蘇志文這會兒特別怕這個小老板認出他來。腳做完了,他賴著沒起身。朱蓮偏偏性子急,來,到那邊按摩床上。
小老板轉過頭來看了一眼,遲遲疑疑地說,蘇,蘇部長啊?
蘇志文懶洋洋地睜開眼睛,笑笑,什么部長啊,現在閑人一個。
兩個女的都停了動作,瞪著他們。蘇志文也沒說話,耷拉著眼皮躺在那兒。小老板果然什么都知道,于是唇紅齒白地感慨了一番。蘇志文很想對準那張唇紅齒白的臉來上那么幾下子。讓他再開個顏料鋪子,他不自覺地握緊左拳,又慢慢放松。于是,他什么也聽不到了,只是心里起了點惆悵,像冬天的玻璃窗上那層淡淡的霧氣,影子一樣跟著他。
唐姐沒說什么,繼續捏著玉板刮痧。朱蓮一驚一乍地說,哎呀,真沒想到,真沒想到呢。
蘇志文從書房出來時,客廳的電視機開著,小桃在廚房。電視機在重播本地臺的新聞,蘇志文聽聲音就知道是她。果然,還是那樣引人注目,妝容精致,衣著優雅,正是她所孜孜以求的時尚雜志上的名媛風范。就在上個月,李月琴指著她(當然是電視上的她)說。你還不知道吧,你女朋友要結婚了,嫁了個官二代。兩年前,她還是他的女朋友,或者說情人。雖然她沒說過,蘇志文看得出來她是想過要跟他結婚的。惟獨為了她,蘇志文曾經動過離婚的念頭。他生病之后,他們只見過一次。她跟著一幫人來醫院看他,普通的上下級禮節,至多摻雜點朋友式的關心,那以后,她大概就把他刪除了,沒有電話,沒有短信,沒有微信和QQ留言。
這樣很好。蘇志文想著,慢慢關了電視。他朝著廚房說,小桃,讀書。小桃出現在廚房門口,系著小熊圖案的圍裙,她一邊在小熊的臉上擦著手,一邊走過來。蘇先生,還是讀艾伯比先生?自從讀過《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之后,她就觸類旁通地稱呼他蘇先生了。小桃捧著小說,一邊讀一邊走來走去。她的聲音像唱歌一樣,跟小說內容極不相符。蘇志文卻饒有興致地看著她,這個女人有小鹿一樣輕盈的四肢,神態中還殘留著女孩的純真。他知道她絕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純真,正如她也絕沒有看上去的那么年輕。她十六歲學美術,十八歲那年跟美術老師私奔。高考時因為文化成績不夠而落榜,她開始四處打工。用她的話說。后來她跟一個混蛋結了婚。這個混蛋已經失蹤一年多了,手機停機,地址失聯,莫名其妙地人間蒸發了。她不大會收拾房間,卻很會收拾情緒,收拾生活投射給她的種種陰影。蘇志文斜倚在沙發上,舒舒服服地放平自己,又朝小桃示意,邀請她一起躺下來讀書。
蘇先生,我賣藝不賣身。小桃彎腰笑。
你就是賣身,我也消受不起啊。蘇志文喜歡跟小桃斗嘴,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瞞著李月琴每月另貼一點錢給她。
蘇志文一邊拉小桃并排躺下,一邊笑著說,來來,關愛殘疾朋友。人人有責。
小桃就笑,然后順從地躺下來,很合作地擺出一副關愛的姿勢。她的頭和他的頭,她的身體和他的身體,間隔著一點點可供想象的距離。她是李月琴拐了幾個彎的親戚,算起來比他們晚一輩,誰在乎這個呢。她繼續往下讀。
讀到第三節,她忽然停下來,問他,一小塊地毯真的殺了六個,不,七個人,可能嗎,又不是哈利波特的魔毯?
蘇志文帶著鼓勵的微笑看著她,很像一個盡責的語文老師,似乎在表揚學生,好,這就對了,你終于抓住了小說的中心思想。
下午來的時候,你買塊小地毯帶來。
小地毯?
是的,就像書中說的這樣,不要太大,放在走廊那兒,客廳電話機旁邊的位置。
為什么?
我們照著書中內容模擬。蘇志文神秘地說。
小桃顯得很有悟性地笑了。
小桃走后,蘇志文上床躺了一會兒,奇怪地沒有睡著。他起身到書房研墨,書櫥里有格抽屜,放著他這些年收藏的墨錠。上個月,他取出抽屜中最貴的一盒。一盒四塊,印著清瘦的梅蘭竹菊。一塊的價值約等于他一個月的工資,他慢慢磨掉了它們。這會兒,他又取出一盒新的。硯臺上年代了,還是爺爺傳給父親,父親又傳給他。用老的東西都有靈魂,幾滴清水就活過來。右手在左手的幫助下捏住墨錠,慢慢轉圈,“磨墨如病”,像他這樣,倒真適合研墨。右手握不住筆,但是還能假裝握住一塊墨。書房有幾幅蘇志文的書畫作品,一面墻上是幅小楷的心經扇面。另一面墻上掛著花卉四屏。有位名家對蘇志文的小楷評價甚高,認為“妍麗清秀,用筆遒勁,有隋唐風致……”曾有人想出重金買他的心經,蘇志文笑著拒絕了。如果說書法有些家學,他的花鳥小寫意完全是業余愛好。這幅四條屏,蘇志文純為致敬白石老人,一為牽牛,一為菊花,一為牡丹,一為枯荷。
他想起小桃得知這些是他寫的畫的,立刻瞪大了眼睛,哎呀蘇先生,你這要去帶學生,賺錢不要太多噢。
蘇志文笑著暗自搖搖頭,不慌不忙地,把磨好的墨汁悉數倒人下水道。手機里的收音機出現一個嚴肅的男聲,播送著一則本地法治新聞:2016年4月26日,原交通局長馬長斌涉嫌嚴重違紀被立案調查。蘇志文咧嘴笑了笑,挺好的,至少比他蘇志文的下場好。關個三五年出來,照樣風風光光重新做人。蘇志文要想徹底康復重新做人,怕是不可能了。
一個下午,蘇志文在書房磨磨蹭蹭。看看時間差不多了,心情激動地不停看表。終于等到小桃上樓,鑰匙在外面不停抖動,其中一支插進鎖孑L,她閃身進來。小桃出現在門口,眼睛亮晶晶地看著他,手里拿著一塊小地毯。
蘇志文看了一下,很滿意地說,就放那兒。客廳與三個房間相連的那段走廊,光線略暗的盡頭,有個嵌入式胡桃木吧臺,通常放電話機和花瓶。蘇志文示意小桃把地毯放在吧臺不遠處,客廳到主臥的通道上。一切就緒,蘇志文端著一杯水。
他說,小桃,我們開始,對照書上的說明,精確到每一個細節,開始一次完美的表演。小桃不知所措地站在地毯上。
“將一只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下方,一只手繞過她的脖子,再突然推一把。”他背著。
我遞水杯給你。
我是丈夫?
是的,你是丈夫。我是那個妻子。
我一只手放在你肩膀下方,一只手繞過脖子,再推你一把?
小桃個子太矮了,夠不著蘇志文的脖子。他們只得互換了角色。蘇志文端端正正地站在小地毯上。小桃端著一杯水,慢慢遞給他。他一只手伸到她肩膀下方,一只手繞過她脖子,他用使得上力的左手推了一下,小桃向后仰去,小地毯跟著滑了一下,漂亮的玻璃杯摔了出去。幸虧小桃有準備,她抓住了旁邊的胡桃木吧臺,于是,花瓶也飛了出去。客廳里一地的玻璃碎片,蘇志文卻滿意地哈哈大笑。
表演堪稱完美,果真如書中所說,事情發生得很快,除了褲子上濺了幾滴水以外,其他都完成得干凈利落。艾伯比真是一個體面的聰明人,蘇志文對小說更加愛不釋手。
蘇志文的死,是對門阿姨發現的。因為兩家處得不錯,李月琴放了一把鑰匙給阿姨,方便過來照應照應。那天早晨,阿姨開門進來的時候。看到他躺在客廳通往主臥的過道上,玻璃杯打翻在地,竟沒有碎。陶阿姨想拉他起來,才發現人已經涼了。
警察來的時候,現場謹慎地維持著原狀,蘇志文躺在地上像是正在進行一個小憩的睡恣,客廳整潔明亮,空曠寬大的沙發上孤零零躺著一本郁郁寡歡的書。一個小警察拿起來翻了翻,書簽處正是那篇《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小警察顯然沒有興趣,鄭重地把書放回原處。
他們告訴李月琴,都是那塊地毯惹的禍,正常人都容易絆倒,更何況他這樣一個腦中風患者。加上他又端著一杯水。李月琴反復打量著那塊小地毯。她確信這不是他們家的東西。阿姨也說,她也從未見過這塊小地毯。這塊小地毯似乎成了某種詭異的謎團,成了哈利波特的魔毯。
李月琴很傷心,反復跟人哭訴他恢復得很好,他們還打算賣了這邊房子,到蘇城買房定居。誰能想到,摔個跟頭把命都送了,都是這塊該死的地毯。這時候,李月琴才想起來小桃,這個點小桃應該來了。她拎著地毯茫然地問,小桃呢?小桃呢?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