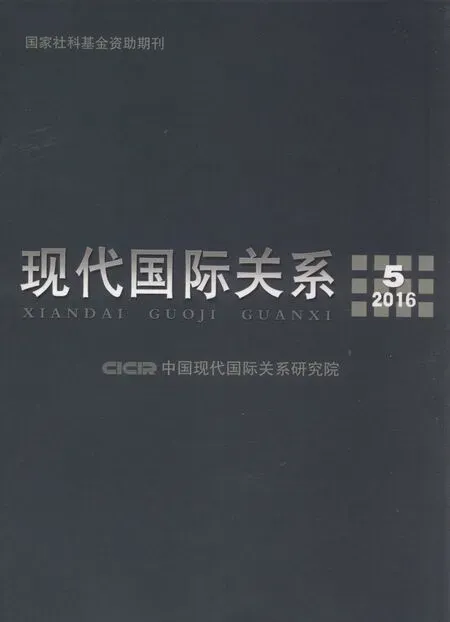試析德國面臨的“領導力困境”
李超 王朔
試析德國面臨的“領導力困境”
李超 王朔
德國是歐盟事實上的“領頭羊”,但目前并不善于發揮領導力,在主導應對歐盟內外挑戰的過程中遭遇諸多難題。德國面臨的“領導力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國獨特的國民性格和歷史經歷所致,一定程度上也與其尚難快速適應當前國際形勢發生劇變有關。德國對此亦有所認識,正在積極調整政策,試圖以更靈活的手段推動歐洲一體化、參與國際事務。未來德國將逐步適應自身角色以及環境的變化,并展現獨特的領導力。
德國 領導力 歐洲一體化 國際責任
[作者介紹] 李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德國問題;王朔,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歐洲一體化、歐洲經濟等。
2008年以來,全球形勢風云變幻,歐盟及其成員國經歷重重危機,唯獨德國“獨善其身”,不僅經濟發展“一枝獨秀”,國際地位也持續上升,還被推上“歐洲領導者”的位置。但是受歷史包袱和自身傳統觀念所限,德國還不能完全適應其地位和責任的變化,在試圖發揮“領導力”,推動歐盟一體化進程及化解國際沖突的過程中,遭遇了諸多挑戰,應對乏力,更為外界所詬病。為何德國自身實力雄厚,卻在領導歐洲時顯得進退失據?今后德國到底能否擔當引領歐盟的大任?本文將就此試作初步分析。
一
近年來德國在歐盟內實力地位持續上升,但能力越大意味著責任越大,歐盟內外面臨一系列難題,都有待德國發揮主導作用來解決。然而,德國并不擅長領導他國,尤其面對歐盟內部千差萬別的利益訴求和外部盤根錯節的國際關系,德國猶如處在“十字路口”中央,深感彷徨,甚至不知所措。
具體而言,德國在發揮領導力方面主要有如下四大困境。其一,德國所堅守的價值理念與當前現實之間存在錯位,這集中表現在其難民政策上。眾所周知,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政府對難民態度較為開放,最初曾敞開國門,允許難民不經登記而直接進入德國境內。默克爾的“開放政策”并非心血來潮,2015年8月難民危機大規模爆發之初,絕大多數德國民眾支持接收難民,這主要是因為德國民眾對難民存在“歷史情結”:納粹德國的侵略行徑曾經在歐洲制造過大量難民,使德國人對難民普遍負有“人道主義虧欠感”,總想著能一定程度彌補曾經的過錯。同時,20世紀80年代末,大批東德人涉險前往西德避難,包括東德出身的總理默克爾在內的德國人更能理解難民的處境。接收戰亂地區和受政治迫害的難民,對于德國來說幾乎意味著“政治正確”,即使代表民粹勢力的政黨,也不會輕易挑戰“接收政治難民”的“底線”。然而接收的口子一放開,難民就以潮水之勢大規模涌來。2015年僅從“巴爾干路線”進入歐洲的難民就超過100萬,而德國是主要目的地,其中不僅有政治難民,也包括來自巴爾干國家打算改善生活的“經濟難民”,使德國不堪重負。于是德國主張在歐盟內實行“配額制”,各成員國共同承擔安置任務,但由于許多歐洲國家并不像德國一樣背負歷史負擔,缺乏主動接納難民的意愿,因而越來越多地抱怨德國的做法。特別是東、南歐國家作為難民進入歐洲的主要通道,安置壓力和安全風險較德國更為直接,其中東歐普遍“家底薄”,南歐則經歷債務危機打擊尚未恢復元氣,自然對德國“攤派任務”更為不滿。波蘭、愛沙尼亞等就明確拒絕執行難民攤派方案,斯洛伐克甚至將此上訴至歐洲法院,并稱“只接收基督教難民”。隨著形勢日益嚴峻,原本支持德國政策的奧地利和北歐國家也紛紛與德國“劃清界限”,丹麥在丹德邊境設置邊檢,奧地利則引入了“難民上限”。“盟友”的態度轉變對德國形成很大壓力,畢竟人道主義是德國“軟實力”和價值觀的一部分,若急速收緊政策,不但有損德國國際形象,也損害政府信譽。因此,到底是堅守價值理念,還是顧及民眾和成員國的現實利益,令默克爾很是頭疼,媒體也多以“默克爾失意”、“默克爾對歐盟影響力不再”等描述德國領導力的下降。默克爾自已也坦言,“難民危機的復雜程度超過烏克蘭危機與歐俄關系”。*Robin Alexander, “Merkel steht vor einer historisch paradoxen Situation”, http://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50321992/Merkel-steht-vor-einer-historisch-paradoxen-Situation.html.(上網時間:2016年4月1日)
其二,德國沒能在“堅持自我”與“尋求妥協”之間找好平衡,尤其在經濟治理方面。德國在經濟發展道路上有其獨特的一面,即習慣過“緊日子”,嚴格遵守各項財政紀律。在解決歐債危機的手段上,德國同樣秉持該理念,“按規矩辦事”,拒絕給予重債國特殊待遇,不提供無條件的援助和債務減記,而是將緊縮性財政政策推廣全歐,敦促重債國搞結構性改革。然而問題在于,不是每個國家都持相同的理念,國與國之間的差距更客觀存在,簡單將“德國標準”強加給其他國家,不僅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還會引發極大的抵觸情緒。以希臘為代表的重債國就一再高呼“不堪壓榨”,并常向媒體展示德國的“鐵面”態度與希臘的“弱者”形象,以博取同情。2015年初,希臘激進左翼聯盟上臺執政后,出臺反緊縮和反改革舉措,與德國矛盾進一步激化,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陡增,市場極為緊張。而德國卻依然我行我素,財長朔伊布勒甚至以“希臘退出(歐元區)風險可控”來“震懾”希臘,默克爾也默許其相關表態,被希臘輿論怒稱為“納粹分子”。*Joachim Huber,“Karikatur: Bundesregierung will Vernichtung der Griechen”, http://www.tagesspiegel.de/medien/nazi-vergleich-in-griechenland-karikatur-bundesregierung-will-vernichtung-der-griechen/11968326.html.(上網時間:2016年3月25日)最終雖然德國的強硬態度占了上風,希臘政府幾乎全盤接受了改革要求,但并不等于根本上解決問題,結果反而更糟:希臘經濟因“退歐”風險受到極大沖擊,增長率從年初預計的3%直降為-1.4%;一年內不得不兩次進行議會選舉,政治穩定性大打折扣;更嚴重的是希臘等“邊緣國”與德國等“核心國”的互信進一步受損,嚴重影響歐盟團結。此外,圍繞應對債務危機,德法兩國矛盾也在加大,“德法軸心”的推動力有所減弱。法國傳統上就主張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發展,對德國“緊縮模式”不以為然,尤其當前法國經濟不佳,財政赤字、公共債務水平難達歐盟規定的標準,奧朗德政府又屬左派政府,對希臘政府容易產生同情。法國反對德國以“退歐”來恐嚇希臘,強調“退歐”后果嚴重,堅持推動談判與妥協。而從德國的角度看,法國不僅在希臘問題上“站錯隊”,其自身也是問題多多。默克爾就曾暗示,意大利、西班牙等國改革“取得了成效”,而法國是個“短板”。然而法國畢竟是大國,德國無法像指揮希臘一樣指揮法國,如何推動新形勢下的德法合作,同樣令德國領導人感到為難。
其三,德國在推動歐盟一體化進程中遇到的阻力不斷增加。關于歐洲一體化的前景,德國一直都是堅定的“聯邦主義者”,認為理想的狀態是建立“歐羅巴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統一政治、經濟、安全政策,各國緊密合作,共同發展壯大。然而德國版的“歐洲夢”在現實中卻屢遭挫折,其中尤以英國當前搞的“脫歐公投”對德國震動最大。英國從歷史上就對參與歐盟事務三心二意,重視維護自己 “金融中心”、“全球大國”的利益。因此,與德國支持“聯邦”不同,英國的理念是“邦聯”,更多將歐盟看作一個“松散的聯盟”,要求歐盟維護英國的獨特性。一石激起千層浪,英國“脫歐公投”刺激多個國家以同樣方式發泄對歐盟的不滿:不少荷蘭政治家已發聲支持英國“脫歐”,并稱若荷蘭利益得不到重視,也將考慮發起公投,*Nick Gutteridge, “ Dutch Urge Britons to Back Brexit Amid Despotic EU Plot to Ignore Their Voters”, http://www.express.co.uk/news/uk/657883/EU-referendum-Brexit-Holland-vote-Britain-leave-Brussels.(上網時間:2016年4月22日)捷克總理索博特卡也持相同立場;有經濟學家預測,如果英國脫歐,希臘也將很快退出歐元區;*Elizabeth Anderson, “Greece ‘Could Leave Eurozone’ on Brexit Vote”, http://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16/04/20/greece-could-leave-eurozone-on-brexit-vote/.(上網時間:2016年4月22日)歐盟內此起彼伏的“脫歐”聲嚴重打擊了德國的領導力。經過多輪博弈,2016年2月19日,在德國的積極推動下,歐盟與英國達成一致,英國將在歐盟內保留“特殊身份”,脫歐可能性顯著下降。但這勢必在歐盟內形成示范效應,其他國家將為本國利益更多地與歐盟討價還價。與此同時,歐洲社會極端思潮顯著上升,給德國推動一體化帶來了更多的阻礙。當前,歐盟安全形勢惡化,伊斯蘭恐怖襲擊成為最大安全威脅,而成員國政府普遍應對乏力,民眾排外、反歐情緒明顯上升,極端、民粹勢力趁機坐大。縱觀歐洲各國,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德國選擇黨以及瑞典民主黨、芬蘭人黨等極端政黨不斷瓜分主流政黨選票,拋出廢除歐元、趕走移民等極端主張,要求維護“民族國家利益”。這不僅有悖于德國一貫倡導的民主、包容的價值觀,也背離了其致力推動的一體化發展方向,而要扭轉歐洲這股急劇右轉的勢頭,德國明顯感到勢單力薄。
第四,德國外交政策相對保守,在踐行“大國責任”方面與外界期待存在較大差距。近年來,德國實力有所上升,外界對于德國承擔更大責任的呼聲也在升高。2012年2月,時任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曾公開宣稱,相比擔憂德國“強權”,他更擔心德國的“不作為”。*Markus Bauer, “Ist Deutschland eine Milit?rmacht?”, http://www.focus.de/politik/deutschland/sicherheitskonferenz-in-muenchen-ist-deutschland-eine-militaermacht_aid_710463.html.(上網時間:2016年3月23日)2013年6月,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在訪德時號召德國“展現斗爭精神,不局限于一時的安逸,要放眼全世界的公正與和平。”*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the Brandenburg Gate——Berlin, Germany”,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19/remarks-president-obama-brandenburg-gate-berlin-germany.(上網時間:2016年3月28日)然而對于外界的殷切期盼,德國感到壓力巨大,力不從心。畢竟德國在國際舞臺上還是“新手”,尚未熟練掌握在各方之間“縱橫捭闔”的能力,面對一個個沖突和危機,就如一個新入職場的年輕人,突然被委以重任,雖希望有所作為,但能力明顯不足,其典型例證是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表現。當時德國雖積極介入其中,但既無力統一歐盟內各成員國立場,又受美國施壓,既要顧及東歐國家的反俄情緒,也要考慮到歐盟對俄羅斯的經貿、能源需求,掣肘頗多,難以抉擇。烏克蘭危機本就由美、俄主導,德國發揮實際作用的空間實在有限,更多還是“搭平臺”和“傳話”。雖然默克爾被認為是“西方為數不多能與俄坦誠對話的領導人”,但其與普京存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嚴重缺乏互信,極難達成一致。
二
可以看出,德國當前所遭遇的困境,并非自身發展出了問題,無論國內民眾還是歐盟成員國,批評聲也主要集中在其處理外部事務的方式方法上。現實已經把德國推到了歐盟“老大”的位置,外界對于德國的需求和期待自然也在上升,德國原來可以置之不管的事務,如今卻必須有所作為。但問題是德國似乎還沒有找準自身的定位,地位、能力與行動意愿之間也不匹配,時常偏執于“自我化、理想化”的行事風格。因此,需要對德國的歷史、文化、政策理念以及內外環境的變化等進行深入剖析,才能真正理解其“領導力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
第一,德國人一直在心理上抗拒成為“領導者”。歷史經驗告訴德國,“單打獨斗”和“霸權主義”終將遭遇失敗,只能通過自身實力來影響他國,維持“均勢”大局,才能保障和平穩定。可以說,這是“血的教訓”,亦是二戰后德國參與一切外部事務的心理基礎。從地理上講,歐洲國家數量眾多且普遍面積狹小,德國又地處中心,邊緣與中心力量此消彼長,導致自中世紀以來,德國所在之地就一直是“歐洲中心與邊緣的角斗場”*Helmut Schmidt, “Deutschland in und mit Europa”, http://www.spd.de/aktuelles/Pressemitteilungen/21498/20111204_rede_helmut_schmidt.htm.(上網時間:2016年4月1日),如果“中心”過于強大,必將招致周圍各派政治力量的打壓。歷史上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就一直致力于在歐洲大陸維持“均勢”,并在此基礎上最終實現了德國的統一。他聯合奧地利攻打丹麥,聯合意大利、法國發動普奧戰爭,戰后又迅速修復德奧關系,協調俄、奧以發動普法戰爭,合縱連橫,避免單干。但威廉二世上臺后卻拋棄了這一政策,嘗試追求“稱霸世界”,結果在一戰中遭遇慘敗。此后的納粹統治者更是膨脹自大、鼓吹“德意志民族高于一切”,最終將德國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如今德國在外交政策上十分謹慎低調,一方面因為其背負兩次世界大戰的包袱,至今尚未完全獲得諒解,一旦在某些問題上過于強硬又不符合別國利益時,就會遭遇別國以歷史問題為由的責難,美國對德國政要開展系統性監聽就是一個典型例證,說明外界對德國“重歸霸權”的擔心從未停止。另一方面,歷史教訓也在德國人心目中深深烙下印記,即只有“聯合”才能事有所成,只有做好“平衡者”,才能在歐洲“地緣的夾縫中”求得和平發展。因此,德國人樂于協調各方利益,在此過程中充當“榜樣”,希望以自身軟實力影響別國,更愿意在“幕后”發揮作用,不愿“拋頭露面”充當領導者。在外界高調炒作“德國領導論”時,德國人卻保持高度警惕,公開場合諱言“領導”,更多強調“合作”,尤其注重與法國溝通,盡可能將法國推向前臺。在此問題上,聯邦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就一再教導德國人要“銘記歷史,攜手歐洲,服務歐洲”,*Helmut Schmidt, “Deutschland in und mit Europa”, http://www.spd.de/aktuelles/Pressemitteilungen/21498/20111204_rede_helmut_schmidt.htm.(上網時間:2016年4月1日)不要嘗試搞“德國的歐洲”。
第二,“文明國家”(Zivilmacht)和“克制文化”是德國外交政策的“基因”。1992年,德國特里爾大學政治學教授漢斯·毛爾(Hans W. Maull)總結二戰后德國外交政策并對比美、日,提出著名的“文明國家”概念,其核心內涵在于:一是嚴控武力,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重視人道主義,通過多邊渠道商討處理國際事務;二是推動“集體安全”的機制安排,向國際機構讓渡部分主權;三是維護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管控下的秩序,不單純以民族國家利益為行事準則。*對“文明國家”的解讀,詳見Hans W Maull, “Zivilmacht Deutschland”, Handw?rterbuch zur deutschen Au?enpolitik,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3, S.73-84.毛爾認為,二戰后德國的外交實踐最接近“文明國家”的理想類型,該理念也被此后的歷任德國政府所接納和堅持。近20年的德國外交實踐中不斷強調“以理服人”,反對“強人所難”;重視“國際規則”,反對“霸權主義”;重視“協商對話”,反對“軍事干預”。這與美、法等大國理念截然不同。在對待武力的問題上,德國尤為謹慎。二戰后,為全面消除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對外侵略的國際形象,德國在政治安全領域極大地約束著自身行動,很大程度上為德國重返國際舞臺奠定了基石。久而久之,“和平主義”和“克制文化”深入骨髓,成為德國外交安全政策不變的傳統。若論軍力,德國無疑是個“弱國”,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統計數據,2015年德國軍費開支占GDP比重僅1.2%,遠低于英國的2.0%和法國的2.1%;*SIPRI,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5”,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604.pdf.(上網時間:2016年4月5日)德國軍工業十分先進,國防軍的裝備卻十分老舊,常常出現故障,以至于2016年新增軍費開支不得不主要用于更新裝備。但必須承認,德國這種“克制文化”長期以來受國際社會認可、本國民眾認同,即使外界環境發生變化,德國人在心理上也很難輕易接受一種積極的、先發制人的外交風格。2002年施羅德政府曾強烈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2011年默克爾政府拋棄盟國,拒絕參與利比亞戰爭,均是民意的集中體現。即便在當前十分緊迫的反恐問題上,德國依然不愿使用軍事手段。2015年11月巴黎恐襲案發生后,德國最初僅是表示譴責和哀悼,支持力度還不及英國,完全沒有體現出德法關系的“特殊性”,法國十分不滿。后經奧朗德與默克爾閉門商談,德國態度才有所“進步”,決定派兵支持法國的軍事行動,但實際上也僅限偵察保衛等后勤領域,為此法、美一再敦促德國“更多出力”*“Deutschland muss noch mehr gegen ISIS tun!”, http://www.bild.de/politik/ausland/isis/mehr-unterstuetzung-gegen-isis-43779854.bild.html.(上網時間;2016年4月5日)。不少人認為德國這種“軍事克制”做得有些過頭,屬于“從‘權力狂暴’(Machtbesessenheit)的極端走向了‘權力忘卻’(Machtvergessenheit)的極端”。*連玉如:“‘新德國問題’探索”,《歐洲》,2002年第3期,第72頁。德國聯邦國防軍協會主席伍斯特納(André Wüstner)也認為德國在軍事方面承擔的責任太少,因為“自由和安全不能免費獲得”。*“Wüstner: Sicherheit und Freiheit haben ihren Preis!”, https://www.dbwv.de/C12574E8003E04C8/Print/W29KQCEM565DBWNDE.(上網時間:2016年4月5日)
第三,德國人的性格中,有嚴謹、務實、崇尚規則的優點,也有自負、倔強、不會變通的缺點。國民性雖然不是外交政策走向的直接決定因素,但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政治家的行為方式。從普魯士時代起,國王就注重建立標準化、高質量、步調一致的軍隊,給士兵灌輸“負責任、守紀律”的觀念,戰斗力由此大幅提升。經過長年累月的發展,形成了如今舉世聞名的“德意志精神”。*楊佩昌:《為什么德國國富民強》,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43頁。德國人遵守規則的態度近乎達到偏執的程度,他們堅信,只要創設合理、有效的規則,每個人都按章行事、各盡其責,任何事情都可順利進展、不出故障。例如針對難民大規模涌入,德國并不認為歐盟真無力應對,而是在邊境管控、難民登記和攤派等規則的設定和執行上出了問題,因此默克爾一直執著于細化規則,敦促各國嚴格執行,同時堅持反對設置接納上限。由此可以看出,德國人解決問題的思路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在規則上下功夫。但問題是德國人往往太過自信,倔強地認為適用于德國的規則即是最優規則,“德國模式”理所應當成為“通行模式”。這種自負心理成為德國與希臘等歐盟“邊緣國家”發生齟齬的導火索。德國是歐盟的“老大”,政策效應波及全歐,但德國近年來的一系列政策安排,如接納難民、推行緊縮等政策,更多是基于自身實力和價值觀制定的,慣于以“德國標準”要求全歐,較少顧及別國國情。波蘭現任外長瓦什奇科夫斯基就明確要求德國對波蘭“多一點理解”,并質問德國“要奴仆還是要伙伴”*“Polens Au?enminister: etwas mehr Verst?ndnis der Deutschen w?re wünschenswert”,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polen-aussenminister-witold-waszczykowski-fordert-von-deutschland-mehr-solidaritaet-a-1070296.html.(上網時間:2016年4月12日);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批評德國在難民問題上推行“道德帝國主義”*Michael Dalder, “Orbán wirft Deutschland moralischen Imperialismus vor”, http://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5-09/viktor-orban-horst-seehofer-csu-einladung-klausurtagung.(上網時間:2016年4月12日)。這些不滿情緒加深了歐盟成員國間的緊張關系,同時也加重了德國“領導歐洲”的心理負擔。
第四,德國與其他成員國利益分化令其難以“號令諸侯”。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有句名言,“德國統一和歐洲一體化就像一塊獎牌的兩面”。意即二者不可分割,統一的德國,其一大使命就是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在此過程中,德國一直以自身為樣板來打造歐盟。一方面,德國希望引導歐盟向“聯邦制國家”方向發展,在諸多領域鼓勵成員國向歐盟讓渡主權,既包括財政政策,也包括情報交換、邊境管理等安全政策,將歐盟委員會打造成接受歐洲議會監督的政府。另一方面,按照德國央行的模式來建立歐洲央行,這也正是其放棄馬克的一大前提條件。事實上歐州央行多年來的貨幣政策總體思路也與德國相一致,即以維持價格穩定為首要目標,奉行穩健偏緊的政策導向,主張建立完善的規則和監管制度。但問題在于,成員國發展模式及對一體化的理解各不相同,德國的主張并不一定能使所有成員國同樣獲得利益,一些國家必然所失大于所得。對德國來說,強勢的馬克被相對弱勢的歐元代替后,出口能力進一步增強,“歐元區核心國家”的地位也為其帶來諸多政策便利,支撐其出口導向型經濟,故成為一體化的“最大贏家”;但英國就希望維護“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不愿過多受到歐盟制度束縛,也不會接受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理念。與此同時,歐盟成員國實力分化加劇,歐元區內外界限日益清晰,盡管歐盟一直不鼓勵固化這些差異,抵制“雙速歐洲”、“核心歐洲”的表述,但這已經是既成事實。*馮仲平:“歐盟發展前景和中歐關系”,《現代國際關系》,2012年第9期,第5頁。處于邊緣的弱國不滿這種身份的不平等,自保傾向有所加重,并不愿犧牲自身主權,來成就德國的“領導力”。當前歐盟的改革和制度建設步入“深水區”,德國的主張越來越深地觸及成員國主權和現實利益,因而也越來越多地遭遇抵制。意大利總理倫齊就曾在歐盟2015年冬季峰會上抨擊默克爾的歐洲政策,稱其“利用德國在歐洲的優越地位,推行僅利于德國的政策”。*“空前激烈,外媒稱意大利總理歐盟峰會炮轟默克爾”,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51220/1031921.html.(上網時間:2016年4月12日)
第五,國內“孤立主義”抬頭也阻礙德國在歐盟積極作為。德國推動歐洲一體化的主要考慮就是通過“抱團”來實現“集體安全”和“共同發展”。一體化幾十年來,德國從中獲利頗豐,因而民眾十分支持。然而隨著全球化程度加深,歐洲一體化進程受到不少負面沖擊,尤其近幾年來,歐盟周邊沖突頻發,地區性危機此起彼伏,一向安全狀況良好的德國恐襲風險也急劇上升,加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歐盟更不景氣,德國民眾也頗感失望。鑒于德國體量大、實力強,在歐盟遭遇挑戰和困難時,往往需要德國來“善后”和“買單”,侵害到部分民眾的利益,民粹主義因而上升。例如,德國本來支持建立歐洲銀行業聯盟,卻因擔心債務共擔殃及自身經濟而封鎖“泛歐存款擔保”方案。在難民問題上,德國民眾雖同情難民,但當面對“巴伐利亞州數百人的小鎮安置6倍于本地居民數量的難民”以及“難民參與科隆性侵案”等極端事件時,民意就發生逆轉。3月13日,在德國三個州議會選舉中,成立僅3年的民粹政黨“德國的選擇”得票率均達兩位數,在薩安州甚至成為第二大黨,令外界震驚。該黨不僅排外,還要求廢除歐元,其主席公開要求默克爾下臺。一旦類似的民粹政黨借危機而坐大,必然對德國政府制定“負責任的歐洲政策”帶來不利影響。
此外,默克爾的執政風格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德國發揮領導力。一方面,默克爾為人謹慎,決策前習慣“等等看”,決斷力相對較弱,尤其不善于應對突發事件。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初,德國猶豫徘徊,寄望其能自行緩解,直到沖突激化后才被迫介入。*Jan Techau, “Deutsche Führung”,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rz/April 2016, S.67.在是否軍事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默克爾決策同樣遲緩。另一方面,默克爾較為倔強,不會變通。當國內外輿論已開始反對繼續大規模接納難民時,默克爾仍堅持自我,一再宣傳其著名的“我們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默克爾在2015年8月31日的記者會上首次針對難民危機提出該口號,隨后多次重申,經媒體宣傳引用后廣為人知,代表了德國傳統的“歡迎文化”,成為默克爾難民政策的“代名詞”。的口號,貽誤了調整政策的最佳時機,還一度引發外界質疑其總理地位是否穩固。在歐債危機期間同歐盟國家談判時,默克爾也是強硬有余而妥協不足,顯得缺乏“領導藝術”,令外界將其行為看作是“強迫”和“指揮”,故而有“納粹幽靈再現”的質疑。
三
德國在歐盟內究竟應當發揮怎樣的作用?這既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新問題。在國際政治的概念中,人們常用“德國問題”來描述其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作為曾經的殖民帝國、“遲到的”民族國家以及強大的工業和軍事國,一再對歐洲及國際秩序發起挑戰,其霸權行為給世界帶來浩劫。但隨著德國戰后融入西方,尤其是兩德統一,“德國問題”已不再困擾世界。盡管德國在歐債危機中的表現略顯強硬,引發一些爭議,有媒體甚至炒作其為“新德國問題”,但主流輿論并沒有擔心德國崛起給歐洲帶來威脅,相反在遇到困難時,各國習慣性地寄望于德國來出面解決,人們普遍對德國的領導力持認可和期待之態,“德國引擎”、“德國領頭羊”等詞匯近年來也充斥于歐洲媒體。正如著名社會學家、風險理論專家烏爾里希·貝克所言:“每個人都心知肚明,歐洲已經成了‘德國的歐洲’,只是還沒有人打破禁忌將其說出來而已”。*Ulrich Beck, Das deutsche Europa, Suhrkamp Verlag, 2012, S.7.
因此,對德國來說,如何擺脫發揮領導力的束縛、逐漸適應自身新的角色就成了當務之急。而事實上,德國對此也并非缺乏應有的認識。自從兩德統一后,關于德國外交政策“正常化”的討論就從未停止。德國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負擔,在政治外交領域長期“自縛手腳”,但內心深處還是期待能夠完全自主甚至積極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并獲得外界認可。如果說1997年2月,聯邦國防軍作為多國維和部隊的一部分在波黑監督《代頓協定》實施行動,德國軍人自二戰以后首次完全參與了一場軍事行動,標志著德國外交政策舊時代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連玉如:“‘新德國問題’探索”,《歐洲》,2002年第3期,第69頁。那么如今面對危機頻發的歐盟和世界,德國則獲得了進一步實現“正常國家”目標的機遇,而能否抓住機遇正考驗著德國領導人的智慧。因此,盡管有種種不適應,但為了扮演好各方都能接受的“領導者”,德國的政策已經開始有了明顯的轉向。
一方面,從理念上逐漸調整原有的外交思路。2014年初,德國總統、總理以及相關內閣部長同步發聲,宣稱德國將奉行“積極外交政策”,*關于該政策的詳細解讀,參見李超:“德國‘積極外交政策’評析”,《現代國際關系》,2014年第9期,第41~47頁。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外長施泰因邁爾則稱德國要“更及時、更堅決、更為實質地行動”,“不僅應對危機本身,還要加強預防和善后能力”。*Frank-Walter Steinmeier, “Krise, Ordnung, Europa: zur au?enpolitischen Verortung und Verantwortung Deutschlands”, Review 2014 -Au?enpolitik weiter denken, ausw?rtiges Amt, 2014, S.9.從近期表現來看,德國確實有意加大對周邊熱點問題的干預力度:在中東問題上,一改過去在伊拉克、利比亞戰爭上曾與盟國“唱反調”的做法,開始主動表態,拉打結合,盡管決策略顯遲緩,但最終還是派出了1300人參與打擊“伊斯蘭國”,同時其副總理以及情報機構負責人等還公開批評沙特“為‘伊斯蘭國’提供資金支持”,*Axel Schmidt, “German Vice Chancellor warns Saudi Arabia over Islamist funding”,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audi-germany-idUSKBN0TP0H720151206 (上網時間:2016年4月16日)突破了歐盟一貫“討好沙特”的做法;在難民問題上,向土耳其亮出“高價”,如同意重啟土入盟談判、為土提供更多財政援助、在土俄分歧上支持土等,提升土耳其接納難民的積極性;在烏克蘭問題上,考慮到歐盟和德國自身的安全穩定,默克爾雖同意延長對俄制裁,但同時并未放棄與俄接觸,更在反恐問題上推動俄美歐共同合作,有意創造西方與俄緩和的氛圍。
另一方面,在實踐中學會以更為靈活的手段處理事務。德國一直對自身模式高度自信,不愿在原則問題上過多讓步,這是導致歐盟伙伴對其信任度下降的重要原因。近些年來,德國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對“歐盟是妥協的產物”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德國前總理科爾就告誡民眾,“如果執拗于做自認為正確的事情,歐盟就不會取得目前這樣的成果”。*赫爾穆特·科爾著,鄭春榮、胡瑩譯:《憂心歐洲——我的呼吁》,同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1頁。因此,德國逐漸傾向于采取更靈活的手段處理分歧,較以往更重視其他成員國訴求,著力維護歐盟團結。例如,向英國許諾“可適度修改歐盟條約”,極力挽留英國留在歐盟內;默許法國不將增加反恐開支列入預算赤字;承認歐州央行量寬政策對刺激經濟起到正面作用;尊重部分國內民眾和東、南歐國家的意愿,出臺系列措施收緊難民政策,并協助意大利、希臘等國加強邊境管控等。 而且,從客觀環境來看,德國從“幕后”走向“臺前”也是大勢所趨。其一,盟友對德國的疑慮將日趨消減。伙伴國對德國領導力存在正反兩方面看法,既反對德國“只注重經濟利益,對國際事務漠不關心,對全球秩序缺乏戰略思考”,同時又擔心德國過于強大、主宰歐盟,疑其“不可信賴”。但隨著時間推移,外界逐漸發現,英國游離于歐盟邊緣,法國麻煩纏身,均無力擔當領導歐盟重任,在遇到問題時,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德國出力解決。德國強大的實力、推動一體化的堅定決心、拒絕“霸權主義”的傳統思維令其日益收獲信賴,預料未來歐盟國家將更為心平氣和地接受德國崛起和領導,這種氛圍也更有利于德國發揮領導力。其二,歐盟對外影響力中需要德國“色彩”。德國雖身處西方陣營,但發揮領導力的方式顯然有別于美、法等國。德國的行事風格總體穩重,遇事不會“爭強好勝”,能夠務實地看待問題并理性地尋找解決辦法,對待國際事務一般不走極端,樂于扮演溝通者和平衡者的角色。德國雖將更為積極地展現領導力,但“領導”不等于“主導”,德國也不會“事事出頭”,而將“勇于擔當、謙卑行事、不做獨行者”。*劉麗榮:“德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選擇性領導”,http://www.iis.fudan.edu.cn/2f/26/c6897a77606/page.htm.(上網時間:2016年4月18日)在此基調下,歐盟也將更多以合作和對話的模式解決內外事務,從而成為西方陣營中有別于美國的一支獨特力量。
綜上所述,德國當前面臨的“領導力困境”,根源在于其自身理念沒有跟上快速變化的環境,以致對于能力和地位的提升深感“不適應”,處理外部事務的手法尚顯稚嫩,領導力運用不夠純熟。事實上,傳統觀念雖難改變,但也不會一成不變;“適應新角色”需要一定時間,但也不會無限期延續下去。因此,雖然未來一段時間內德國在處理外部事務時或許還會遭遇這樣那樣的困難,但足夠的量變必然會帶來一定的質變,不斷積累經驗的德國將會逐步跳出“民族國家”的小圈子,更加主動地轉變思維去適應國際形勢新變化,以獨特且更靈活的手段展現其領導力。○
(責任編輯:王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