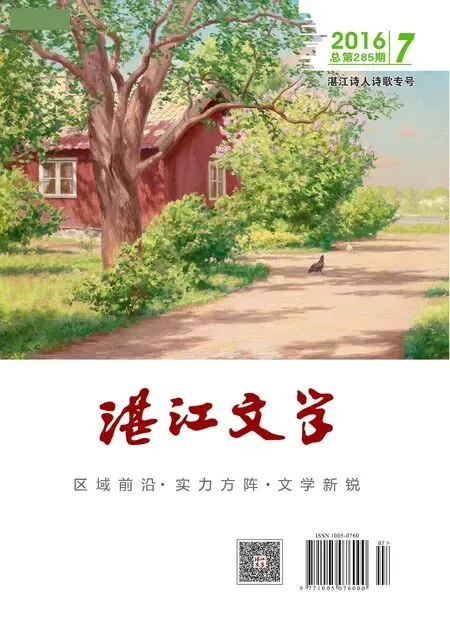魅力來自規范
——我的寫作觀
※ 趙金鐘
魅力來自規范
——我的寫作觀
※ 趙金鐘
康德指出:“每一藝術是以諸法則為前提的,即在它們的基礎上一個被稱為藝術的作品才能設想為可能。”藝術的魅力就在于在限制中爭得自由,在捆綁中爭得灑脫,在有限中爭得無限。正如朱光潛所言:“每種藝術都用一種媒介,都有一個規范,駕馭媒介和牽就規范在起始時都有若干困難。但是藝術的樂趣就在于征服這種困難之外還有余裕,還能帶幾分游戲態度任意縱橫揮掃,使作品顯得逸趣橫生。”。
詩歌寫作的規范較多,我覺得主要有三點。
第一,抒情表意之范。
古人云:“詩言志,歌永言”(《尚書·堯典》)。“志”就是“心”。“心”借助語言來體現,即為“志”。“志”其實就是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等的總和。體現在作品中,就是主題、旨趣。好的旨趣是一種美。“旨趣美”是功利的,也是審美的。它是詩歌的靈魂,是欣賞的重要內容和詩歌解讀的關鍵。
一些詩人顯然忽視了這一點。他們感興趣的是“語言還原”,追求的是對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意義的消解,以此來達到對詩歌所應承載的社會與文化意義的拆除。這是對詩歌寫作的誤解與架空。正像80年前陸志韋所說:“詩應切近語言,不就是語言。詩而就是語言,我們說話就夠了,何必做詩?”陸氏的話語在今天還有警示作用。
深度介入生活,在凡俗中求典雅的生活化審美特征和審美態度,是現代漢詩的重要詩學價值。新詩與舊詩介入生活的方式與程度不同。舊詩多在一種先在的敘述體系(或敘述框架)中介入生活,為了求雅而與生活拉開了距離(它有一套“雅”的結構體系和言語體系)。而新詩則是直接介入生活,在生活中求生存,在凡俗中求典雅。由于語言和結構的解放,就使得現代新詩較之舊詩更加生活化。這其實是新詩的一個長處,我們沒有理由擯棄。
第二,“寫的語言”之范。
語言在詩中的地位遠比在散文中顯赫。瓦萊利有句名言:“正如走路和跳舞一樣,他會區別兩種不同的類型:散文與詩。”走路只看中結果,不看中手段;跳舞得遵循舞步,自由度有限,且舞步本身就是目的。這說明語言不僅是詩的手段,同時是詩的目的。它本身就是詩歌鑒賞的主要內容。因此,詩不能直接運用現成口語,它必須對口語進行深加工,使之“書面化”。這就是詩歌寫作必須就“寫的語言”(朱光潛語)之范的緣由。
語言是人類思維的物質外殼,詩作為人類形象思維的產物,必然離不開這個外殼。但詩的語言絕不同于人類信息交流所使用的日常語言,它是對日常語言的詩化處理與二度提純,有著自己的獨特的組合法則。這種組合法則和組合后所誕生的語言,往往與其它文學語言也不相同,它是獨特的、惟一的。它不僅能表達“意義”,更要能表達“意味”,表達人格。這里面有兩個層次的含義:第一個層次是,它必須具有文學語言的一般性特征,如精練性、形象性、生動性,等等。但除此之外,它一定還要有第二個層次,高于一般文學語言的層次。即有著在精練性、形象性、生動性等基礎上的“有意味”的超越。
第三,詩歌結構之范。
在所有文學體裁中,詩歌的體格最小,所以最講究結構。而結構也最費心思,最需要詩人的才情與藝術修養。詩的成敗主要在于其是否以成功的組織方式釋放并框定了詩人對生活的認知,并通過這種組織方式去激活讀者的接受靈感,以達到對詩人留在詩中的情感與思想的認讀。這就是結構的功能。
古人將文學創作分為詩、文兩大類別是有道理的。這兩大類在構思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文”(含散文、小說等)因更注重外在描述而傾向于大眾化的話,那么“詩”則因更注重內情展示而帶有精英化色彩。表現在結構上,它更需要有化博為精、化散為聚、引淺入深的功能。一個小說家可以引導他的人物做一次長時間的旅行,一個散文家也可以做一次長距離的放足,但一個詩人只能將“距離”截斷,在戛然而止中給人一種豁然開朗的頓悟。如果說通過對某種生活的流程或情節的敘述即能完成一篇(部)“文”的結構的話,那么對于“詩”的處理就沒法來得這么干脆。它的結構的背后是對現實及其前動力的深刻認識與把握,而其本身則又是對于生活與詩人情愫的一次有意義的安排。結構不是一個外在于內容的皮囊,而是化入內容之中的詩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