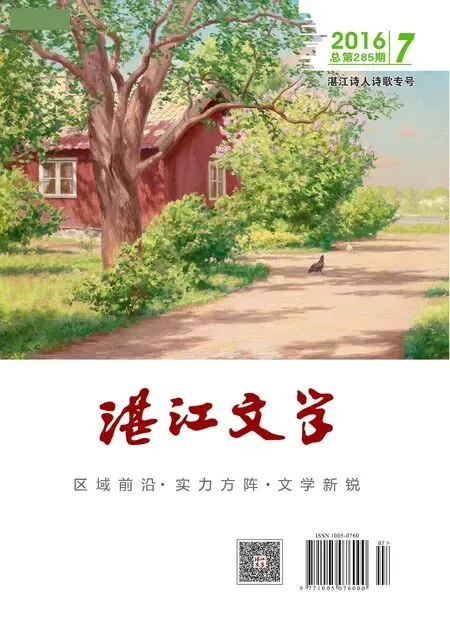在學習詩歌的路上
※ 袁志軍
在學習詩歌的路上
※ 袁志軍
孔夫子有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不學詩,無以言。”詩歌,被冠上了無數美好的寄托和遐想。她記錄了我們青蔥歲月里五彩的歌吟,是心靈跳動的強音!有人說過,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或長或短有過一段鐘情于詩歌的日子。在自己成長的歲月里,尤其是在那如詩的青春歲月里,無不懷著傾心而熾熱的心情,朝拜繆斯。
我的詩歌的寫作,最初是在高中時代開始萌芽。我是理科學生(當年的班主任認為我應該選學文科),不斷強化訓練邏輯思維,但那腔沸騰的熱血和感性無以寄托,就寄情于模仿古體詩詞,雖對平仄不得要領,但樂在其中,哪怕是打油詩,籍以抒發了滿腔的青春激情。及后考上大學,學的工程專業,卻噴發了詩歌的狂熱和創作的井噴。當時(1990年)在武漢水運工程學院(現武漢理工大學)擔任水藍藍詩社總編,編輯了一本社員詩刊,投寄到甘肅省刊《飛天》,在《大學生詩苑》欄目選發了13個人20首詩歌,這是那個階段我的詩歌創作最可以稱為標志性的事件。
學生時代,詩歌是我情感的出口。
1992年大學畢業之后,我到了一家交通部屬轄大型國有企業湛江港工作。工作半年之后,我從見習技術員調到機關總部宣傳處企業報編輯部,擔任副刊版編輯。在這個平臺上,職業(專業)接觸詩歌的機會多了,編、改投稿的詩歌機會不少,自己也陸陸續續寫了一些詩歌。而當時的宣傳處長(四十年代出生的老政工)到辦公室質問:這些是詩歌嗎?前言不搭后語,邏(狗)輯(屁)不通,我搞不懂你這個現代詩歌……這樣的江湖,從這開始,為了不影響“飯碗”,我的詩歌寫作絕對不觸及現實和工作這個“形而下”的土壤,走那些風花雪月的虛空飄渺。隨著職位的變遷,特別是做到了集團公司中層(尤其是作為黨委書記),必須要“講政治”,許多只能內心獨白卻又無法抒懷的感受,寄予詩歌,詩歌就成了我靈魂的出口,成了自我救贖的文字宗教。
在具體的詩歌寫作層面上,我的感受是:
等待靈感。靈感是一個非常玄妙的近乎唯心的東西。
臧克家說:“詩思來潮,半夜五更,便扭亮了小燈,急速提筆,恐怕稍儀遲疑,詩情跑了。”靈感的到來讓我們變得手足無措,會欣喜,會緊張,會不安,仿佛連心底那一絲最微小的情感亦被勾起。可以說,靈感只是給我們帶來了微稀光明,但卻讓我們尋著這抹光亮,看到了整片光明。當靈感來臨時,會感覺心中涌過無數情思,或許會想到天地,廣闊的空間,這偉大的造物;抑或會垂憐微小的事物,以寬厚的仁慈來注視生命的平凡。在充滿靈感的世界里,不需要太多理性的駕馭,只要愿意,可以將愛情比成受傷戰士對僅剩的一條腿的憐惜,也沒有人會拒絕向一株小草俯首稱臣……靈感中頓閃而過的情緒,一并決定了詩歌世界中的結局和命運。
當靈感來臨時,可能會有這樣幾種狀態:或許你是一個熱愛生活、有豐厚生活積累的人,各種熟悉的情境你思考了很久,在你的潛意識中積聚了很久,而在某個瞬間突然膨脹擴張以至一發而不可收拾。或許你在一個靜謐的清晨,一個安詳的午后,一個悠遠的午夜,獨自默然靜坐。周圍很靜,你的內心一如周圍一般,也很安靜,你任憑思緒如煙飄飛,在毫無預兆中,靈感悄悄地扣響了你的心門。又或許你正在桌前冥思苦想而不可得,有些倦了,掬起一捧水,輕輕拍打在臉上,看看窗外,伸個懶腰,風拂過,也可能在涌起的音樂波浪中,激起了腦海中閃過的一絲清明,瞥見了靈感的蹤影。
真情投入。除卻奇妙的靈感,詩歌創作同樣需要真情的投入。歌德曾告訴過我們,詩的骨子里是滲透著情感的,具有抒情的美;放逐了情感,也便放逐了詩。情感是一塊調色板,讓詩人隨心所欲,描繪出構想的意境。運用真情實意進行創作,是一個自然真實的過程,在那樣一個情境中,我們吐露的是最珍貴的心聲。
肆意想像。一個原始而靈動的生命,內心叫囂著焦躁和不安,掩藏在平靜的外表下,只想要憑借詩歌,去宣泄久已積聚的情緒(心靈的能量),撫平不得寧靜的心。因為蘊含情感,詩歌會讓我們產生共鳴,產生一種感情的滿足,心靈的顫動。海涅說過,讀者內心的情感,或者能被作家振奮起來,或者又會被作家刺傷。這也是詩歌能夠長久打動人心的獨特魅力。
語言訓練。每一個詩者必定會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前期可能更多的是模仿,日積月累,終于遇到(發現)了自己喜歡也適合表達自己的個性化的語言。
其實,我遠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一直在詩歌學習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