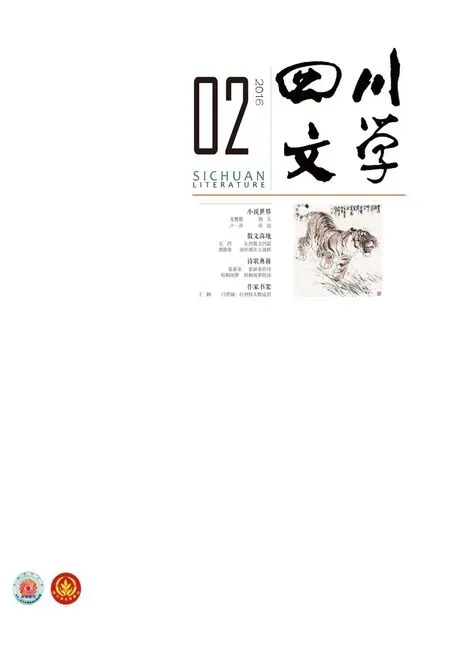四川的回憶錄
顧 彬
?
四川的回憶錄
顧 彬
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銷愁愁更愁。
四川,這個中國一個省的名字,我大概在高中學校第一次聽到,很可能是1964年。那一年我們學生在德文課上看了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 最有名的話劇。這個話劇叫“四川好人”,納粹時代布萊希特從1938年到1940年在國外寫了這部話劇。主人公是一個女的,她名字叫神德。這是一個說明人性格的名字。這女人好像是“神”,她肯定有“德”。布萊希特一輩子受到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他會很明白“神”與“德”是什么意思。
話劇里的人把神德看成“貧居窟的天使”。讀者或看眾也會認為她是很有道德的人。那么,這個女人為什么算四川的好人呢?原來是百神想了解大地上還會不會有仁人。如果有的話,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有希望。因此他們從空中下來,到大地上去找。因為神能找到神德這類的人,所以作者解釋作品的時候,說因為有她的氣質,四川就是世界上唯一個沒有受到剝削與壓迫的地方。真的是這樣嗎?從歷史來看不一定。社會發展不會這么簡單。但是如果我們從儒家來看,一個有獨特魔力 (Charisma) 的人可以改變一個社會。也很可能布萊希特受到了儒教的影響。反正他離不開中國文化。也可以說沒有德文版的中國哲學,就沒有布萊希特的作品。
布萊希特看了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1873-1930)所有翻譯成德文的中國經典哲學大作。特別是《道德經》決定了他的世界觀和寫作的路。他文筆的節奏,以及他對水弱不弱、強不強的了解都是從老子那里來的。
再談神德的名字。我相信女人的魔力,相信詩人的詩意。女人是生命、生活的起源,詩人是空想、幻想的主人。沒有女人,就沒有愛。沒有詩人,就沒有愛情。那么,這樣看,四川是女人美、詩人詩意的故鄉嗎?有不少人這樣對我說過,也包括現居北京的四川詩人們在內。咱們相信他們吧。
在高中學校時我與四川的關系當然是文本上的。當時因為是“文革”的時代,1973年前我們“西方人”沒辦法去中國看一看。雖然我們那時候可以去臺灣、香港和澳門,但是這三個地區對我們來說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從今天來看,這么一個立場當然會有問題的,這不必多說。
六十年代末,在當時的西德我們學漢學的學生們太需要有人給我們介紹中國,但是我們學到的基本上是書上的中國。我們的老師大部分也沒去過大陸,原因是第二大戰與冷戰。因此介紹中國的教授中到過中國的不多,不過是有的。我的導師是其中之一。他40年代在北京與南京待了好幾年。每一次在波鴻大學上課的時候,他給我們三、四個學生講他當時在當地的經驗與經歷。他有沒有去過四川,我不知道。但是他特別喜歡給我們分析李白最有名的一首詩,“早發白帝城”。 白帝城允許我第二次跟四川有文本的關系。
不過,那一次我聽到的好像不一定是一個百分之百純德國人的聲音,我聽見的聲音聽起來是一個中國人的。這是什么意思呢?當然李白最有名的詩好像還是一個德國教授給我們解釋的。無論如何,因為我的導師 Alfred Hoffmann (1911-1997) 上過中國老師的課,他就是每一次從他們的角度出發講的。因此我們覺得當時聽到的聲音是中國人的聲音,是李白個人的聲音,是唐朝的聲音。
白帝城是我的避難所,我很晚才去過。我在那里碰到過猴子嗎?沒有。為什么問呢?“兩岸猿聲啼不住”,我們的導師老給我們講這行詩。猴子真的能哭嗎?如果能哭,為什么要哭呢?白帝城不是很美嗎?猴子的美學跟人的美學可能不太一樣。
不過,也可能我的導師把“啼”這個字理解成“啼哭”是錯的。今天的古代漢語辭典把“啼”解釋成“鳥獸鳴叫”,大概是這個意思。很可惜我們今天的人沒辦法問當時的詩人。但是詩人如果還在的話,他會回答我們的問題嗎?我估計李白聽我們的問題以后,要把一杯酒吞下笑著說:“你們問猴子吧”。當時的猴子不能問,今天的猴子好像全部跑了。我們怎么辦呢?
德國哲學家 Hans Georg Gadamer (1900-2002) 說過一句使人吃驚的話。他說,聽很難。我們人應該好好學習聽。聽,這就是理解、了解。男人聽一個女人說話,也可能才聽到音素和不太有內容的響聲。男人不一定理解女人,人不一定理解動物。能不能了解、理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啼”不太可能是“啼哭”的意思,不過我們能理解一個猴子的心嗎?
我們高中學校的學生們當時上德文課不光看布萊希特的話劇,同時也看他的詩歌。他最有名的一首詩談老子出關。這個作品也是在國外寫的。它最重要的話題不一定是在納粹時代不得不流亡的問題,它的題目是《道德經》是怎么形成的。雖然這首長詩又讓我們學生再跟中國重新打開另外一種書上的關系,但是它主要觀點是幫助我們當時的讀者,也幫助我們今天的讀者理解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品是在什么情況之下出生的。除了《圣經》以外,《道德經》是最多翻譯成德文的一本書,也可以說它是德國人第二本圣經。
看書的人都覺得作者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可以不管,寫作的背景不要思考。通過他的“老子”,布萊希特想說明這類傳統的、對經典的態度是錯的,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具體情況的重要性。如果當時沒有海關要求老子給他留下來“什么東西”,那么我們今天的人大概沒辦法看到什么《道德經》之類的作品。
老子出關去四川這個故事當然是編輯的。從歷史來看不一定有道理,但是從創造來看它就是太有道理的。所有的創造需要一個來源。比如我現在寫的這篇散文,如果沒有“美文雜志”要求的話,我從來沒有開始拿筆。這不光是從來沒有開始寫的問題,這更是從來沒有想出一些思想來的問題。如果沒有海關讓老子記載他的觀點,《道德經》非常豐富的思想會存在嗎?因為老子“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不必跟任何人說話。可是我們今天的人不一定“什么”都知道。因此我們需要老子,因此我們需要海關問老子這類的人。
幾十年來批評我們所謂的西方人是非常時髦的,特別是批判我們與中國的文本關系。不過到最近,沒有批評家思考過連中國人對中國有的時候也才會有這類文本的關系。為了了解白帝城的猴子,他們能夠回到唐朝去嗎?他們能跟李白見面嗎?猴子走了,李白走了。只有我們今人留下來。后代會批評我們,但是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當代人都覺得我們是歷史的高潮。白帝城的猴子也可能是這樣看自己的。不光時間是殘酷的,歷史是更殘忍的。今天最偉大的,明天變成了歷史木乃伊。而我們的后代覺得后天才是歷史的終點。我們呢?我們是歷史的廢物。
I
回憶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它跟一個養壞的情人一樣,有的時候來,有的時候不來。我脾氣多變的記憶說我第一次到成都是1979年。當時我作為導游帶一個德國旅行團來中國訪問。因為那時候漢學沒有太發展,我心里準備好一輩子作為旅游陪同。當然我已經拿了博士學位,但是在當時的西德不少有博士學位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就開出租汽車,也包括后來獲得漢學教授位置的學者在內。雖然我會開車,但我不喜歡開車,我寧愿騎自行車。70、80年代的中國是自行車的天堂。當時我讓不少旅客們跟我騎自行車參觀北京,我們都很高興。汽車不多,路好走。人很慢,山很慢,太陽很慢。什么都慢。不光慢,也不太亮,因為電不夠。1975年的北京晚上7點后是黑色的。當時我們歐洲來的在今天的北語學中文的人,享受中國首都的黑夜。因為在非常發達的西歐我們看不到真正的黑夜,連夜里也是明亮的。
對歐洲人來說,黑夜算浪漫的,算女人的本身。因此每天晚上在頤和園看日落的時候,我們感覺到我們存在的秘密。老看日落這是說明我們有空,不再受到身心負擔。當時我們好像跟其他中國人一樣,沒事兒要干。當時我臨時的故鄉是明斯特 (Münster),北威州一個古老的大學城市。在那里我每天感覺到精神壓力。原因是讀完博士后 (1973) 我看不到前途,拼命地找工作,最后決定作為高中學校的老師,要在我 Rheine 的 母校教德文與宗教。閑暇這個詞,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更不說能享受什么悠閑。在急急忙忙的情況之下,1973年的春天突然有一個沒有想到的機會,我能夠來華學一年的現代漢語。1972年當時的西德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1974年的11月底,我第一次到北京,北京是灰色的。我第一次到成都,成都也是灰色的。當時大概是1979年的春天,我陪了一個旅行團。除了大雨外,我們當時好像什么都沒有看到。不過我的記憶不完全同意我的感覺,它提醒我我們在老城還看了一些老房子。因為我是策勒(Celle) 出生的,因此我特別愛老房子。策勒這個德國北方的小鎮第二大戰沒有受到破壞,它仍然保留它原來中世紀的樣子。遷居到策勒郊區的新房子以前,我家住在15世紀的桁木架房屋。好幾年以前我帶住北京的詩人王家新與住成都的詩人翟永明參觀他們兩位參觀我的故鄉,都非常興奮。
我經常說老房子是一個城市的臉孔。不過,今天不少城市缺少它們自己的面孔。這不光是一個中國發展的問題,這是一個世界上到處都能發現的傾向。對我來說,每一個古老的建筑都有它自己的歷史,會講它獨特的故事。拆老房這是拆一個城市的來源,留下來一個傷口。恐怕1979年的雨中我看到的成都老房今天已經都沒了。代替它們的很可能也是高樓。住在摩天大樓生活當然會舒服一些。空間多,從上面每天可以看日落,也好。可是,因為高樓大部分一模一樣,人很快會覺得缺少什么。缺少一種認同感。因為房子跟書一樣,應該作為一個人最密切的朋友。我們真正的朋友們不可能都沒有區別。他們是個體的,他們有自己的面貌、語言和手勢。看他們的眼睛,我們知道他們是誰,不可能把他們叫錯。
因為我第一次來中國距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年,所以我有四十多年的記憶。我的中國學生,無論在波恩、北京、汕頭或者青島,他們都沒有這么長的記憶。我的中國和他們的中國完全不一樣,這是正常的。我的中國是藍天的、四合院的,沒有太多車的、小房子的、非常慢的、閑暇的,不一定是不幸福的,沒有錢的,簡單的。他們的中國是發展的、快的、堵車的、高樓的、讓人家疲勞緊張的,不一定非常幸福的,富裕的、復雜的。
成都我幾年來去得不少。我在那里上過課,開過朗誦會。那么我跟其他的外國人一樣特別喜歡這個城市嗎?2005年在四川大學教書的時候當地的人告訴我,外國人愛成都的無所事事。1000塊人民幣差不多夠好好過一個月的日子。那么,1000塊當時等于100塊歐元在當天的西歐這筆錢可能才允許一個人過一天。我不知道四川的首府今天還是這么便宜,還是讓人家入一個頹廢的生活方式。我呢?當時我住在一個賓館,沒有時間頹廢,我寫我的詩、備課、鍛煉身體、參觀城內外的名勝古跡。那一年我在成都感覺到什么靈魂上的、身體上的煩惱嗎?好像沒有。我好像非常,睡得好,吃得好,游覽也不錯。
我了解成都嗎?了解是一個太復雜的現象。了解是一種藝術,是一種過程。不可能我們今天的了解跟明天的一樣。更不可能我們男人了解一個女人,她不會不要求我們第二天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來看她。對所謂異國的了解也是這樣。今天的四川不是明天的。如果我們在長江坐船到了萬州后要進四川的門,我們跟李白或杜甫一樣嗎?他們當時來的時候沒看到什么高樓。如果我們能問他們你們是乘馬達船,飛機或高鐵來的嗎。他們會聽得懂嗎?從今天來看他們是中國人,但是連中國人也不一定能全部懂中華的過去和未來。大部分的外國人會比蘇東坡或曹雪芹更理解1949那一年。你跟他們說什么解放沒用。因此我們的了解都發生在固定的條件之下,這些條件是歷史決定的。
最近我在杭州上課的時候,那里的一個教授問我了解杭州嗎。他的意思是說我理解多少呢。他以為外國人沒聽說過這個城市的名字,因此在介紹它的時候該加上“在上海附近”這些字。那么成都呢? 問題可能一個樣。不會很多外國人知道它在哪一個省。不過,德國人好一些,因為波恩與成都90年代來建立了友好交流關系。
無論如何,什么都是一個符號。四川的符號比方說是麻辣豆腐、是酸辣湯。我都喜歡吃,我也會自己做。我的兒子們老要求我給他們做。他們多么享受。連我的中國朋友也覺得我的酸辣湯很特別。因為它非常辣,也非常酸。不過它的秘密在于醋。好些年前,大概是2000年的秋天, 我在烏鎮聽當地的人說他們的醋可以預防癌癥。后來我在青島發現那里的人喝醋,吃飯的時候喝小瓶。那么我學烏鎮人、青島人多“吃醋”。另外準備酸辣湯,我就多加醋。因此我的酸辣湯比不少中國飯館兒好吃得多。此刻我的酸辣湯是我的符號。北島寫我,他寫我的酸辣湯。每一次我的女兒Anna回家,她想吃酸辣湯。顧城歌頌了我酸辣湯的醋,因為我用的是中國的醋。我還記得他1992年的秋天在我柏林房子吃我的酸辣湯時說的話“ 中國醋還是好”。這句話重要嗎?已經過了20多年了我還記得。不是奇怪嗎?好像不是。如果他少吃過我酸辣湯的醋,也可能他還會在我們中間。
魯迅說過因為不能忘記,因此他寫作。寫作與紀念是分不開的。沒有回憶,沒有文學,應該說沒有回憶就沒有優秀的作品。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問題就在這。這個不多說,因為這不是我的題目。我的題目是四川。談四川我碰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今天的四川跟我書上認識的四川不一樣。四川一部分現在不再算是四川。它一部分現在叫重慶,屬于重慶市。它有奧地利大,好像是小國。但是因為李白入過四川之門,這就是今天的萬州,原來的萬縣,因此現在屬于重慶的這個城市對我來說還是代表四川。要不然來四川的李白不是李白,他是另外一個人。
我談四川,當然談我個人的四川,我不談別人的。我要談我的四川形象 (image)。當然某一種形象不能代表所謂的現實 (reality)。如果兩個人對某一個對象有同樣的感覺,他們的現實可能開始形成。不過我一個人創造的形象,那么我的形象沒有代表性。如果有的話,那么它只能代表我個人的觀點。另外,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形象不光能發生變化,它們也會變老了,跟人一樣。每一種形象只能告訴別人我們是怎么看的。我們的形象跟我們說的、要的、主張的道理、真理沒有什么關系。新約的羅馬帝國代表 Pilatus 問得很對“ 什么叫道理、真理呢”。
也可以說每一種形象才是一種建議,允許我們思考要怎么理解什么。因此這種建議是 o開放的(open),根本不是固定的。我為什么主張這個呢?后殖民主義的理論與政治正確的理論都認為有對的和錯的認識,比如對中國的認識。如果我們的立場不是非邏輯的,那就沒有對的或錯的了解。只能存在有意思的、沒有意思的看法。這個原來跟后殖民主義或政治正確性都無關,還是應該說我們不要老從這種很有問題的理論來看我們想了解的對象。
最大的問題不一定在這兒。問題在于這兩種意識狀態不允許人培養什么“錯的”、什么“不正確的”觀點。大概2000年,我在意大利開會談憂郁、憂郁癥在中國的問題。我原來想說明辛亥革命前的中華不一定有歐洲式的憂郁、憂郁癥。那么我很快倒霉了。一個美國人聽我的報告后,馬上就要求我應該承認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歐洲式的悲哀。但是如果我們從歷史來看她根本沒有,另外憂郁、憂郁癥不一定是好的。但是這個美國漢學家為什么非要求我承認中國也有呢?因為美國漢學界討厭我們歐洲人說“中國沒有”的學術態度。按照政治正確理論“西方”有的,中華也應該“有”。雖然那個美國漢學家要求我承認“中國也有”,從思想史來看完全是錯的,我為了避免其他的麻煩還是“承認了”傳統中國也有憂郁、憂郁癥。她就滿意了。我只能說可憐的中國,更可憐的美國。
歷史是復雜的,因此人家寧愿選意識狀態(ideology),從意識狀態 看歷史、看男人、看寫作。意識狀態允許我們用最簡單的說法來談中國。這不是一個外國人的問題。這也是一個中國人的問題。也可能更是中國人的問題。因為外國漢學界還會有比較客觀的日本、韓國、德國學者談中國優秀的文化。
中國是一個符號。不光對外國人,也是對中國人。比方說成都出生的巴金把中國傳統的家庭看成一種代表壓力與剝削的機構。不過他在國內外讀者中非常成功的長篇小說《家》對儒教系統的看法太簡單。孔子的學說好像全部是壓迫年輕人、特別是女人的制度。從五四運動來看,儒教肯定有不得不批判的地方。但是真地可以或應該全面否定它嗎?另外,年輕人離開“家”以后,他們會很容易找到一條新路嗎?他們不要的是中國的傳統,他們追求的是現代性 (modernity)。當然現代 (modern times) 給我們帶來好多好處:讓人健康的醫學,允許我們自己決定我們個人的未來,女人的解放等。都不錯,都應該有,不能否定。比方說沒有女人解放,就沒有現代性。不過,現代性也會有它不太理想的地方。因為什么都可以自己決定,人會越來越孤獨。作出要“走”的決議后,人家去哪里呢?魯迅提過這個問題。他從易卜生話劇的主人公娜拉( Nora) 出發談這個困境。
現代人老在路上。他的“路上”跟李白或杜甫在四川的“路上”完全不一樣。兩個詩人離開家想回家,回到具體的家。還是他們希望在四川能看到他們的朋友。有家、有朋友就不要發愁,因為家與朋友給他們需要的認同 (identity)。不過,現代人無家可歸。因為社會發展,人老要變。不光是他個人要發生很多變化,他的周圍也是、也可能更是。現代城市老在變。為了擴大生活空間、生活方便,要蓋好多高樓。高樓里有自來水有暖氣,有洗澡間,有地方享受看書、吃飯或看錄像等可是高樓跟舊房子非常不一樣。在第36層不能看樓下的人什么時候來,什么時候走。鄰居也不一定互相認識也可能不要互相認識。
再說,人到了現代不再會有一個“故鄉” ,“故鄉德文說 Heimat,味道跟英文 home 不太一樣。現代性不是一種 終點,它是一個過程,一個從來不會停止的過程。所以人因為不斷在過程中沒有他的認同,沒有固定的認同。如果還有的話,它每天不一樣。比馬克思早幾十年的歌德時代 (1770-1830) ,人已經發現了分工給人帶來什么困難。分工的現象把人變成兩種人—分工讓人失去他原來有的、還是覺得有的整體感。現代的勞動方式才允許他完成部分工作。在傳統時代大概是一個人能做一輛馬車。在現代時代是好幾個人生產一輛奔馳。原來是 一個人需要掌握好幾個工序來創造什么,現在一個人才掌握一個工序,就夠了。這就是流水線每天給我們講的事實。
流水線是速度,現代性是速度化。沒有速度,沒有現代。“文革”的中國沒有發達的原因就是在這兒。當時什么都慢。晚上7點后所有的飯館關門了。人回家看新聞,然后睡去。中午的南京街上沒人,鄭州的中午誰都在睡覺。恐怕成都當時也是這樣。巴金《家》的主人公也都睡去了嗎?這個四川來的作家有一次說:“文革”最深刻的話是“你多保重”。保重什么呢?保重慢性嗎?思想的慢性嗎?痛苦的慢性嗎?巴金要求過該建立一個“文革”文獻資料站。“文革”結束了快40年了。這類的資料站中國有嗎?不能夠說沒有,也不敢說有。因為汕頭市附近有紀念當時、當地死的不少人。我去過,我在那里寫過詩。汕頭外的紀念館不是全國的,只是地方的。也好。因為跟一滴水一樣。了解水,一滴水夠了;了解“文革”慢性的悲哀,一個紀念館夠了。
速度與慢性。它們不得不對立嗎?所有的現代化只能破壞傳統嗎?在傳統的廢墟上創造一個完全新的時代嗎?這個問題難回答。我的回答不一定會有代表性,不過可以思考。德國巴瓦利亞的丁克斯比爾 是小鎮,人口可能不超過一萬。它是中世紀全部保留下來的城市。原來有火車站,但是居民不要,怕太多旅客們會來。現在只能坐大巴來參觀,但是公交車不允許進城,人應該從城外的停車場走路進去。原來日本人多參觀丁克斯比爾。現在不來了,因為他們不想走路。過去他們的旅游車可以到城市的中心。現在不行了,日本人就不來了。代替他們是中國人,他們不怕走一點路。路上他們越來越興奮。因為他們可以回去。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他們渴望的花園。到處都是花、樹、仙鶴。
丁克斯比爾是一個很慢的城市,沒有工業,它靠農業,旅游業。它是一個富裕的小城,沒有乞丐,沒有窮人。不少人整天坐在街上聊天,什么都不做。城里誰都認識誰,誰都跟誰打個招呼,也包括外地來的人在內。我最近在那里的飯館聽一個老百姓談外國人。他講得滿有意思。他說,誰都可以來,但是他該有道德。如果有道德他是我們的,如果沒有他不是。
從丁克斯比爾來看,好像財富與速度不一定應該有關系。我經常帶中國朋友到這個小鎮去。最近我的一個很密切的中國朋友到了以后說,這里老百姓住的家在中國只有百萬富翁能住。好像丁克斯比爾完成了社會主義。它的情況很特別,完全靠它的傳統。每年這里紀念幾百年前的一個小孩子,這個小孩當時救了丁克斯比爾。三十年戰爭時瑞典軍隊原來要占領這個城市。不過,城里一個四歲的男孩兒說服瑞典的統帥不要搶劫它。為了記住這件事情,城市讓孩子每年游行表演當時的故事。游行活動時,好像丁克斯比爾所有的孩子在街上。因為這個紀念活動,到外地賺錢的居民都回來參加活動。他們的回鄉跟李白與杜甫的回鄉一樣,是一個很具體的回家。為了歡迎他們,所有的房子安上了花的裝飾,不能出來的老人在比較低的窗戶上跟他們打個招呼聊天。
這是陶淵明的桃花源嗎?好像是,好像。德文有一個說法: 少是多,慢是快。丁克斯比爾是它最理想的代表。
林語堂描寫的中國文化是一個慢性的文化。他特別喜歡從北京的老頭子來看它古老的文明。到最近我們還能觀察老爺爺們在首都的街上打牌、下棋、看熱鬧。他們當然賺不了什么錢,不過對他們來說財產不是他們生活的目的。他們寧愿跟他們的哥兒們聊聊。他們幸福嗎?大概是。我呢?我看他們的快樂,我看丁克斯比爾的小花園,我知道愉快不是能賣的,所有的得意是精神的事情。
北京胡同的老人缺少什么嗎?丁克斯比爾 的居民感覺到分工的壓力嗎?好像都不是,好像。黑格爾說過一句決定現代性特點的重要的話。他認為,人到現代時代只能夠有一種自覺狀態,這就是不幸福的意識。請看巴金《家》里的主人公,他們都是年輕人。他們想離開成都。因為對他們來說,成都代表中國的傳統,一個壓迫人的傳統。無論我們怎么看他們對儒教的理解,從黑格爾的角度看,他們是矛盾的,因為他們大概覺得自己是這種人,但是想做那種人。走了后他們得到幸福嗎,能夠做為“一個人”嗎?我們只能希望,他們從成都到北京或到上海的路不太悲哀。在“文革”的上海對巴金和他的同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你多保重”。他們當時也許是兩種人,是充滿了痛苦的人,同時充滿了希望的人。1979年后呢?那么,問問他們吧。
II
成都詩人翟永明在第一組詩“女人”中,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來。一個人完成了他想作的、他想寫的,他想創造的,那么后來還會有什么嗎?還會有什么優秀的作品、什么貢獻嗎?這個女詩人不是第一個思考這個重要問題的人。德國詩人戈弗里德 ·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 可能比她早30年也問過自己:完成了20世紀最好的詩歌之一,一個作家還會寫什么呢?
有些藝術家們也包括歌手在內,雖然才出了一幅圖畫、一支歌兒、一首詩、一篇散文,他們還是能終生有名,一輩子賺得了好多稿費。丁玲很早就主張一本書。她的意思是說,一個作家能出一本誰都聽說過、誰都看過的書,那么就夠了。丁玲有這么一種著作嗎?她有。反正在國外她寫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到現在有它的讀者。還有成都來的張棗 (1962-2010)。去世前,他在中國、在德國才有一本書,是中文的和德漢雙語的。去世后他的朋友出了他的散文集等。無論如何他還在的時候,他已經算新時期最優秀的詩人之一。他去世了后,他的讀者不光在中國也在德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買他的一本詩集。
好像張棗出版了他唯一本詩集后,不能再創造什么。我最后一次跟他見過面,大概是2006年的九月份在北大,他坦率地告訴我,他“寫完了”。他的意思是,他幾年來不能再寫什么,未來也可能是這樣。當時我想,他原來該翻譯。他的創造力量會回來。我從1988年到1994年連一行詩寫不出來。那么除了從事我的散文寫作外,我當時多翻譯,基本上翻譯了魯迅的作品和中國當代詩歌。到了1994年的夏天,我突然能再寫詩,到現在沒有停筆。我已經出了什么十本一百多頁的詩集。
張棗會不少外語。他的德文跟德國人一樣,他的英語流利,好像他還掌握基礎俄語與法語。因此我原來老希望他能翻譯到現在沒有中國人注意到的德國當代詩歌。我老鼓勵過他這樣做,見面時他每一次答應了。不過,基本上除了學李白多喝酒以外,他去世前再沒有什么大的貢獻。這不是很可惜嗎?老實說他浪費了他優秀的才能。
不光張棗這個人可憐,他德文版的詩集也是。這個作者覺得他太了不起。因此他想他在德國出的書應該賣它自己。無論我給他安排什么朗誦會,他不會帶他的作品,也不告訴人家有我的翻譯。原因大概是他怕他的一個朋友會不高興。原來是這個朋友應該、也想出張棗的詩集,但是他從來沒有。怎么辦呢?沉默。沉默是中國人避免問題的好方法。我不太喜歡避免問題,因此也不愛沉默。事實是事實。事實上我翻譯了張棗的詩集。不過,他的朋友寫張棗的悼詞說,附件里有他第一次翻譯的張棗一組詩。我為什么提到這個呢?這不是小事兒嗎?面對生死肯定是。但是這也說明一個問題。如果連最密切的朋友與同事不知道我們譯者們做什么,那么我們的工作是白做的。最可憐的不一定是我們,可能更可憐的是我們的書,是出版社。
聽說他還在的時候,他德文版的、設計非常美的詩集才賣了四本。出版社不一定為了張棗而虧本兒了,但是事實是出了我的翻譯后出版社很快關門了,賣了他的房子。張棗的書在一個柏林地下室失蹤了。幸虧有波恩一個很能干的書店找到了它書的新主人,買了一百本。它們在萊茵河地區賣得很不錯。因此該書店又訂了幾十本。這樣地下室的張棗詩集又復活了。我高興嗎?我當然高興,因為我沒有白搞過我的翻譯。不過我同時也很難過。四川有很多有才能的作者,但是他們自己知道他們是天才嗎?他們大概知道,但是也許他們覺得,自己的天賦是永恒的,跟他們的生命一樣。今天不寫,那么可以明天寫吧。對張棗沒有明天,連今天也沒有。他已經去世五年了。少一人,多一種痛苦恐怕張棗的早死有象征的意義。聽說成都文人的興趣首先在于玩兒。白天睡覺,晚上出去。玩兒也可能就是一種頹廢。張棗最后在北京過的日子是玩兒,白天吃喝,夜里吃喝。什么都不寫,什么都不翻譯。
一本主義有道理嗎?不少1979年后的中國作家,從德國的角度來看不過是蜉蝣,他們缺少很長的呼吸。因此老貝恩與小翟提的問題是非常重要,作者們太少思考這個問題。不過,他 / 她們兩位提到的難題不光是一個文學的,也是一個社會的。人類還在夢想自己能夠克服所有生命的困境,幻想有一天會入天堂。因此人老在試試看能不能改善社會的情況,能不能提高生活的標準。但是人知道什么時候他夠了嗎?“More i not enough”( 更多還不夠), 這類的口號我最近在北京機場看過。那么,再問什么是 enough,什么算 夠呢?第二大戰來大部分的國家主張現代化,歌頌現代化。這個態度大概是對的。不過,現代化后會有什么,還會有什么嗎?現代化完了,歷史也結束了嗎?1989年有一個姓 Fukuyama 的美國學者公開宣布了歷史的終止。那么,歷史真地停止發展嗎?原來的夢都會結束嗎?那么就問離開四川的老子,寫《四川好人》的布萊希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