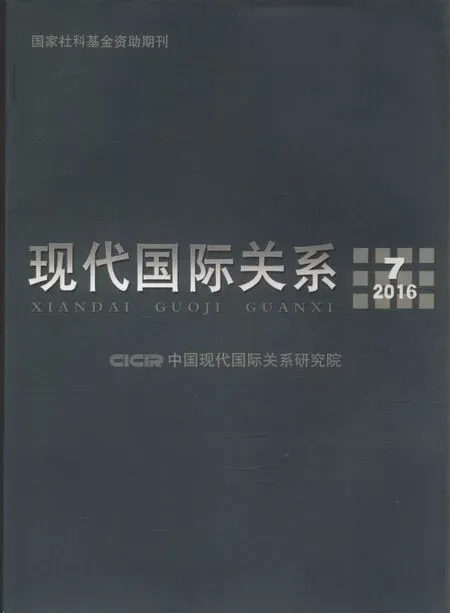對法國當前“疲弱癥”的看法
王 朔 周譚豪
對法國當前“疲弱癥”的看法
王 朔 周譚豪
當前,法國正陷入經濟與安全的雙重困境,似患上了某種“疲弱癥”,屢遭外界質疑。執政的社會黨政府雖采取系列應對舉措,并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改革推進十分艱難,效果不彰。未來法國不大可能陷入嚴重衰退,但囿于自身結構性桎梏,難有根本性改觀。
法國 法國經濟 歐洲大國
[作者介紹] 王朔,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歐洲一體化、歐洲經濟、法國問題;周譚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研究實習員,主要研究法國問題。
“法國衰落論”源起于上世紀90年代,時常被輿論拿來炒作。但法國畢竟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經濟總量仍能保持世界前列,且一向“擁有超出自身實力的政治影響力”,故以往此類預言從未成真,結果當然也就不攻自破。然而,自此次金融和債務危機以來,法國卻陷入內憂外患,經濟落入泥潭難以自拔,更禍起蕭墻、連遭恐襲,以致唱衰聲再次抬頭。法國甚至被外界指為“歐洲心臟的定時炸彈”、“問題兒童”和“歐洲病夫”。法蘭西昔日的榮光似乎因此黯淡無存,人們甚至懷疑法國可能就此沒落。本文試圖從當前法國面臨的主要困境入手,分析其深層次原因,由此展望法國未來的發展前景。
一、 難以擺脫的經濟困境
相對多數歐洲國家而言,法國經濟的增長緩慢既不新鮮亦不典型,何況法國在金融和債務危機期間所受打擊并沒有那么大,更無法與飽受詬病的“歐豬五國”相提并論。但危機發生后,歐洲國家普遍知恥后勇、忍痛改革,力圖亡羊補牢,唯有法國明顯滯后、疲態漸顯,手持“藥方”而拖延難醫。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普雷特直言,法國“最令人驚訝”之處有二:一是“并無他國那樣的嚴重債務或銀行業危機,經濟卻表現疲弱”;二是“政府改革意愿真實,卻選擇碎步推進,至今成果有限”。*AFP,“ La BCE ‘surprise’ de la faible croissance fran?aise”, http://bfmbusiness.bfmtv.com/monde/la-bce-surprise-de-la-faible-croissance-francaise-925391.html.(上網時間:2016年7月3日)事實上,法國的問題還遠非僅僅是經濟低迷那么簡單,經濟問題還進一步激化了階層、族群及宗教等社會矛盾,加之周邊安全局勢急轉直下,極端勢力趁虛而入,首都巴黎一年內兩遭重大恐襲,令人不得不正視法國全面下滑而自身又力有不逮的現實。
2008年以來,法國經濟年均增幅不到0.5%,*Eurostat,“ Euro Area Unemployment Rate at 10.7%”, 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7091248/3-01122015-AP-EN.pdf.(上網時間:2016年6月5日)且失業率始終居高不下,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高達10.2%*INSEE, “ Le taux de chmage est stable au premier trimestre 2016”, http://www.insee.fr/fr/themes/info-rapide.asp?id=14.(上網時間:2016年6月5日),系典型的無就業復蘇。2014年法國經濟體總量更被英國超越,排名降為全球第六。*邢雪、李永群:“時隔40多年,法國經濟被英國趕超”,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108/c1004-26345593.html.(上網時間:2016年6月5日)這種經濟上的疲弱具體表現為消費和投資動力不足以及產業競爭力低下,同時更因政府調控空間有限、政策失誤而使問題進一步被放大。
其一,通脹率一路走低,在歐元區基本墊底。2015年2月,法國5年來首現通縮,全年平均通脹率僅為零。*INSEE,“ Taux d’inflation en France”, http://www.insee.fr/fr/themes/series-longues.asp?indicateur=inflation. (上網時間:2016年7月2日)2016年在歐元區多數成員國通脹有所緩和的情況下,法國仍在低通脹與通縮間徘徊,6月法蘭西銀行更將2016、2017兩年通脹預期自1%、1.5%大幅調低至0.2%、1.1%。*參見敦敏:“經濟前景仍暗淡,法國央行調低法國2017通脹及GDP預期”, http://news.fx678.com/C/20160603/201606031653201542.shtml.(上網時間:2016年7月2日)低通脹既是經濟低迷的直接反映,也會加大緊縮預期,反過來推動消費者延遲消費、企業縮減成本,從而進一步抑制增長、加劇失業,造成螺旋式下滑。對于法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來說,危害遠大于通脹攀升,僅依靠現有政策非常難以逆轉。
其二,在歐盟整體緊縮的情況下,財赤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仍持續攀升。誠然,法國1981年以來就從未實現過政府預算的平衡。但形勢今非昔比,債務危機后的歐盟嚴格了財政紀律,要求成員國必須大幅減赤減債,否則將予以懲罰。總統奧朗德原承諾上臺兩年(至2013年)就完成將財赤和公共債務占比降至歐盟規定的3%、60%以下,但實際上進展十分緩慢,甚至不時出現倒退,截至2015年底,仍分別達3.5%和95.7%。*Les Echos,“Le déficit public meilleur que prévu, à 3,5% du PIB en 2015”, http://www.lesechos.fr/economie-france/budget-fiscalite/021793971261-le-deficit-public-meilleur-que-prevu-a-35-en-2015-1209781.php.(上網時間:2016年6月6日)法國不得不兩度宣布推遲財赤達標期限至2017年,引發歐盟及絕大多數成員國強烈不滿。即便如此,各方仍不看好法國能否如期達標,一再呼吁后者“采取更多行動”。*Euronews,“France, Italy, Spain, Portugal Seen Breaking EU Deficit Rules - Commission”, http://www.euronews.com/newswires/3142014-france-italy-spain-portugal-seen-breaking-eu-deficit-rules-commission/.(上網時間:2016年6月6日)隨著法國通脹持續低迷,產品和服務價格將呈下降趨勢,債務實際價值則將上升。政府為解決經濟頹勢,又不得不加大減稅、增支力度,反過來遲滯了減赤步伐,公共債務顯著增加。奧朗德亦坦言,要想如期達標,需同時滿足“經濟超預期增長、控制開支及嚴格實施預算案”三個條件。*秋實:“審計院稱2017年政府減赤目標難實現奧朗德寬慰人心”,法國《歐洲時報》,http://www.oushinet.com/news/europe/france/20160701/235484.html。(上網時間:2016年7月2日)而對當前的法國而言,這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三,生產投資明顯不足,經濟復蘇缺乏最基本的支撐。法國當前增長疲弱的一大重要原因和表現是市場投資意愿不足。一方面,企業不相信未來幾年經濟將大幅回暖,對擴大生產抱有疑慮,不愿加大投入,甚至自己主動縮減瘦身;另一方面,銀行為提升抗風險能力,調整資產負債結構,不看好企業經營前景,而將更多資金由實體部門轉向金融領域,擠壓了企業融資空間。此外,法國近三成的國內生產依賴外資,美資占其中的1/4。*法國中國工商會:“法國概況·投資環境”,http://www.aecf-france.org/france_investissement.htm.(上網時間:2016年7月2日)而近來美國經濟加速復蘇,美聯儲不斷透露加息傾向,加之英國“脫歐”風云重擊歐洲市場,促使美資加速回流。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歐洲央行持續量寬,法國政府也“零零碎碎”出臺經濟刺激措施,但收效甚微,并未大幅改善企業經營環境及投資信心。*Guillaume de Calignon,“Bilan 2015: l’état de la France en 12 graphiques”, Les Echos, http://www.lesechos.fr/28/12/2015/lesechos.fr/021579819444_bilan-2015---l-etat-de-la-france-en-12-graphiques.htm.(上網時間:2016年6月6日)
其四,科技進步被阻塞,產業競爭力難以有效提升。相對而言,法國諸多產業起步早、基礎好、體系成熟,良好教育亦培養出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并能夠產生大量新的創意,如很多德國工業設備和英美金融產品均由法國人設計,但法國國內始終未疏通將技術和創意轉換成本土生產力的有效渠道,導致過去數十年來科技進展相對緩慢,人才大量流失,加之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工業制成品形成層次“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局。同時,法國單位生產力為歐洲最高,但1999年實施35小時工作制后,工時顯著減少、勞動力成本迅速升高。2000年法國制造業平均小時成本為24歐元,低于德國的28歐元,而現今升幅已超過20%(德不到10%),成為歐盟小時勞動成本最高的國家,每小時最低工資達35歐元,而德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分別為32、28、22和21歐元。*參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2014年法國經濟形勢分析及2015年前景展望”,http://daibiaochu.ccpit.org/Contents/Channel_1632/2014/1224/437434/content_437434.htm.(上網時間:2016年6月6日)因此,近年法國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榜上的排名呈下降趨勢,2015~2016年僅列第22位,遠遜于德國、英國,甚至還不如馬來西亞等發展中國家。*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2016”, http://www3.weforum.org/docs/gcr/2015-2016/Global_Competitiveness_Report_2015-2016.pdf.(上網時間:2016年6月6日)企業利潤空間呈下降趨勢,逐漸失去國際市場份額。2000~2014年,法國占全球貿易比重從5.1%一路降至3.1%,遠遠落后于德國目前的7.8%。*Ministère fran?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Résultats 2014 du commerce extérieur”,http://www.diplomatie.gouv.fr/fr/IMG/pdf/Commerce_exterieurV2Compresse_cle817d9e.pdf.(上網時間:2016年6月6日)特別是2012年以來,隨著債務危機的緩解,德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出口份額紛紛開始回升,法國卻依然處于頹勢。*BNP,“ France: External Accounts: Misleading Improvement?”, http://economic-research.bnpparibas.com/views/DisplayPublication.aspx??type=document&ldPdf=27656.(上網時間:2016年6月6日)
其五,“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趨勢加劇,削弱經濟發展的根基。20世紀80年代以來,法國政府就一直力推產業改革,但政策始終處于搖擺之中,在國有化與私有化間幾度徘徊,而外部世界日新月異,新興經濟體開始崛起并大力招商引資,推動法企將主要精力移向海外。金融和債務危機助長這一勢頭。如今法企60%的產業均在海外,令該國工業比例在歐盟內“墊底”,甚至不如重債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特別是出口結構中制造產品日減,而服務產品、對外投資日增。*Cécile Crouzel,“ Les entreprises fran?aises préfèrent s'implanter à l'étranger qu'exporter”, http://www.lefigaro.fr/conjoncture/2015/06/26/20002-20150626ARTFIG00003-les-entreprises-francaises-preferent-s-implanter-a-l-etranger-qu-exporter.php.(上網時間:2016年7月7日)2005~2015年法國工業領域的工作崗位流失7.5萬個,對外貿易連年逆差,法國工業亟待以新的面貌贏得市場。*參見韓冰:“法國品牌推廣的三大亮點”,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5-04/29/content_5076.htm.(上網時間:2016年6月7日)奧朗德也坦言,法國一度有一種錯誤想法,就是工業已過時,國家發展不再需要工廠、工程師、技術工人,法國進入了“服務業經濟”的時代。事實證明,這一想法并不現實,“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不具備強勁工業實力”。*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fran?aise,“Intervent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ur la nouvelle France industrielle”,http://www.elysee.fr/assets/pdf/intervention-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sur-la-nouvelle-france-industrielle.pdf.(上網時間:2016年6月7日)
奧朗德政府思路不清、政策混亂則是造成如此窘境的背后推手,甚至可謂“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2012年社會黨上臺前已17年未曾主政,執政團隊中包括總統、總理在內的絕大部分要員缺乏經驗,左派的理想主義色彩濃厚。故而其在執政初期一直高舉“公正與減赤并重”大旗,主張通過“劫富濟貧”來增稅增收,甚至提出邊際稅率分別高達75%、60%的巨富稅、資產利得稅,讓“所有人都為國作貢獻”。*La Tribune,“La taxe à 75% disparat le 1er janvier 2015”, http://www.latribune.fr/actualites/economie/france/20141229trib267ff7d00/la-taxe-a-75-disparait-le-1er-janvier-2015.html.(上網時間:2016年6月7日)毋庸置疑,此種做法的結果必然是適得其反,最后成了資本外逃的催化劑,法國的市場形象一落千丈。2013年10月的美國商會晴雨表顯示,法國推出增稅措施僅一年,美企對赴法投資的積極比例就從56%驟減至13%。*American Corporations in France,“ American Business and Some French Traditions...”, https://www.understandfrance.org/Business/AmericanCorporations.html.(上網時間:2016年7月5日)至此,奧朗德才如夢初醒,開始重新調整經濟改革思路,轉向“增長與減赤并重”,并部分吸納右派主張。這又引發了社會黨內左派、其他左翼各黨及工會的激烈反對,反而動搖了社會黨自身的執政根基,政府被迫三度改組,執政聯盟貌合神離,極大削弱了其施政力。當然,奧朗德自己也因此成了“第五共和國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Le Parisien,“ Sondage: Hollande, le moins bon des présidents de la Ve République”, http://www.leparisien.fr/politique/sondage-hollande-le-moins-bon-des-presidents-de-la-ve-republique-17-05-2014-3849067.php.(上網時間:2016年7月5日)
二、 越陷越深的安全困境
經濟好,一切可能都不是問題。但經濟不好,可能一切都會是問題。經濟的持續低迷,必然會從社會層面上反映出來。人們看不到希望和前途,情緒不免緊張焦慮,原有的社會各階層、族群及宗教之間的矛盾隨之加大,安全形勢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惡化。由于歷史、地理和政治等因素,法國階層本就分化明顯,加之族群眾多,多元文化長期并存,發展卻不平衡,導致社會融合明顯不足。各方在“蛋糕”夠分的時候尚能相安無事,一旦“蛋糕”不夠,自然就要為爭奪權利和資源、轉嫁成本和風險進行博弈,更難免相互推諉、指責,削弱社會團結和宗教寬容,甚至不時出現打砸搶燒和以暴易暴的情況,直接沖擊其自由、平等、博愛等基本價值觀。
一方面,近年來,以穆斯林為代表的移民與本土白人矛盾激化,致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極右排外主義雙雙坐大。法本土約有600萬穆斯林,幾乎占總人口1/10,且規模日益壯大。*Samuel Laurent, Alexandre Pouchard,“ Quel est le poids de l'islam en France?”, http://www.lemonde.fr/les-decodeurs/article/2015/01/21/que-pese-l-islam-en-france_4559859_4355770.html. (上網時間:2016年7月5日)盡管法國政府一直持“多元包容文化”的論調,但基于歷史與現實原因,主流社會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始終或多或少地存在偏見。大量穆斯林移民只能徘徊于社會底層,在教育水平、職業地位、收入等方面遠遜于本土白人,部分地區25歲以下穆斯林青年半數失業*Claude Minni, Mahrez Okba, emploi et chomage des immigres en 2011, Dares Analyses, no77, octobre 2012.,極易陷入“失業、種族歧視直至與警察沖突”的惡性循環。加之經濟困境持續難解,本土白人對穆斯林表現出的所謂“得寸進尺”更為不滿,反移民、反歐盟、反全球化的行為日增,雙方沖突甚至還波及到其他少數族裔,引發猶太人大量外遷,使整個社會處于一種撕裂狀態。2016年以來,法國各類游行示威不斷,有關各方激進性、敵對性有增無減,惡性事件頻發,政府疲于應對,甚至不得不考慮摒棄法國民主、人權傳統,暫時禁止游行示威。但這并非根本解決之法,甚至連治標都做不到。雖然法國政府也在反思以往的移民政策,甚至已開始著手加強管控,但問題已廣泛、深度發酵。
另一方面,法國在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馬里和中非等地強勢干涉,不斷招致仇恨,最終引火燒身。由于近年歐盟周邊持續動蕩,法國為保后院利益不失,軍事活動十分活躍,甚至一度有超過美國的勢頭,這引發了穆斯林世界對法國的強烈不滿。伊斯蘭極端勢力則趁機將“惡毒骯臟的法國人”鎖定為優先襲擊目標,利用法國地理位置近、邊境管控松、國內安保力量不足及穆斯林移民數量多等特點,重點經營涵蓋宣傳、培訓、滲透及后勤等在內的“圣戰產業鏈”,周密策劃,伺機作案。“伊斯蘭國”等極端勢力還“與時俱進”地運用新媒體爭奪輿論高地,通過各類涉“圣戰”網絡論壇、視頻網站、社交平臺等宣傳“圣戰”思想、“招兵買馬”、傳授制造恐怖行動技術,利用PS4游戲機、匿名網絡瀏覽器等工具傳遞加密信息,阻撓警方解密與追蹤。這些蠱惑、煽動頗有成效,尤其對徘徊于西方社會與伊斯蘭傳統之間、懷抱理想又涉世未深的法國青年來說,誘惑不可謂不深,“圣戰”分子也顯著呈年輕化去向。法國內政部長卡澤納夫就指出,2014年法國遭受的恐襲案中,“近90%的案件中互聯網發揮了關鍵作用”。*Adrienne Sigel, Cécile Ollivier,“Cazeneuve,‘ 90% des individus qui basculent dans le terrorisme le font par Internet’”, http://www.bfmtv.com/politique/cazeneuve-90percent-des-individus-qui-basculent-dans-le-terrorisme-le-font-par-internet-864646.html.(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目前,法國已是歐盟“圣戰”分子第一大來源國,涉“圣戰”“核心圈”人數至少有2000余人,其中200多人“受訓”后回流法國,成為不折不扣的“定時炸彈”。*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aise,“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http://www.gouvernement.fr/action/la-lutte-contre-le-terrorisme.(上網時間:2016年7月7日)
上訴兩方面的問題相互結合引發恐襲的集中化、常態化。自2014年底開始,法國連遭毒手,不僅覆蓋眾多城市、動輒數十人傷亡,且襲擊目標、手法不斷翻新,令人防不勝防。2015年11月13日,巴黎更遭號稱“歐版9·11”的“二戰后最嚴重恐襲”,致132人死亡、349人傷,甚至奧朗德、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等政要也險些遇害。*Le Parisien,“Attentats du 13 novembre à Paris : le fil des évènements de la nuit”, http://www.leparisien.fr/faits-divers/attentats-paris-fusillades-explosions-etat-d-urgence-13-11-2015-5273837.php.(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不同,這些恐怖分子拒絕談判、不提條件,悍不畏死,手段極其兇殘,作案唯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制造殺傷,引發社會及民眾恐慌,煽動民族宗教仇恨,將法國逼入安全內外交困的窘境。
經濟與安全本就是深關國家與人民發展乃至生存的核心問題,當二者均陷困境時,不僅牽扯大量精力,還不可避免地產生溢出效應,加劇法國政治分裂,束縛外交手腳。傳統左右兩派之間對立加深,各自內部四分五裂;極左、極右小黨乃至無黨派力量日漸坐大,開始形成獨立于社會、共和兩黨外的“第三勢力”。法國標志性的獨立自主外交也受波及,經濟外交、反恐外交上升為主旋律,價值觀色彩進一步褪色,軟實力大打折扣。奧朗德“法國還是不是大國”的自問與“希望是”的自答正凸顯了這種無奈。*Fran?ois Hollande,“Discours de M.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vant la communauté fran?aise à Vientiane”,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fran?aise, http://www.elysee.fr/declarations/article/discours-de-m-le-president-de-la-republique-devant-la-communaute-francaise-a-vientiane/.(上網時間:2016年7月7日)
三、 結構性桎梏根深蒂固
既然知道問題是什么,也知道解決問題的要點,但為何就是難有作為而聽之任之呢?說到底,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法國社會長久以來的結構性矛盾,其個中因素紛繁復雜。
其一,傳統思維方式難以適應環境快速變化。法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存在著較為深層的社會文化根源,因此不應完全將其看作是經濟問題。逾半數法國人是天主教徒,受其影響的比例更達八成,因而普遍對經濟不感興趣,更愿意做公務員。法國歷任領導人,無論政治立場如何,都在經濟上相對保守,對市場經濟較為警惕,致法國國內商業氛圍有所不足。而且法國社會一直以來都是國家概念較強,民主主義勢力強大,民眾更普遍天性擔憂,骨子里“仇富”,不愿意信任市場,對市場經濟的接受程度低。第五共和國開國總統戴高樂公開將“錢”列為法國兩大敵人之一,奧朗德則稱國際金融為“真正敵人”。*Henry Samuel,“ Francois Hollande, the Drab Socialist Who Declared Finance His ‘True Enemy’”,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9219689/Francois-Hollande-the-drab-Socialist-who-declared-finance-his-true-enemy.html.(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同時,面對全球化、自由貿易浪潮,法國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成本太高,而是“別人的成本太低”。在這種思想主導下,法國難以較好地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快速變化。此外,法國還是一個難有共識的國家,不具備德國施羅德式改革的條件。當年德國改革的層次很深,主要針對勞動力市場,到默克爾上臺后即開始享受改革的紅利,經濟也一路順風順水,在歐債危機中一枝獨秀。而法國始終礙于其“國家團結優先、解決現實問題優先”的思維邏輯,很難做到既保護一部分,又不傷害另一部分。因此,法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其很難像某些國家一樣因應環境而動、強力推進改革,這很大程度上與薩科齊還是奧朗德執政并沒有關系。
其二,自身經濟體制機制相對僵化。法國雖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其具體模式卻有著與其他歐盟成員國不同的特征。如德國實行所謂社會市場經濟,即政府不直接干預市場,但通過制定嚴格的規則和實施有效的監管,保持市場穩定正常運轉,充分發揮企業自身的積極性,同時兼顧社會公正;英國實行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式自由市場經濟,是世界上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經濟支柱主要是金融、保險、商業等服務業,因此更偏重于“最少的干預就是最好的管理”。法國的市場經濟總體沿襲路易十四時代的科爾貝理念,屬于混合模式,既強調市場的作用,同時國家在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政府通過控股企業等方式較深程度地掌控國民經濟,更接近于“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二戰后,法國曾連續施行過多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在實現經濟的快速復興、解決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曾發揮重大作用。但現在,這種模式在全球化下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如政府干預過多,行政效率低下,特別是大型國企擠占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令后者“脆弱不堪”,國家的扶持卻往往向大企業嚴重傾斜。同時,法國還是一個典型的高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理念,對教育、醫療、救濟等領域關注度高,民眾也慣于“養尊處優”,高度依賴政府,甚至主動失業,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法國公共支出長期占國家財政“半壁江山”,2014年占GDP57.5%,在世界范圍內僅次于芬蘭,其中社保及養老金分別占比32%、13.8%,遠高于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21.6%、7.9%)。*Rapha?l Legendre,“Le FMI épingle l’inefficacité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en France”, http://www.lopinion.fr/edition/economie/fmi-epingle-l-inefficacite-depense-publique-en-france-97663.(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2015年其公共支出占比雖略有下降,但仍達56.8%。*INSEE,“ General Government Accounts - Year 2015 (preliminary results) ”,http://www.insee.fr/en/themes/info-rapide.asp?id=37.(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法國經濟與觀察研究中心指出,隨著老齡化加劇(目前法國65歲以上人口約20%),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法國2017年養老金缺口將擴大至150億歐元。*Guillaume Guichard,“En 2017, le déficit des retraites pourrait être bien pire que prévu”, http://www.lefigaro.fr/retraite/2015/01/06/05004-20150106ARTFIG00273-le-deficit-des-retraites-pourrait-etre-plus-mauvais-que-prevu-en-2017.php.(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但在歐盟的財政紀律要求下,法國政府不得不控制赤字,導致在向來自詡為“西方民主先鋒”的法國,民眾示威游行成為家常便飯,政府根本不是對手,所以只能不斷增加稅收。2014年法國稅收占GDP比高達45.2%,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僅次于丹麥。*Anne Cheyvialle,“La France, vice-championne du monde des taxes”, http://www.lefigaro.fr/conjoncture/2015/12/03/20002-20151203ARTFIG00104-la-france-vice-championne-du-monde-des-taxes.php.(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同時,法國勞動力市場十分僵化,對勞動者過度保護,許多行業甚至依然沿用工業革命時期舊習,如現代火車司機的勞動強度與蒸汽機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但仍然保留著舊的福利制度。解聘更有諸多條款約束,雇主階層擔心麻煩纏身而不愿增加雇員,進一步加劇了失業。此外,法國的退休年齡比英、德等一直偏低,薩科齊時期就曾試圖將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以縮小日益擴大的養老金缺口,但甚是不得民心,奧朗德上臺后不得不再將這一政策回調。法國制度的僵化、保守導致企業怨言頗多,加之工會力量過于強大,在勞資談判中往往占據優勢地位,更使企業束手束腳,難以應對。
其三,傳統價值觀與社會現實存在矛盾。法國一向自視為自由、民主和平等先鋒,積極倡導多元文化、包容并蓄,并將其作為法蘭西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視為自身軟實力體現。而且,法國在歷史上曾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至今仍與其中多數保持著密切聯系,這里頭既有情感親近,也有道義虧欠,同時日益老齡化的社會也確實需要外來勞動力注入,因此對移民大開口子,尤其以中東和非洲裔居多。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新的競爭與挑戰日益開始沖擊歐洲舊有體制,加之危機后法國的經濟長期低迷、失業率高企,福利社會負面問題日益突出,極易將失業、治安等問題的矛頭指向移民,為社會對立情緒提供了養分。民調顯示,43%法國人認為穆斯林社區對其國家身份是種威脅,65%法國人將伊斯蘭教與“暴力”、“落后”相聯系。*陸華:“‘伊斯蘭恐懼癥’:被誤解和受損害的穆斯林”,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5/1/9/1223951.shtml.(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面對這種情況,法政府開始推行較為嚴格的政教分離政策,強調公民身份,淡化族群、民族及宗教身份,堅持文化同質性和單一性,試圖以法國價值觀“改造”國內伊斯蘭教。但現實中,這些政策往往缺乏對伊斯蘭文明的尊重,與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文化習俗相悖,結果非但未產生團結,反而孕育分化,導致穆斯林移民年輕一代更堅定自身宗教認同而非公民認同。從另一個角度看,社會現實也使得穆斯林群體自身欠缺融入的主動性。一代穆斯林移民的伊斯蘭屬性根深蒂固,抵歐后抱團取暖,抗拒融入,但仍與主流社會相安無事。二、三代移民成長于“文明沖突”前沿,始終對“認同”迷惑,被家庭要求恪守伊斯蘭傳統的同時又接受“平等、自由”價值觀熏陶,但在現實中被迫蝸居社會邊緣。多種糾結和落差助燃其負面情緒,極易受極端思想蠱惑。同時,盡管法國主流穆斯林群體竭力宣示伊斯蘭教“和平屬性”,極力撇清與極端勢力關系,但法執法部門、媒體輿論及本土白人仍“自然地”將法境內違法犯罪和暴恐事件增多與穆斯林掛鉤,過分強調部分案犯“穆斯林身份”,并不斷加大對國內穆斯林監控和約束,也逐漸喚醒了穆斯林群體歷史積怨和“悲情意識”,使其對法不滿情緒逐漸上升。
其四,政治大眾化束縛手腳。債務危機雖已過去,但余波未平,民眾生活也沒有明顯改善,因此對現行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充滿不信任,對主要政黨的政治認同度不斷下降,認為“政黨內部不再能夠產生創意與新思想”*周文儀:“法國民眾對政黨‘絕情’ 學者:法國政黨走向沒落”,法國《歐洲時報》,http://www.oushinet.com/news/europe/france/20160222/221944.html。(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事實上,歐盟嚴格的財政紀律已激起部分民眾的強烈反感,認為歐盟不能傾聽其呼聲,太過注重財政緊縮,已成為國家經濟的束縛。2016年6月,皮尤最新民調顯示,超過60%的法國選民反對歐盟,比例甚至超過英國。*子衿:“皮尤研究所:反歐盟情緒彌漫全歐”,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6-06-08/doc-ifxsvenx3651290.shtml.(上網時間:2016年7月5日)此外,近幾年伊斯蘭恐怖主義事件接連發生,歐洲排外、保守一面趨強,也為反歐洲一體化、反移民的極右勢力提供了養分。在整個歐盟范圍內,極右勢力普遍上升,政治碎片化加劇,法國政壇尤為明顯,政治生態持續惡化。極右政黨“國民陣線”聲勢日盛,成為2014~2015年的選舉大贏家。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換屆選舉中,出人意料地收獲近25%的選票,明顯領先于傳統黨派;2015年3月的法國省議會選舉中,雖未獲任何一個省的控制權,但拿下25%的選票支持,民意基礎不可小覷;2015年12月的大區議會選舉中,雖未在任何大區獲勝,但大區議席數量卻猛增3倍至300余個。*Olivier Mazerolle, Julien Absalon, Aymeric Parthonnaud,“Marine Le Pen:‘ Le Front national gagne progressivement la confiance des Fran?ais’”, RTL, http://www.rtl.fr/actu/politique/marine-le-pen-est-l-invitee-de-rtl-resultats-regionales-2015-7-decembre-7780766698.(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國民陣線”黨首瑪麗娜·勒龐支持率水漲船高,一路突破30%,各方預計其很可能在2017年總統大選時進入次輪。小勒龐本人亦“劍指總統寶座”,自詡“腳步無可阻擋”。*Les Echos,“Régionales 2015:‘rien ne pourra nous arrêter’, lance Marine Le Pen, malgré sa défaite”, http://www.lesechos.fr/13/12/2015/lesechos.fr/021555824953_regionales-2015-----rien-ne-pourra-nous-arreter----lance-marine-le-pen--malgre-sa-defaite.htm.(上網時間:2016年6月19日)相比之下,當前執政的奧朗德卻始終面臨左右為難的困境,既要秉持社會黨傳統的“公正”理念,又要挽救低迷的經濟,事實上改革只能是避重就輕、含糊不定,雖然隨著社會壓力增大,奧朗德的政策也開始有所“右傾”,逐步向企業作出減負、松綁承諾,甚至不惜觸動民眾“福利蛋糕”,希望能借此提高經濟競爭力、平衡公共收支,但事實上是左右兩派都不買賬:右派認為改革力度小,理想色彩過重,沒有觸及根本問題,不能有效提振經濟;左派則認為政府是“為了資本家利益犧牲民眾”,有悖左派傳統,傳統選民紛紛投奔“反全球化”的極右勢力。
如此種種,法國各界早有共識。但是,縱觀法國歷史可以發現,大改革、大變局無一不需靠激進革命或重大危機倒逼。奧朗德的改革理念與舉措也并非獨創“法門”,而是與前任希拉克、薩科齊大同小異。但希、薩二人面對各自改革機遇,或無法克服社會阻力,或受到外界沖擊,都只進行了“百日維新”,而奧也沒能抓住其剛上臺時既獲絕對權力、又攜民眾期待的機遇,始終前瞻后顧、左搖右擺,至于今日,雖仍懷作為之心,但實屬有心無力。
四、未來的法國之路
面對難題,當前執政社會黨政府自然知曉“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也確實一再表示要“勒緊腰帶改革”,同時推進經改與“維穩”措施,一面將促增長、帶就業作為政策重點,鼓勵創新,力推“再工業化”,增加對企業支持,改革勞動力市場,整頓公共財政;一面強化社會管控,健全安防體系,力促民族融合,加緊內外打恐,力圖遏制極端主義驟升勢頭,維系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社會黨政府改革確實取得了些許成效,經濟略有回升,內外安全威脅也有所緩解,如2016年年初政府提前截獲“伊斯蘭國”將再襲巴黎的情報,最終迫使該組織將襲擊目標轉移至布魯塞爾;在國際社會聯手打擊下,敘利亞、伊拉克反恐戰局亦有一定改觀等。
但顯然,這些都只是表征改善,奧朗德式改革沒有也很難卒除現有桎梏,而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進三步退兩步”,停留在“小修小補”,并未“傷筋動骨”,甚至念“拖字訣”,更多寄望于外部利好。可以說,能做的都做了,而那些能夠解決問題卻很難做到的,卻一點兒也沒做。在此情況下,經濟低迷與社會矛盾仍將繼續相互作用、彼此放大,進一步增加問題的復雜性。對法國來說,促增長、保就業本是政府的首要目標,但當前迫切的反恐及移民問題卻打亂政府了工作計劃。提升反恐級別,增加對情報執法及國防投入力度,強化對中東、非洲等地干預,必然導致“維穩”成本增加。法國還計劃未來兩年接收3萬難民,多種壓力將使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更困難,既不利于減赤、減債及推進結構改革,也勢必壓縮政府在教育、科技及培訓等公共領域投資空間,長遠看,不但不利于法國經濟走出困境,也將進一步放大社會矛盾,助長惡性循環。
2017年大選日益迫近,奧朗德希望在執政的最后時段通過主打經濟、安全牌挽回民意,反而在改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甚至被法國政治學家福蓋評論為“搬起石頭砸自己腳”。其在經濟與安全領域標志性改革也遭遇前所未有阻力,勞工法改革命途多舛,政府尚可繞過議會強行通過,但難死守最初版本,政府內部也分歧日顯,奧朗德會否臨陣妥協尚難預料;加強反恐能力的憲法修正案更因議會兩院“未能就修正案的措辭達成一致,尤其是未能就廢除恐怖分子的法國國籍等問題達成妥協”,并被輿論諷刺為“雷聲大、雨點小”。當然,如果奧朗德真能頂住內外壓力,有效落實改革措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改善政府預算赤字并減少政府債務,則蟬聯總統寶座猶有可能。但問題在于,奧朗德不可能不顧及本身黨派根基,因此也不可能真去大幅削減醫療、救助等社會福利,必然畏手畏腳、虛多實少,難見成效。從近期民調觀察,不論右派候選人為何人,奧朗德都很可能在2017年總統大選中止步首輪。
一言以蔽之,所謂法式“疲弱癥”,就是大病難犯、小痛不斷。盡管藥方眾所周知,改革也在搞,推行起來卻總是艱難、反復、糾結、搖擺,不但解決不了老問題,還有可能牽出新問題。2017年法國大選后,無論是社會黨接著執政,還是右派得以上臺,恐怕仍將是同樣問題、同樣方案甚至同樣結局,很難堅持“不忘初心”。可以預見,法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繼續處于這種經濟低速增長、安全風險反復的“新常態”。○
(責任編輯:吳興佐)